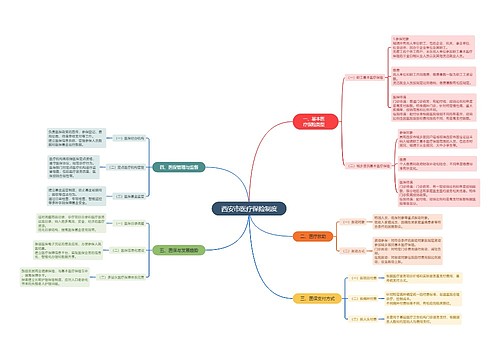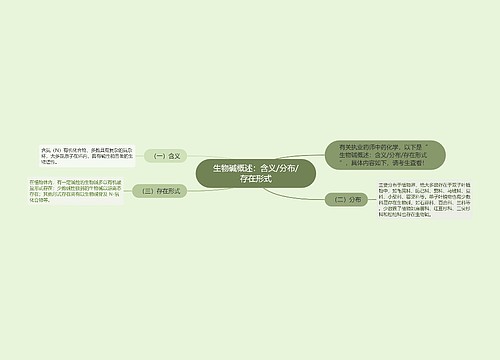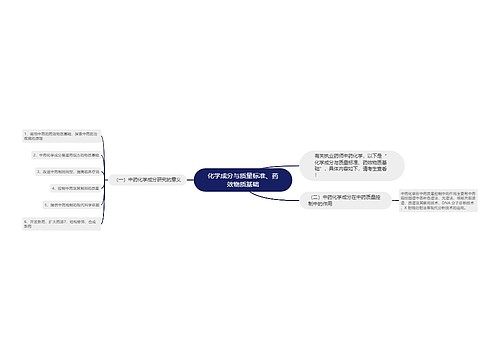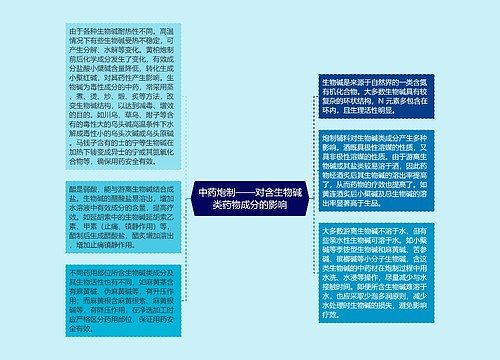宋文斌拉开抽屉,只见里面摞着用信封做成的“村民家庭账本”,足有几百封。上面登记着哪家哪户、何时就诊、历次处方及所欠药费等各种信息。
“加起来,这些账怎么也有六七千元。”这名山西文水县的村医说,“都是乡里乡亲的,也不好意思张口讨债。有的能还,有的就一直欠着了。”
由于要支付卫生室的房租、水电费,以及各种培训管理费,资金周转有困难,宋文斌也欠着药店的钱。每次都得等“村里的账收回来些,再还药店”。
宋文斌是本村人,去年考试通过后,成为本村唯一的一名村医,每月能领到政府补助400元。妻子从卫校毕业后也来到卫生室帮忙。在别人眼里,能够捧到这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宋文斌是幸运的,但他却有自己的苦衷。
在农村,医生上门看病都是义务的,不收一分钱出诊费。“出诊还不分白天黑夜,夜里两三点被人叫醒去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宋文斌的妻子说。
出诊不收费,靠卖药也挣不了钱。有时夜间出诊,算上卖药的钱,连本带利下来总共也就有个两三元。更多时候,村卫生室的药都是“拆零”来卖。村民要买个3片5片的,收费的话宋文斌小两口也说不出口。
妻子说,与过去不同,现在村里人看待村医的眼光也变了。以前叫“请医生”,现在是“叫医生”。医生治好病是应该的,看不好,就落埋怨;不是医生的责任,也说是医生的。因为责任太大,宋文斌每天给人看病打针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
“风险太大、挣钱太少,说起来咱还是带手艺的。”妻子说,“村医不好干,弊大于利,一旦有个医疗纠纷我们根本担不起。”
听说年底村卫生室要推行药品销售零差价,宋文斌也不知此事是好是坏,具体情况到时才知道。
除了看病,宋文斌每周还要协助上级进村入户,搜集信息,建村民健康档案,承担着多项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很多时候忙不过来。小两口也曾想聘请年长的赤脚医生来分担,但聘人又是一笔支出。算算账,他俩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们还好说,还年轻,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赤脚医生)挺可怜。”宋文斌说,他父亲宋执保做了一辈子“赤脚医生”,60多岁了还“转不了正”,很失落。老人原先子承父业很满意,现在却有些悲观。
在宋文斌的周围,像父亲这样“老无着落”的赤脚医生大有人在。
宋文斌也冒出过一个念头:如果有好事情做,就不干这行了。但想归想,30多岁了,改行也不好改。宋文斌的妻子说,民间不是有那句俗话嘛——“三十不学艺,学艺不咋的”。
现在,愿意做村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而宋文斌最大的心愿则是:希望医改能出台政策,等自己年老时能有保障。
当地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乡村医生是农民身边的“健康守护人”,在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受待遇、机制等种种因素影响,村医的岗位要想吸引人,并且长久地留住人,仍是推进医改过程中待解的难题。

 U156383470
U156383470
 U248012522
U248012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