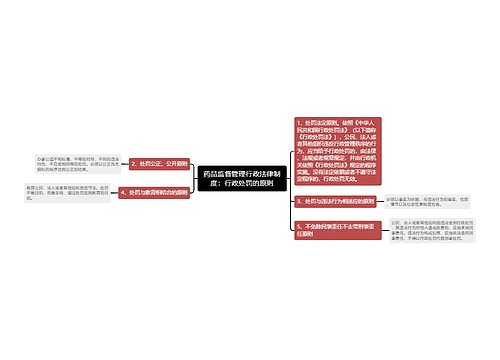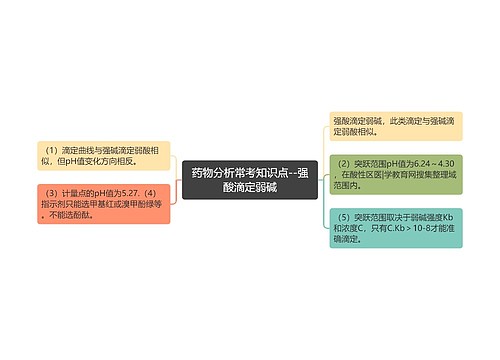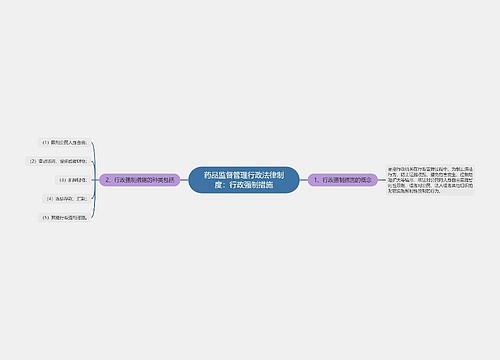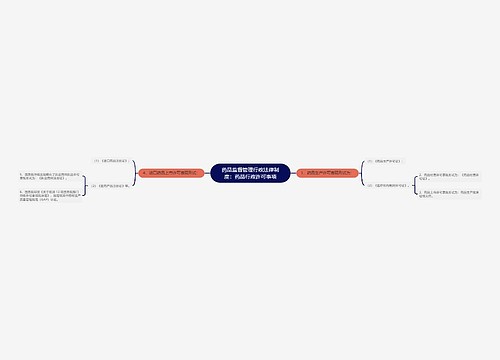《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意外失踪思维导图
落魄潦倒
2023-02-20

意外
医院
政府
医疗
卫生部
改革
卫生
没有
医疗事故
医疗改革
医疗改革解读
一年以前,一份有关医院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业界纷纷扬扬传说很久后几乎已经落生,但一年过去了,围绕这份《意见》,人们从企盼、焦虑,到疑惑、失望,《意见》流产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意外失踪》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意外失踪》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a1b833ecb2d0051a55a05308fb556df9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意外失踪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记者 胥晓莺
《意见》一拖再拖
“是有这么一份《意见》,但《意见》还在征询意见。”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蔡仁华有些无奈地说。
蔡仁华1988年进入国家卫生部,先后担任过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全国公费医疗事务管理中心主任等重要职务,1998年退到卫生部所属卫生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可以说亲身参与策划和见证了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的卫生体制改革。但对于这场改革,现在是大学教授身份的蔡仁华已经不愿再发表什么意见了。
他所说的这份《意见》,全称《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由卫生部牵头制定。2004年7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一个针对医院管理的培训班的开学仪式上,国务院法制办公司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曾透露,《意见》将在几个月内出台。此后,有媒体报道《意见》已定在2004年底之前出台,后又传言将在2005年1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布。随后,业内又传说《意见》出台可能拖延至今年的6月底。可是时至今日,《意见》依然不见踪影。
这份《意见》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传说原稿中对国有医院市场化的敏感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宋瑞霖在那次公开表态中曾透露,按照《意见》,国有医院的产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
而据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意见》原文中还有更具轰动性的提法:“以前隶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医院的剥离工作,必须在2005年以前完成”,“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中国医师协会一位肖姓职员向本刊透露,去年根据“上面的精神”,到2005年底之前,北京的医院要“卖掉”100家,上海“卖掉”一半,全国其他城市保留一两家公立医院,其他全部改制。
因此,《意见》一直备受业界和媒体关注。有媒体曾在去年底预计,随着《意见》在2005年初颁布实施,2005年将是医院改革的元年,也将是医院投资热年。一盘财富大餐将随之上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春天”将随之降临。
大量社会资本也闻风而动。据2005年初的报道,当时有至少百亿的民间资本和外资在伺机介入医院改制。北京双全集团、香港长江国宝医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医疗系统集团、北京盈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国内外大型公司均被传出有数亿元资金准备投资医院行业。一位业内人士解释道:“虽然卫生部的医疗体制改革政策还没有明朗,但要等一切都确定了的时候,投资机会可能也就没有了。”
与此同时,众多医院也向社会资本抛出了绣球。双方的蠢蠢欲动,带动了医疗投资行业的发展。北京一家著名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当时表示,每天都有1—3家医院院长找到他们寻求合作,而且数字还在逐渐增大。
“让医改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位投资界人士曾兴奋地说。
但是时至今日,关注《意见》的各路人士望穿秋水,它却千呼万唤不出台。尽管按常理,《意见》应该正在国务院法治办排队,但也有消息灵通人士表示,《意见》可能已经流产。
蔡仁华教授告诉本刊,据他所知,现在的《意见》里并没有此前流传的“国退民进”之类国有医院产权改革的内容,而是涉及对国有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据透露,《意见》将逐步取消国有医院“以药补医”的机制,为医院提供财政补偿。而《意见》迟迟不出台,也是因为对补偿资金谁来出资和监管,政府部门之间意见尚存分歧。
如果按此说法,即使《意见》仍将出台,也已经改弦易辙,此前纷纷扰扰的国有医院民营化的《意见》,实质上已经胎死腹中。
官员表态的悄然转舵
其实从卫生部官员的发言里,人们已经嗅到了变化的气息。
去年,政府高层的有关讲话所传达的精神,还都对国有医院产权改革表示支持。去年4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称,在政府增加基本医疗服务投入的同时,中国将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促进多种所有制医疗机构有序竞争;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医疗事业,将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而在有关政策出台后,国家将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试点。高强的讲话被认为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全国医疗体制将会有震荡性的动作。
在2004年8月举行的21世纪医学国际论坛上,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透露,国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的鼓励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形成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私立医院、股份制医院等多种所有制医院并存,公平有序竞争的医疗服务格局。业内人士分析说,朱庆生大致描绘出了未来中国医疗体制变动的轮廓。
但是临近年底,传说中的《意见》迟迟未公布,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刘新明司长却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产权改革不是下一步城市医疗改革的核心内容,也不是主要内容。”
刘司长的此次发言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蠢蠢欲动的民间资本还在企盼《意见》的出台,期待大举进军医疗服务市场的“春天”来临。
然而直至2005年夏天,《意见》仍未露面,此时卫生部的态度已悄然转舵。6月20日,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全国医院与医药企业峰会上指出,当前医疗服务市场上出现的“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而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次刘新明司长和高强部长的讲话,被认为是卫生部正式站出来否认“市场化道路”。卫生部关于国有医院的改革思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中国医师协会的肖主任同意拐弯的说法,他告诉《商务周刊》,和去年主张绝大部分都卖相反,现在卫生部的态度是,公立医院原则上一律不能卖,公立医院产权改革的事情暂时搁置,不讨论。
与此同时,7月5日,卫生部印发了《卫生监督稽查工作规范》和《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若干规定》,北京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周子君教授认为,近来卫生部接连的动作和表态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卫生部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将从产权层面转向卫生监管。
谁导致了《意见》的流产?
对于卫生部关于医改方针的转变,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和猜测。
蔡仁华教授表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的“郎顾之争”,可能是使得卫生部对医院产权改革更加慎重,采取了缓行、慎行处理方式的原因。
公立医院改制也同样遭遇着国企改制类似的“郎顾之争”。在轰轰烈烈的“郎顾之争”中,民意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郎咸平,今年春天,中央也对国有企业的MBO叫停,这可能都促使卫生部对公立医院的改制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
而且,医院改制比国企改制更复杂,它争议的焦点不仅仅是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还涉及公立医院作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政府的责任以及政府在改制后要不要退出、如何退出的问题。这些可能都是卫生部犹疑踯躅的原因。
2000年,江苏省宿迁市率先在全国开始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截至今日,宿迁135家医疗机构中,有133家医疗机构实施了改制。通过挂牌拍卖和协议转让的方式,全市所有的公立医院全部实现了“民投、民有、民办、民营”。宿迁医疗总资本中,民间资本已占绝大多数。宿迁这种做法,被一些媒体称为“宿迁卖光”。
宿迁的激进改制,引起了空前的争议与指责。职工的举报,患者的抱怨,媒体的争论,甚至引起了卫生部高层的关注。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公立医院“卖光”后,基本的医疗保障,包括救济医疗谁来提供?改制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妥善安置医院分流人员?
这样的争论,特别是医院职工的举报、停诊、上访,也屡屡发生在各地的医院改制过程中,2004年,杭州第四医院和杭州整形医院被作为杭州医改的试点进行股份制改制,两家医院的职工多次到杭州市政府甚至浙江省政府门前上访。
在地方医改过程中,基层的国有医院院长和医务工作者对医院产权改革大都表现出了抵触情绪和行为。对院长们来说,特别是三甲医院,因为享受政府拨款及与民营医院不平等竞争的垄断地位,很多医院营利状况不错,因此并不热衷于产权改革和吸收外来资金。改革后,这些优惠措施都将取消,医院可能与民营医院一起公平竞争,这显然不是院长们愿意看到的。
对医生来说,医院不再是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国家的优惠政策、财政投入和对个人最重要的福利都将取消,医生的身份也从国家干部变成打工者。而且和国企改革一样,众多医院改制中存在着国资流失的问题也直接引发了医生们的上访。
卫生系统基层对改制的抵触情绪自然会对高层的改革思路产生影响。而去年下半年,河南新郑中医院弃重病患者于荒野致使其冻死、北京新兴医院广告“神话”被媒体曝光等事件发生后,民间和舆论对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也开始出现诸多批评,这种批评比基层医院职工上访的杀伤力更大。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还指出,学者和国际机构对市场化道路的怀疑和否定,也使政府对市场化医改方案更为慎重。“特别很多有国际经验的专家学者,看到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在全球都行不通,他们的意见逐渐对卫生部产生了影响”。
王绍光教授本人就是市场论的反对者,他在2003年为反思非典撰写的《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一文中,通过大量数据和论证指出,“中国的卫生领域恐怕已经是全世界最市场化的之一”,而其导致的后果,是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绩效评估中,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
王绍光强调,市场化要明确两个概念,一个“finance”,医疗的钱由谁出,全球经验都表明,这部分绝对不能市场化;另一个概念是“delivery”,医疗由谁提供,是公立还是民营,营利还是非营利?每种模式在全球都有成功的经验。“后一个方面不是不可以市场化,但它不是改革的重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王绍光说。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肖庆伦教授,有着留美经历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李玲教授,都是一直反对国有医院产权改革而呼吁政府加强监管的代表人物。李玲教授在不同的场合强调:“希望依靠产权改革解决医疗领域出现的问题,是一种产权一试就灵的幻觉。”她在广东东莞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内的非营利性医院和营利性医院的经营业绩差别非常小,也就是说所有权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
李玲的声音一年前还被淹没在市场派的高调中,但现在卫生部官员的表态采取了几乎相同的表述方式。
王绍光还透露,作为卫生部政策咨询智囊的卫生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体制内的研究机构,也对中国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大量调研,大多数体制内专家们的意见也是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的。
就在今年的6月中旬,刘新明司长发表讲话前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这份长达158页的报告,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详细的论证,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除此之外,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多次在其与中国卫生部门合作的研究报告、由卫生部高官参加的高层会议中对中国的市场化医疗改革提出批评,建议政府加强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政策介入。
在此背景下,不仅是作为主管部门的卫生部,政府更高层决策者也重新思考医疗卫生这一重要的公共服务未来改革路径。据透露,温家宝总理去年下半年有过一个指示,大体意思是医疗体制改革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更加慎重。“这届政府强调以民为本,和谐社会,医疗系统的改革也必须遵循这个思路。”中国医师协会的那位官员说。
产权改革不再是医疗改革的重点,医疗监管被提上议事日程。北京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周子君教授认为,对于卫生部而言,可能不只是重此轻彼,先此后彼的问题,而是卫生部职能的转移。周子君教授大胆预测,医院产权改革的问题以后将不再归卫生部管。
周子君的依据是近日正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的一项试点。7月18日,海淀区公共服务委员会挂牌成立,海淀区卫生局下属的22家医疗机构的人、财、物,将在一个月内划归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
这个公共委的职能有点像国资委,辖区内承担公共服务职责的事业单位的人、财、物,将被统一纳入其麾下进行管理,卫生局、文化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将只负责宏观规划、行业准入和监管等职能,真正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
据周子君介绍,按照最新国家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试点,医院和其他事业单位一样,将逐步与行业脱钩,医院的下一步产权改革,将不再是卫生部的管辖范围。
“我个人认为,卫生部也不会再出台什么有关医院产权改革的《意见》了。”周说。
卫生体制改革的失败不是市场化的失败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
《商务周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刚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导向的医疗改革是不成功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判断?
李:卫生系统1980年代到现在的改革不成功是肯定的,但这种改革是不是市场化的?我认为不是。今天的医疗系统,是垄断下扭曲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今天出现的问题也不应该由市场来承担。
中国目前的医疗系统,90%以上还是公立医院,虽然从1980年代起,卫生部对医院让权放利,但这只不过是体制内的权力下移,不是一种本质性转变。国有医院目前还是政府的附属物,医疗系统也还是由政府垄断,民营资本和公益组织进入还有很多障碍,因此医疗系统还是个官僚垄断行业。但是国有医院中,又下放了经营权和药品定价权,医院、医生的收入与经营挂钩,在这样的经济利益激励下,很多医院和医生惟利是图。这样的医疗系统,既不像原来由国家提供医疗服务,又没有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准入机制,集中了两个体制的弊端。
《商务周刊》:那您认为政府和市场在医疗事业方面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各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政府不只要处理好和市场的关系,在我看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结构,政府、市场、个人和公共领域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政府的职责就是要管好自己,放开社会。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最基本的职责就是要为人民提供教育和医疗。政府的职责,一个是给钱,第二个是立规则。而现在政府没有尽职尽责,一方面钱没有给够,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1985年的39%,下降到2002年的15%左右。钱给得也不公正,10亿农民的合作医疗,政府才给了10个亿,去年北京一个大医院改建,一下子就拨款了18个亿。
政府也没有立好规则,该管的不管,凡是不好管的,政府为了减轻负担,权利下放医院,让医院自己挣钱,医生自己创收。而社会能解决的,不用政府管的,或者政府管不过来的,政府现在又管得太死,标准制定也不合理。
现在营利性医院出了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制定好规则,没有严格监管。还是那句话,一方面,不该管的管得太多,民营医院不能提供基本医疗保险,使得民营医院不能从事基本的医疗服务,转而以专治一些疑难杂症,比如肝炎、不孕不育等来吸引患者,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政府该管的又没管好,这些医院从事这样的经营活动是不是经过你卫生部门的批准,它们在电视上做虚假广告为什么没有人管?把现在出现的问题都归罪于市场是不公平的。
政府也没有放开公益性的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这样的国际组织一直想进来,但政府不开放,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和国外组织在国内开展活动,我们现在还都不允许。
民间个人之间的卫生互助和各种中医、草医,政府也管得太死,政策没有弹性。医疗现在的处境与教育很像,政府没有尽到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的职责,却不允许社会力量办民工子弟学校,说他们不合标准。农村缺医少药,政府医疗没有普及,却同时限制社会力量进入。政府制定政策规则的时候,能不能更有弹性?当西医力量不能覆盖全国的时候,你承认不承认没有统一标准的中医?当合格医疗不能覆盖农村,你承认不承认赤脚医生?或者护校出来的没有行医资格的医生?
政府要管住自己,放开社会,让社会多个部门、多个力量发挥作用,形成多方位、多层次的医疗系统。
《商务周刊》:政府应该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医疗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以后,会不会有损医疗公平性原则的体现?
李: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市场在哪里应用、政府又在哪里起作用的问题。
首先,作为政府的职责,我主张要建立城乡一体、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这种公平是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实现的,需要政府职能来保障。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给钱要给够、给公平。
在政府、患者、医疗机构这个三方关系里面,政府与患者之间是非市场的,政府和医疗机构之间、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却应该应用市场关系,患者可以挑选医疗机构,政府也不应该对由谁提供医疗服务做出限制。
只要政府为患者的医疗保险买单,不管是公立医院、民营医院还是公益组织,只要是合格医院,谁来提供医疗服务都是一样的,政府只要制定好规则,作好布局和监管工作就可以了。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对医疗机构的公正。
《商务周刊》:现在各地的医改都是地方政府自己在做,卫生部没有尽到统一协调的作用。
李:我曾经说过,社会可以是多元的,政府应该是统一的。但是现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各有利益,简直找不到统一的政府在哪里。
医疗体制改革牵涉到的不同政府部门,至少包括卫生部、财政部、劳动保障部、民政部,可能还包括发改委,医疗体制的改革当然还是要由政府主导,但这个政府可能不是卫生部,卫生部没有这个协调和领导能力,医疗改革必须要由国务院统一领导。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