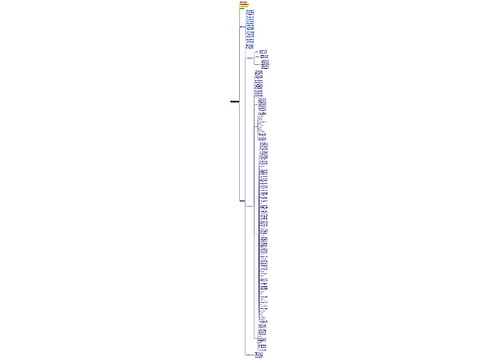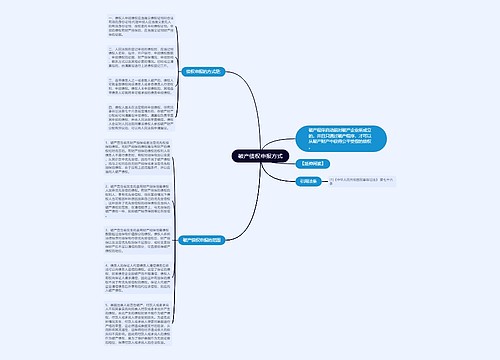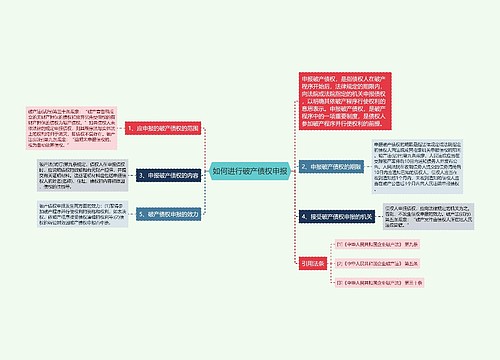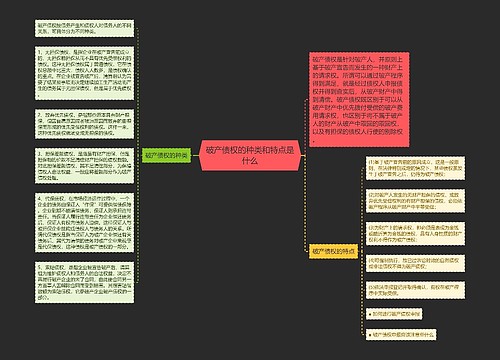侵权债权的顺序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是侵权之债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关系,二是侵权之债与其他民事债权的关系。关于前者,《侵权责任法》第4条以及数量众多的实体法都确立了个人财产优先用于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则。实际上,从破产法的角度看,这一问题还可以以更简便的立法技术解决。例如德国《破产法》第39条第1款第3项规定,刑事罚金与行政罚款债权及相应利息属后顺位债权,应后于普通债权受偿。若我国在破产法中借鉴此类规定(民事优先于行政与刑事责任),则《侵权责任法》(第4条)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便可被更有效地整合和替代,另外也能更清晰地表明,不仅侵权债权,而且合同债权也优先于罚金或行政罚款债权。确立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有以下几项原因。
第一,国家承受财产损失的能力远大于个人,当责任主体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刑事责任时,民事责任优先是弱者保护及社会化观念的体现。
第二,民事责任优先可以减少当事人交易前在核查交易对方是否存在违法或犯罪行为上的投入,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第三,民事责任主要目的在于补偿,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虽然以财产为媒介,但主要目的在于惩罚和威慑。前者指向债权人个人的权利,后者则着眼于社会安定和一般公众的利益,前者更为直接和迫切。
第四,民事责任优先虽然可能造成罚款、罚金等制裁难以实施,但不影响通过对责任人施加人身制裁,达到惩罚行为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第二层次的问题是侵权之债与其他民事债权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曾有所提及。对于法律应否优先保护侵权债权人(至少是人身侵权受害人),笔者持保留态度。
第一,必须要考虑到,债务人——或者确切说是债务人的股东——想从无调节能力的债权人处受益,只能设法通过破产“逃债”的办法进行,因为如果债务人不破产,并不能免掉偿债责任。但在失去自己的企业与破产免债之间进行权衡时,通常投入大量个人心血的股东并不会轻易地选择后者。
第二,债务人欲损害无调节能力债权人的利益,只能通过与有调节能力的债权人——主要是担保债权人——合谋进行。但对担保债权人而言,其在现行法下并不能无折扣、无迟延地实现其担保权,如美国与德国破产法中的诸多限制。这让潜在担保债权人很难参与合谋,进而债务人损害无调节能力债权人利益的可行性极大降低。
第三,从实证研究上看,债务人通过破产有意损害侵权债权人的情形是极少见的,即便将债务人的主观因素排除,侵权受害人因公司债务人破产而比合同债权人受更多损害的情形也是不多见的。
第四,即使论证所有侵权债权享有超级优先权一定程度上能成立的话,试图论证人身侵权受害人优先于担保债权人进而优先于财产侵权受害人也是很难的。毕竟财产也是人生存的基础,在价值上与身体、生命没有本质差异。如肖像、名誉等人格权受损害与作为必要生存条件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受损害相比,哪一个更具有保护的必要事实上很难确定。
第五,不考虑请求权竞合的情况,很多合同债权的标的,如劳动合同、供货合同、部分保险合同等都可能牵涉权利人的重大利益,其重要性不但强于一般财产侵权的受害人,甚至也强于人身侵权之受害人。
第六,现行法上基于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质,有时会对侵权债权乃至人身债权加以特别保护(如《海商法》第22条第1款第2项与第5项),但也主要着眼于物件本身的危险性和物件的价值而将责任的实现直接指向物件(实际上是由物件所有人承担以物件价值为限的有限责任)。相比而言,企业并不一般性地具有侵权的危险性,对其一般性地规定侵权债权优先缺乏充分理由。

 U633687664
U633687664
 U882667602
U882667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