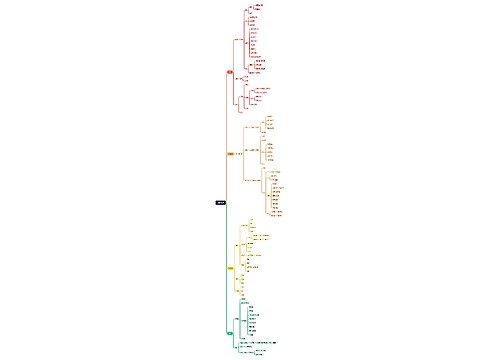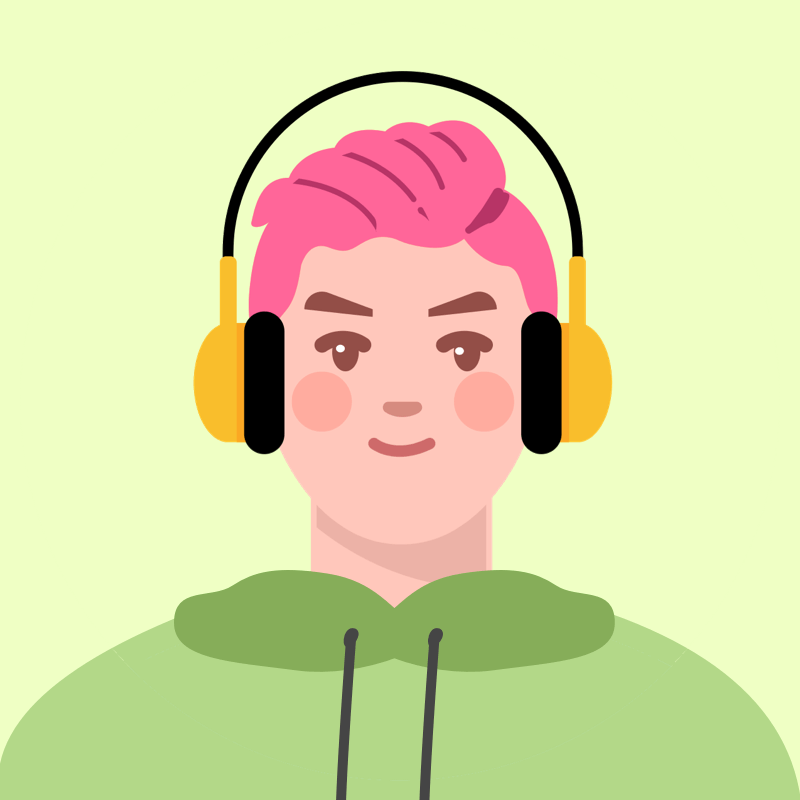由于案件在国内未被受理,2005年10月,部分包头空难罹难者家属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高等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A航空公司、B公司、通用电气均被列为被告。这家法院依据美国法律中的“长臂管辖”原则受理了此案。
在该法院审理过程中,三名被告要求调解,在法官的主持下,三被告在调解协议中愿意共同赔偿1175万美元。
而后,A航空以公司代理律师“越权”为由,拒绝承认这份调解协议,要求按“方便管辖原则”,中止审理此案,交由中国法院管辖。该法院支持了A航空的要求,转而以六个月一次的会议“关注此案”,直至诉讼在中国或美国法院得到解决。
而2007年11月,当郝俊波受32名遇难者家属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民事诉讼时,该院却拒绝接收诉讼材料,也没有给出任何书面答复。此后,郝俊波又向北京二中院申请立案,再次被拒绝。
去年6月,郝俊波转战上海,向上海一中院提起民事诉讼,也未得到受理,他不得不再次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
今年3月,案件终于出现转机,北京市二中院收下了起诉材料,并进行了立案登记。
早在2001年6月,“武汉6·22空难”一周年之际,25名遇难者家属向武汉市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武汉航空公司就空难中每位死者进行人身和精神共计100万的赔偿,武汉市中院亦未受理此案。
在得知包头空难民事诉讼案后,部分武汉空难遇难者家属曾找到郝俊波,他也爱莫能助。“包头空难与武汉空难不同,武汉空难是国产飞机,国内法院不受理,不能到国外提起诉讼。”郝俊波告诉记者。
国内外空难赔偿数额的巨大差异,成为遇难者家属质疑的焦点。
按照包头空难遇难者家属与三被告达成的未履行协议,三被告向32位原告共赔偿1175万美元,平均每位死者的赔偿金约合人民币300万元。
郝俊波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离谱的数额。“在美国空难中,平均每位家属获赔150万美元左右,而按照国132号令,每位家属最高获赔7万元,即使参照中国民航总局2006年颁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和最高法院200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空难受害人可以获得的死亡赔偿最多也不超过40万元。”他解释说。
这种最高限额的赔偿规则,造成遇难者家属找不到法律支持,处于被动接受的尴尬一方。在具体赔偿中,事故责任方拿着相关规定居于主导地位,且态度强硬。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郡高等法院的裁定中,中国A航空公司同意以下条款:东航将不会就原告在这些案件上提出的诉求在中国法院进行抗辩;东航将根据中国法律给予所有原告完整赔偿金,并放弃中国适用的任何关于赔偿金的限制、最高限度或封顶限度。
而在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事实上已经废除了空难赔偿限额的规定。
去年1月,郝俊波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公民建议书,建议将我国公民死亡赔偿标准从40万元的最高限额提高到最低300万元。
郝俊波介绍说,赔偿数额的提高,不仅关乎遇难者家属的利益,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而且是对事故责任方的一种惩罚。
这种惩罚性赔偿原则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还存在一定滞后现象。比如:按照最高法院的“限额解释”,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这种规定不仅产生了“同命不同价”的弊端,也对事故责任人形不成应有的法律威慑,违法成本低,导致事故多发。
让众多包头空难遇难者至今耿耿于怀的是,2006年底,国务院相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包头空难的调查处理结果:“这是一起责任事故,12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飞机起飞过程中,由于机翼污染使机翼失速临界迎角减小,机翼污染的最大可能是霜,飞机起飞前没有进行除霜,东航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领导和管理责任,在安全管理中存在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