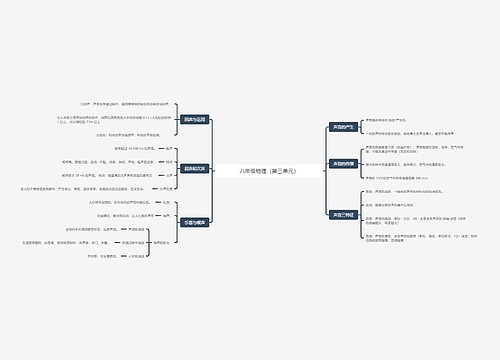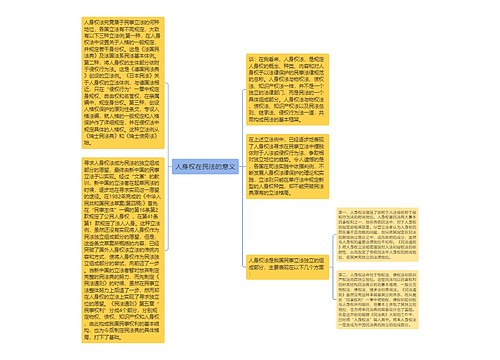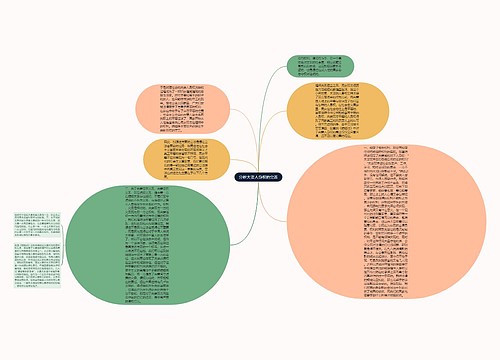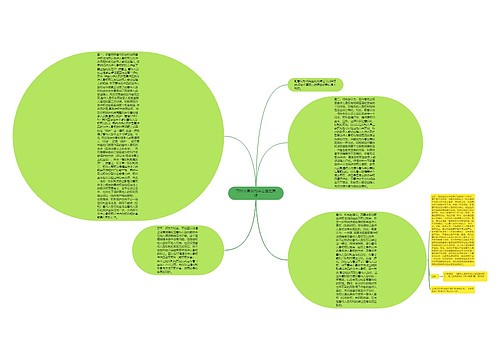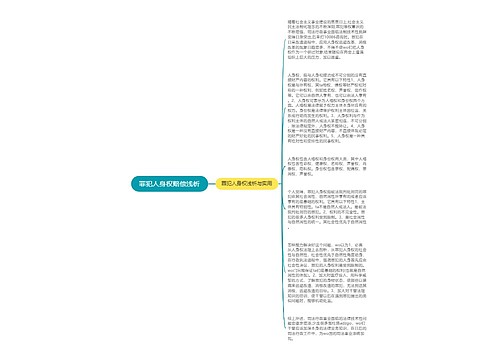林则徐是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他那个时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对所谓"夷情"的了解还是肤浅的。作为大清帝国的官员,他对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应予保障的意识还很薄弱,因此也就不会意识到地位比天朝子民更低的"夷人"对此会如此看重。因此,如果说林则徐的爱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度,那么时至今日,爱国需要超越林则徐的高度。爱国之义,首在建设国家使之富强。而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也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英国人正是从13世纪开始就慢慢确立起这两项权利,才有后来的民主政治和强盛国势。
可见在宪政法理体系中,公民的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乃是通向他们不可剥夺地具有立法、管理国家等等公共权利的基石;而宪政制度对于国民这些权利的保障,也是每个公民发挥自己的道德潜能的前提,所以“私法”与“公法”两大体系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撑的密切关联性,本身就是宪政最重要的内容和根本性的内在逻辑(注:所以康德把“公共正义”的内涵定义为“保护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133页);直到罗尔斯仍然强调,宪政对于国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乃是每个国民实现道德完善的基础:“立宪政体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将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这些道德能力,并随着他们这样做而使他们在整个生活过程中充分发展这些道德能力。”([美]约翰?罗尔斯著,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第215页)而与上述法理相反的,则是居身于权力专制性恶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下,人们就只能越来越普遍地通过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等践踏社会正义和蔑视社会道德的路径来维系、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而使社会发展完全悖逆于宪政和法治的方向,详见拙文:“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5期连载),“再论明代流氓文化与专制政体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 2期),“流氓政治与张铁生现象”(《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也正因为如此,宪政法理这种从国民私有财产权地位的确立进而通向公民社会公法体系的逻辑路径,恰恰就与中国皇权政体的法理逻辑(从规定子民们“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出发,进而确立大救星“统天御宇”、“广有四海”、“代天养民”等无限的普世威权),形成了鲜明对照。
总之,不论是从中国两千多年“蚁民社会”的法权形态及其发展方向,还是从罗马法 以来公民和宪政社会的法权形态及其发展方向来看,其实都不难明白“为什么宪政对公 民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如果将这两者加以对比,则问题的 结论就更加昭然无隐。当然,对上述结论更直接的印证决非“纸上得来”,因为这个问 题关系最为深切的,无疑还是我们今天现实中的制度选择。

 U981790431
U9817904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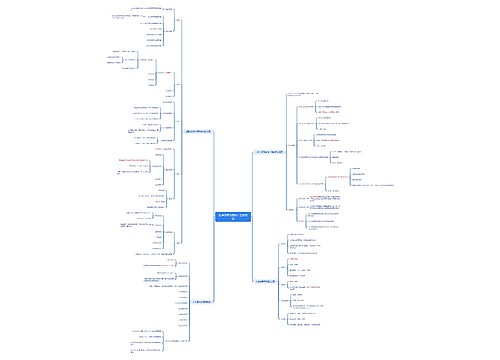
 U580391759
U580391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