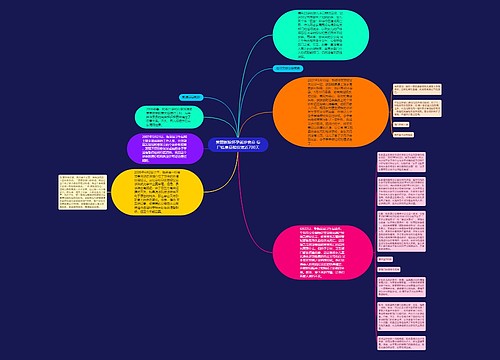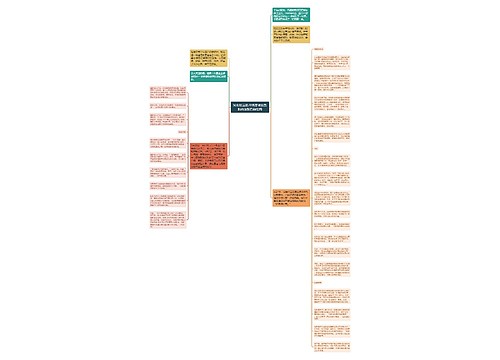2005年12月8日,范树水20岁的女儿患病到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被该院诊断为高度怀疑狼疮性肾炎。在医生的劝说下,范树水同意让女儿接受“免疫吸附治疗”。谁料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女儿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最后竟不治身亡。
范树水认为医院是在拿自己的女儿进行非法试验,为此他花了5年时间试图讨个说法。5年间,他得到越来越多的“有利证据”,并先后两次将上海市中山医院告上法庭,想要医院承认错误,但医院坚持认为其治疗不存在任何失误。
已经五年了,范树水至今都很后悔在《免疫吸附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他坚持认为,就是这种治疗导致了自己女儿范潇的死亡。
“女儿的主治医师吉俊对我说我女儿病情很严重,使用免疫球蛋白吸附器是目前最有效的疗法,而且只有中山医院有。”范树水对记者回忆说,当时,他用眼睛扫了扫《知情同意书》,看到“已经经过国家指定权威检测部门的医疗器械全性能检测,并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在国家药物临床基地开展产品注册的临床试验”字样时,他用了不到两秒的时间,就在纸的右下方签好了名字,日期是2005年12月8日。“孩子的病要紧,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况且这里是中山医院,全上海最大最好的医院。”
为了这当时不到两秒的举动,范树水花了近5年的时间试图讨一个说法。范树水的妻子袁雅(化名)称家里的柜子里塞满了各种打印装订好的医学材料与申诉材料,全出自于本来不会打字的范树水,家里用来写字的手写板已经用坏了3个。
2010年1月19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范树水起诉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范树水败诉。这并不是范家和中山医院的第一场官司,也并非范树水的首次败诉。2006年6月,范树水曾以医院在给范潇诊治过程中存在严重过失为诉由将中山医院告上了同一个法庭。
2010年2月2日,范家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0年2月19日,54岁的范树水在网络上发了一篇“寻找上海市中山医院非法试验受害者启事”的帖文。
尽管范树水称并不介意用真名,在接受采访的最后,他还是改变了主意,解释的说辞是:“对方是中山医院。”
2005年12月2日,范树水接到了女儿范潇的电话,范潇当时正在日本学习语言准备考当地的一所大学。电话里范潇告诉爸爸自己在体检中被查出患有急性肾炎,范树水让女儿第二天立即回国。
12月5日,范树水托人让女儿在离家不远的中山医院肾内科入院,很快她被诊断为高度怀疑狼疮性肾炎。“医生说这个病很严重,医生建议使用免疫吸附治疗法”,范树水说。12月8日,范树水在《免疫吸附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治疗费用一次一万元。“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相信医院。”
12月10日,范潇开始了第一次免疫吸附治疗。12月14日下午1点多,范潇按时开始了第三次治疗。然而这一次,一直到晚上7时许,范潇却还未从手术室里出来,这让范树水和妻子袁雅十分着急。后来他们得知,此次免疫吸附治疗被中途停止,范潇被送去透析抢救。此后,范潇再未被通知去参加免疫吸附治疗。2006年5月10日,范潇在其他医院病故。
在范树水的以上叙述中,袁雅也对记者提到,心里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女儿参加免疫吸附治疗前,都可以和我坐公交车去医院,但是第一次治疗之后,就不能行走了。我们当时以为是正常的副作用,也没有太在意。”
吸附疗法是指将患者的血液引出体外,经过吸附剂的吸附作用清除各种致病因子,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免疫吸附疗法是在血浆置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高新的血液净化疗法,主要用于治疗传统药物或手术方法难以奏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免疫介导性疾病。
痛失爱女的范树水夫妇对中山医院的医疗救治开始产生怀疑。2006年6月,他们将中山医院告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原告女儿的病入院时就很严重了,已经是晚期。在我们的治疗下,各项指标显示都有好转,但是最终也阻止不了病情的恶化。”上海中山医院医务处医务科副科长,同时也是外科医生的杨震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了一下,“我们中山医院是国家医院,带有公益性质,基本不拒收重症患者”。
立案后,徐汇区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市医学委员会对中山医院的医疗行为与范潇之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2006年9月18日,上海市医学委员会出具了鉴定报告:“免疫吸附为目前治疗狼疮性病变的可行方法之一,该治疗措施符合规范,整个诊疗过程无违反治疗原则。范潇所患病均属重症狼疮病变,其发病凶险,愈后差,本病例最终的不良后果是疾病自然转归的结果。结论为双方医疗争议不构成医疗事故。”
2006年12月14日,法院驳回了范树水、袁雅的诉讼请求。
范树水觉得这份鉴定报告只是在提及治疗的有效性,而回避了作为他四个诉求之一的“试验是否合法”。但范树水放弃了上诉。至今范树水也不知道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失误,“但当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范树水一脸无奈地说。
第一场官司开始的时候,少数知道此事的朋友曾经劝过袁雅。“他们说你不要打官司,越打官司越伤心。结果果然是这样。但是我一打开电脑,就会不自觉地去看药监局等等网站,想寻找各种医学信息,总觉得这些消息都是和我有关系的。”
范树水和袁雅称,2007年1月11日,他们意外接到了国家药监局的来电。这个电话让绝望中的范树水夫妇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
原来2006年11月22日,范树水曾就《免疫吸附治疗知情同意书》中涉及国药局的相关内容咨询投诉。“电话是一位自称姓郭的同志打来的,他说他们没有批准同意过开展免疫球蛋白吸附疗法这一临床试验。我听了一下子就激动了。我们请求国药局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文字回复函,他说他们是不能给个人出具回复文书的,如果法院提出申请就可以。他还说会来我们这里具体调查。”范树水称国药局调查的人最终没有来,当时自己也没有录音,但这个电话还是给了夫妻俩极大鼓舞。
2007年,范树水和退休在家的袁雅开始了更为频繁的证据搜索和撒网式的上访、电访以及信访活动。“医院医务处、国家药监局、卫生部、上海市卫生局和药监局、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法委,甚至公安局等等,只要我们想到的,都会去投诉。”袁雅说。
袁雅随后在网上查到了2005年3月16日国家卫生部发布的《关于加强“血液疗法管理”的通知》:“对于既无基础研究结论、又未经临床研究的‘血液疗法’,一律停止临床应用。”
范树水看到这条通知后几乎要跳了起来。女儿范潇接受“免疫吸附治疗”的时间为2005年12月。范树水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中山医院非法实验的重要证据。
2007年2月9日,上海市卫生局对范树水的信息公开申请给予了回复:“根据您提供的材料《免疫吸附治疗知情同意书》来看,其中涉及的免疫球蛋白吸附器目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未正式用于临床。”
在范树水看来,3月至8月与上海市药监局的约谈和信访最为曲折。他认为最后是自己拿出的卫生部的《关于加强“血液疗法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起了作用:“上海市药监局的王教授当时就不说话了。”
“免疫吸附疗法是一种很成熟的疗法,并且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其中就包括狼疮性肾炎。”中山医院医务处医务科副科长杨震很肯定地回复记者。
对此,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也对记者称:“血液吸附疗法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比较先进的方法,该技术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基本成熟,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属于合法的医疗行为,不违反诊疗规范,也不属于卫生部文件中所禁止的‘血液疗法’范畴。”
“向上海市药监局出具了卫生部的通知后不久,7月,我同学来找我了,我女儿入院时是我托他帮我找的关系。现在他同样成为了我和医院的中间人。他说医院想和我协商,我拒绝了。后来医院医务处的一个处长也给我打了电话,我也拒绝了。我说我要等药监局的信访回复,等一个说法。再后来上海市药监局的一位女士给我打了电话,她说今天正好中山医院、卫生局的人都在这,问我要不要过来一起协商一下。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显然不是‘正好’的巧合。”范树水的“明白”是当时上海市药监局作出信访回复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我还是拒绝了,我坚持要求上海市药监局给我出具书面回复。”
2007年8月15日,上海市药监局给范树水出具了信访处理意见书。在意见书中,药监局表示:依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该临床试验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由宁波菲拉尔医疗用品厂提供的,NO准040825230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州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以下简称广州医疗质检中心)检测报告系伪造。广州医疗质检中心于2004年12月29日才出具了宁波该厂送检的合格检测报告。二、医院临床试验基地存档的,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临床试验方案未按照规定格式要求签署伦理委员会意见、承担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意见、实施者意见,临床试验负责人未签字,不符合“局令第5号”的规定。
而这份有问题的检测报告,在2006年的诉讼中,由被告中山医院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院。
面对眼前的回复,范树水一时间“悲喜交加”:“悲愤”的是上海市药监局仍然回避了他一直想要寻求的“试验是否合法”的问题;“欣喜”的是他觉得上海市药监局还是给他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为了进一步巩固已有的证据,范树水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了信访事项复查。“我的本意其实就是核实,增强上海市药监局信访回复的可信度。”上海市政府在2007年11月29日的复查意见书中,对市药监局的信访处理给予了维持。
“我们也是受害者。”中山医院医务科副科长杨震提及此段,觉得医院也有点委屈。“我们并不是恶意欺骗,我们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负责医疗器械的批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份检测报告是假的,因为有的审批文件我们只收到厂家给的复印件。”
当记者问及为何不要求他们出示原件时,杨震表示:“5年前的伦理委员会和当时大环境一样,都在逐步完善中。之前收的复印件也没出现过这么不诚信的现象。”杨震继而又说:“而且,当时这吸附疗法已经非常成熟,所谓的临床试验,只是因为器械换了生产厂家,就要经历这样一个必经的程序阶段。”
“坦白说,当时厂家提前伪造了检测报告,确实是想多挣点钱。”杨震说,“现在因为这件事,他们也不再生产这种器械了。我们虽然不愿为此让医院声誉受损,但是这是我们的失误,我们就承认并改正”。
而在《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局令第5号”令)里,范树水发现另外一条内容: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费用。
对于免疫吸附疗法一万元一次的费用,杨震认为,这些费用都在病人参加治疗前提前告知。“临床试验收不收费还是得看情况,我们这个是国内器械,收费已经不高了,国外这类器械的治疗费用是好几倍。”
2009年,在第二次起诉中山医院开庭前,范树水“如法炮制”地给浙江省药监局也递交了上海市药监局的信访回复,申请对宁波市菲拉尔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在免疫球蛋白吸附器临床试验中伪造检测报告进行核查。
2009年4月21日,浙江省药监局给予了回复。其中第二条内容为:“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应符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但目前,国家局并未对该产品的临床试验进行审批。”
2008年,认为自己掌握了新证据的范树水和袁雅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在法院审查期间,中山医院亦提供了一份上海药监局于2007年9月7日作出的关于“免疫球蛋白吸附器”临床试验核查情况的书函,证明其辩称意见。
2008年11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范树水、袁雅的再审申请,认为证据尚无法证明被告医疗行为与患者范潇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杨震再次坚称医院对范潇的治疗绝对不存在任何失误:“如果真像原告所说,他女儿因我们的治疗导致病情恶化,其实哪怕有那么一小点点我们的治疗失误,医学鉴定会里那么多专家不可能看不出来。”
范树水觉得中级人民法院给了他另一个思路:将诉由可以转为合同违约。第二次起诉这次,范树水决定自己来打这场官司。
2010年1月19日第二次起诉的一审判决认定:中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复的“免疫性蛋白吸附器”临床试验负责人也未签字,违反了《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上海市药监局已责令菲拉尔厂和中山医院改正。由于原告以违约向被告主张民事赔偿权利,举证责任在原告,而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对免疫蛋白吸附器临床试验中存在的问题是否与患者范潇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我不是医生,如何能去证明因果呢?”范树水觉得很憋屈。事后总结自身教训时,袁雅觉得不是律师出身的范树水对于庭审技巧和相关程序的掌握还不够老到;而范树水亦承认自己奔波五年虽然搜集了诸多证据,但其实并不清楚在庭审中该如何有力使用。
“试验是否为非法试验,是该案的关键。”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在查阅了该案判决书及相关材料证据后认为,范树水收集的证据中,浙江省药监局关于该吸附器的信访回复应该是本案的关键性证据。
“‘目前,国家局并未对该产品的临床试验进行审批’——浙江省药监局的这一答复足以证明该试验就是非法人体试验。因此双方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卓小勤对此表示。
“第二个证明试验非法、合同无效的关键点在于,本案未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即进行临床试验属于违法行为。根据《赫尔辛基宣言》规定,临床试验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审批,因此被告医院构成缔约过失。”卓小勤认为,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医院的行为构成缔约过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医院医疗行为与范潇死亡的因果关系,如果该疗法被认定为非法人体试验,而本案被告未告知有其他合格的产品可供选择,剥夺了病人对医疗器械产品技术的选择权,使病人失去选择正规和成熟技术产品治疗的机会,已经构成了对病人的欺诈和缔约过失。因此,应当由被告医院负责举证。”卓小勤表示。
面对记者关于“临床试验准入证书”的询问,中山医院医务科副科长杨震解释道:“这个包含一系列的文件,比如企业资质等等,检测报告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件。”杨震指着2010年判决书上的检测报告内容部分说,“这是药品监督管理局广州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报告,就是你问的《免疫吸附治疗知情同意书》中,‘并经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同意在国家药物临床基地开展产品注册的临床试验’部分”。
“即便当时我仔细看了那份《知情同意书》,我还是会签字的,女儿的命要紧,我不相信医生还能相信谁呢?”范树水说。
“医患关系是知识、权利上不对称的关系,因此医生应该多多关注病人这一弱势群体,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少医疗机构利用这种不对称欺骗、剥削病人的现象。”邱仁宗对记者表示。78岁的邱仁宗是首位获得联合国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奖的中国人,他被公认为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界的泰斗”。
但作为医务处的工作人员,杨震认为医院对此事的处理一直很积极、公开。他否认了范树水对记者所说的,“第一次起诉中范家愿意调解,但被医院拒绝”的说法。
“我们第一次得知他们起诉后,由医务处和科研处领导挂帅,专门解决此事。我们不止一次地联系他们,哪怕周六周日,只要他们有时间,我们都表示可以坐下来好好协商。虽然不是我们的过错,但是我们也了解家属的心情,我们尊重合法、合理的权益。”杨震如是说。
面对记者采访,范树水的心情很矛盾:“这个事情我觉得恶意性其实很大,但是我不想把事情弄大,我们还要在这个区生活的;可是我真的很想替我的女儿尽一点心意。医院只要认错,哪怕只有一块钱的赔偿也好。”只是这事在杨震看来,却绝非一块钱那么简单。“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像之前那么强硬了,比较含糊。”

 U633687664
U633687664
 U482683014
U48268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