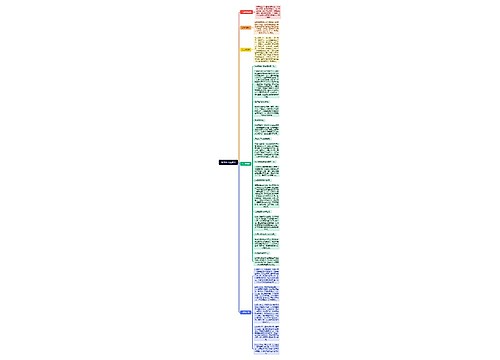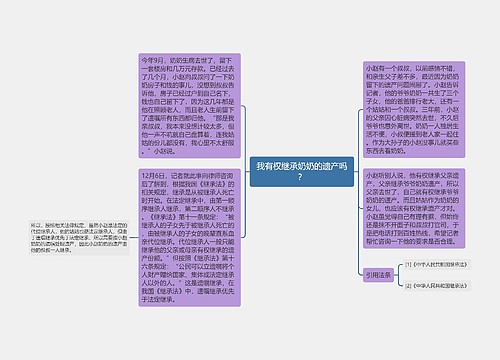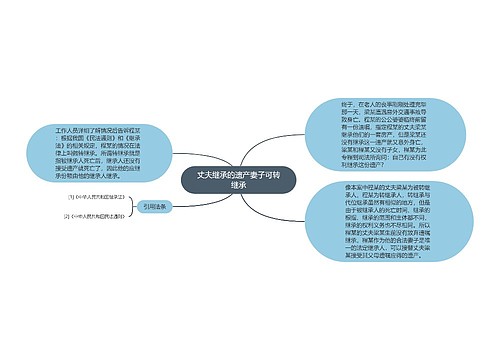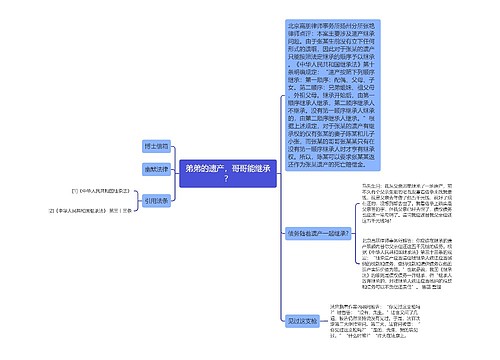在严独鹤图书馆落成仪式上,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新闻学会会长、《新民晚报》原总编辑丁法章详细介绍了严独鹤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和杰出贡献,并首次提出了我们要研究严独鹤、继承和发扬严独鹤先生留下的那份丰富文化遗产的问题,他希望大学的新闻专业研究人员能研究严独鹤的办报思想和做人的精神。许多同志翻阅了《严独鹤杂感录》一书后深有感慨,大家说,独鹤先生当年主持《新闻报.快活林》副刊时,笔耕甚勤,其文虽短小精桿,但关注国计民生,体现了社会责任感,仅从1945年12月起,到1948年就12月就收集到他的随感800多篇,而本书所收的400多篇文章,可以称得上篇篇精彩,有不少文章今天读来仍使人富有启发或引发共鸣。无疑,这样一位杰出的老一代新闻工作者,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我知道严独鹤先生其人,是上世纪60年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候,但真正对严先生有所了解,则是1986年11月开始与严祖佑在《新闻报》同事之时,那时,我们俩共同主持《新闻报》副刊“社会服务”版。1998年我重返《新闻报》后,我与祖佑先生除各自主管一个部门外,又共同主编了副刊“快活林”(以他为主),在工作接触之余,我对他父亲独鹤先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史、对海派文化的贡献开始有所了解和认识。
严独鹤先生祖籍乌镇,这是出过大文学家茅盾的江南小镇,该镇还出了著名文学家、出版家、教育家孔另境(茅盾先生妻弟)、主持中共一大会务的李达夫人王会梧等名人。严先生诞生于1889年,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槟芳馆主,年轻时曾在上海担任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英文编辑,自1914年起进入《新闻报》任副刊主笔,1931年起任该报副总编兼副刊“快活林”(后更名为“新园林”)主编,又兼《新闻夜报》总编辑,1950年后始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直至1968年逝世。他还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上海一至五届市大代表、《解放日报》顾问、作协上海分会理事等。
严独鹤先生对上海新闻事业和海派文化发展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新园林)”上。郑逸梅曾在《记严独鹤》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上海报坛上,有所谓“一鹃一鹤”之誉,鹃是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周瘦鹃,鹤则是指严独鹤。他说,独鹤先生在“快活林”上每日发表“谈话”一篇,影响很大,外界几乎把他当作是《新闻报》代表人物,乃不知尚有总编辑、总经理矣。他在“快活林”上的“谈话”(即杂感),读者能读得入迷,甚至有一读者为其文痴爱而欲谋杀他。其杂感之魅力,与此可见一斑。
独鹤先生对新闻事业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办报纸的副刊上,他力主副刊需有灵魂思想,要有文化品位,但又主张副刊要“杂”,各类文章都要发,以满足各种读者的需求。他更主张副刊的休闲性,吸引读者的兴趣,为此,他坚持报纸副刊上组织、发表市民性的连载通俗小说,当年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侠凤奇缘》、《并头莲》、《荒江女侠》、《啼笑因缘》等都出自于他主编的《新闻报.快活林》,《啼笑因缘》(张恨水著)至今仍是电视、戏剧的题材。独鹤先生办副刊的新闻观,我认为很值得今天的新闻工作者研究和继承。还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大学新闻专业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只重视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党报党刊的研究(这无疑是对的,应是主流),但对这期间民间报刊尤其是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大公报》等的办报思想和理念研究很不充分,甚至《上海新闻史》这样的大著也对严独鹤的贡献“忽略了”,这是明显的不足,是割断了历史,当然是有历史原因的。现在,我们对这一份新闻遗产的继承和发扬,要不要提上议事日程?要不要总结研究?这值得大家思考。我希望从大学新闻专业(尤其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先做起来,将来能出《申报》、《新闻报》甚至严独鹤新闻思想的研究专家或博士、硕士。
严独鹤先生不仅能编报纸,而且多才多艺,他14岁时曾中过秀才,懂外文,还写过长篇小说《人海梦》、出版有《严独鹤小说集》等,他曾是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鸳鸯蝴蝶派”主将之一,他的文学作品,至今仍出版、研究甚少。他主持“快活林”“新园林”长达30多年,其杂感“谈活”数量巨大,今天出版的《严独鹤杂感录》,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主张有关方面能从海派文化的研究、发扬出发,系统地整理出版严独鹤的小说和谈话杂感,在此基础上编辑严独鹤文集或全集,这对上海的文化建设,未始不是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情,连同研究严独鹤的新闻观和办报思想,都应由上海来做,不应推给他的家乡桐乡市或乌镇。

 U237990653
U23799065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