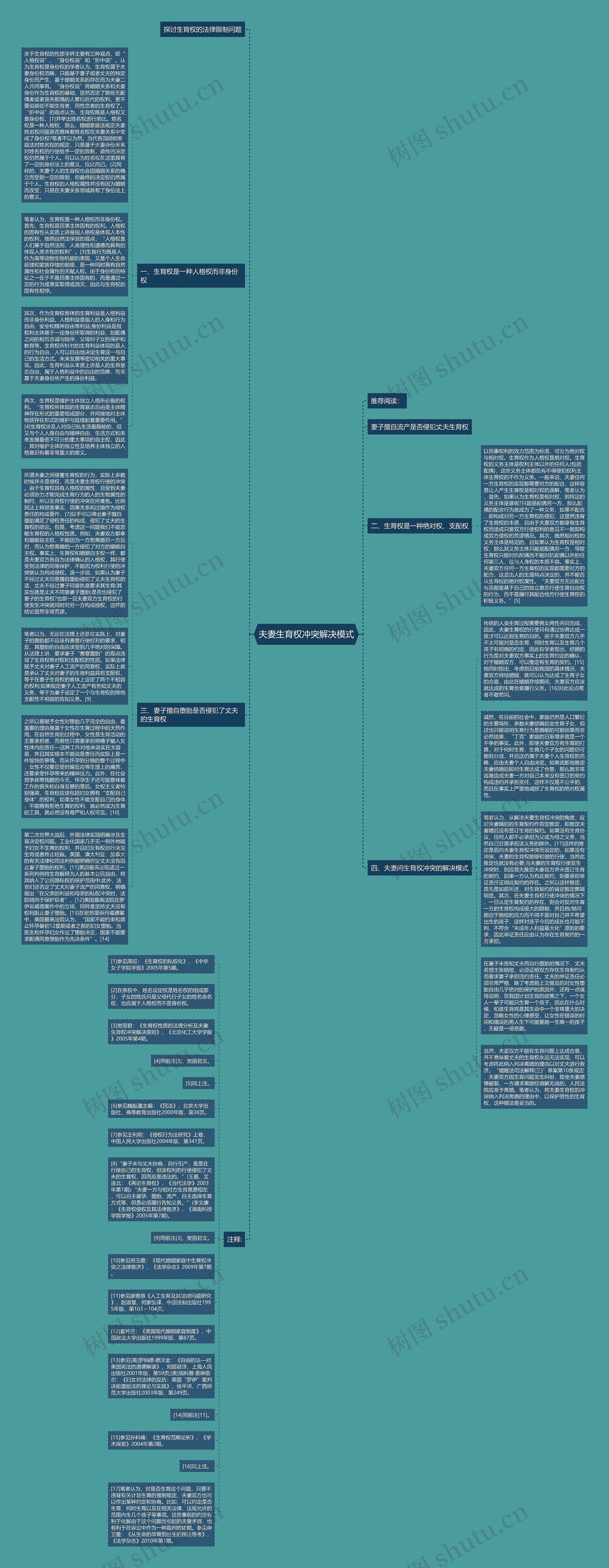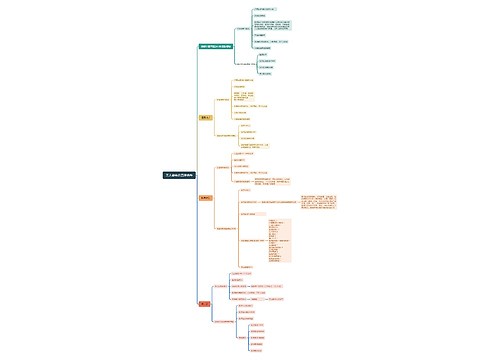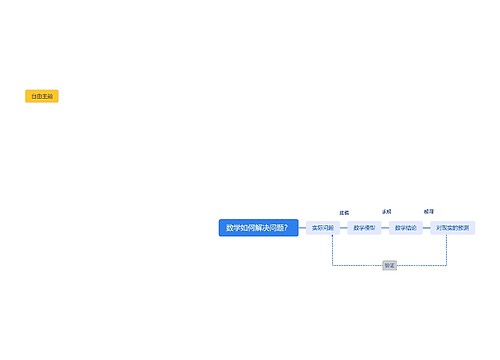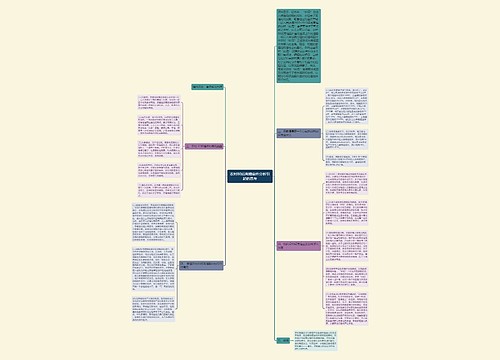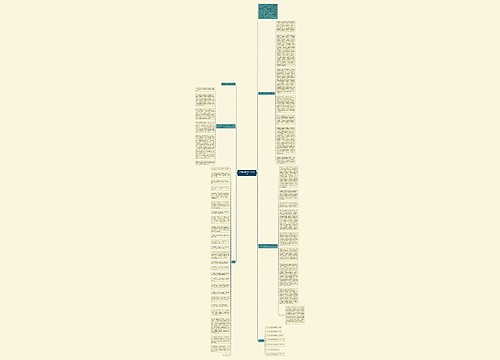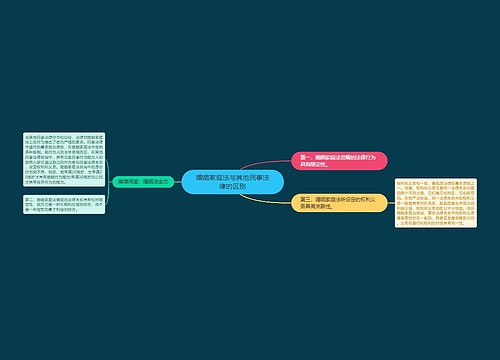[1]参见周征:《生育权的私权化》,《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在亲权中,姓名设定权是姓名权的组成部分,子女的姓氏只是父母代行子女的姓名命名权,也应属于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
[3]樊丽君:《生育权性质的法理分析及夫妻生育权冲突解决原则》,《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7]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
[8]“妻子未与丈夫协商,自行引产,虽是在行使自己的生育权,但该权利的行使侵犯了丈夫的生育权,因而应是违法的。”(王晨、艾连北:《再论生育权》,《当代法学》2003年第1期);“夫妻一方与相对方生育意愿相左,可以自主避孕、堕胎、流产,自主选择生育方式等,但是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李文康:《生育权侵权及其法律救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10]参见邢玉霞:《现代婚姻家庭中生育权冲突之法律救济》,《法学杂志》2009年第7期。
[11]参见廖雅慈《人工生育及其法律问题研究》,赵淑慧、何家弘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
[12]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3]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美]瑞科雅·索琳歌尔:《妇女对法律的反抗:美国“罗伊”案判决前堕胎法的理论与实践》,徐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15]参见孙科峰:《生育权范畴论析》,《学术探索》2004年第2期。
[17]笔者认为,对是否生育这个问题,只要不违背有关计划生育的强制规定,夫妻双方也可以作出某种约定和协商。比如,可以约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生几个孩子等事项。这些事前的约定有利于化解由于这个问题而引起的夫妻矛盾,也有利于在诉讼中作为一种裁判的依据。参见申卫星:《从生命的孕育到出生的民法思考》,《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