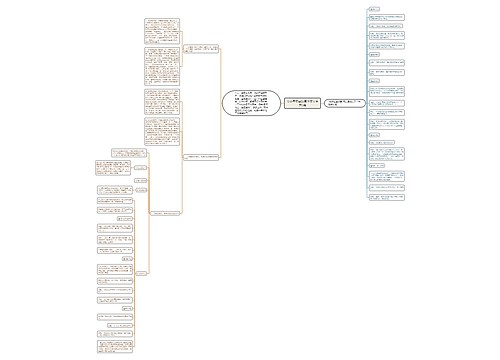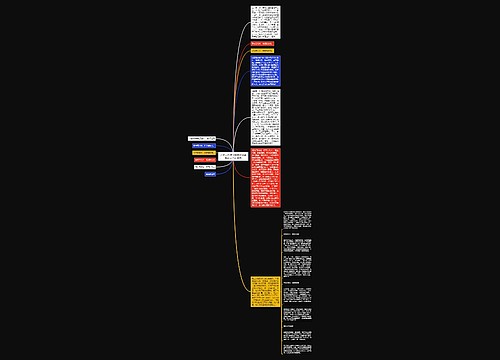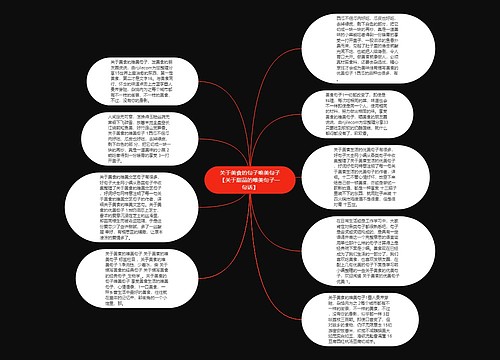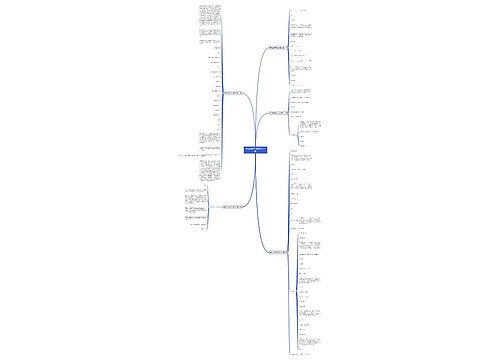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通用9篇思维导图
撩你成瘾
2023-05-09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通用9篇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一篇每当我快要放弃时,我就会想到朋友跟我说的一句话:“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你放弃,你就一点机会也没有。”记得小学五年级时,我的英语成绩非常差。因为基础不好,上课时都听不懂,所以一到上英语课我的心思就飞进了幻想的世界里。直到有一次月考,英语只考了25分。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通用9篇》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通用9篇》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8af8c0e8c3817910017f346c846fd5e8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通用9篇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一篇
每当我快要放弃时,我就会想到朋友跟我说的一句话:"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你放弃,你就一点机会也没有。"
记得小学五年级时,我的英语成绩非常差。因为基础不好,上课时都听不懂,所以一到上英语课我的心思就飞进了幻想的世界里。直到有一次月考,英语只考了25分。当看到试卷时,我伤心地想:就算基础不好,但至少也能及格!这次竟然只有25分。
想到爸妈发怒的'脸,我害怕起来,所以把试卷藏了起来。虽然没被爸妈发现,但我就是高兴不起来,好几天都没认真听课。那张英语试卷上红色的大叉叉和"25"这个数字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
小学时的朋友一直都很了解我的成绩情况,看到我那几天无精打采的样子,就来找我。我以为她来找我玩,所以找了个借口,说:"我不舒服,不想出去玩了。"本来以为她会走的,可是她并没有走。她说:"你以为这样你的英语成绩就能好了吗?这样只会让其他科的成绩和英语一样。"我虽然听见了,但是我并没有说话,只是无奈地想:不然要怎么样?还像以前一样不听英语吗?她好像看出我的心思似的,说:"如果你想学好,就不能只听你喜欢的课,不喜欢的,听不懂的也都要听。那次只是个月考,离期中考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你如果不想再考那么低,就好好努力。"可我却有气无力地回答:"我从三年级就没认真听过英语课,要补也要从三年级的开始补。那么多,还有机会吗?"她却回答,"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你放弃了,你就一点机会也没有!"说完就走了。听了她的话,我茅塞顿开。
利用双休日的时间,我上了一个英语补习班。上课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白老师讲的题目和英语课文,而其他科目也没因为补习英语而被落下。终于在期中考试时我的英语成绩过了80分。
我始终都没忘记朋友的那句话:"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你放弃了,你就一点机会也没有。"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二篇
也许现在有许多孩子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喜欢把什么话都藏着掖着,不告诉父母。这样就形成了一道天然隔膜,产生了代沟。
对父母对我的好,有时心里很感动,很想当面感谢她,看到她辛苦地为我做饭、炒菜的身影,看到丝丝皱纹爬满额头,看到她佝偻着身体时……一种莫名的心酸在心头。我很想对她说:别弄这么多,简单点就好了。不要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我曾经试着向母亲说出那三个字,但是失败了。回想着那一次来到母亲面前,迟疑了半天,还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脸憋得红红的,一个人杵在那里足足愣了一分钟,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母亲好像觉察到什么,就询问一下。我惊慌地跑到室外,面对空旷的地方,我深呼一口气,把压抑内心的闷气全都排解出来。我倚着墙壁,仰望天空。难道说出那三个字真的那么难吗?
小时候,母亲不劳辛苦地哺育我们,嘘寒问暖,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留给我们。长大后,成为了学生,为了成全自己的攀比心理,大把的花着父母的血汗钱,只懂自己的快乐,不懂父母的辛酸,看不见父母的辛劳。又反思过多少,体谅过多少?我们在父母眼里是孩子,可以把所有负担都留给父母,追求所谓的个性,用大把的金钱消磨时光,用大把的时间浪费生命,不知父母的生活是何等的单调。但他们从未抱怨,因为他们有目标,他们的目标就是你啊!你啊,就是一个傻子,被父爱、母爱重重包围,被友情、亲情重重包围,居然还说感受不到爱!那是因为你从未真正地去感受。
醒醒吧!同学们,向父母说出自己最真挚的心声,说出父母最感动的话语,让我们付诸行动,说出:"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三篇
陈诗荣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曾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最近,"内卷"成为舆论场上的热词。这一概念在年轻人中广为流传,屡次出圈,引发重重讨论。"内卷"的热度,不仅是学生的一种自我调侃,也是学生面对学业及自我发展的众多压力的真实写照。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精密仪器系的硕士贺如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竞争本就存在,想往高处走就势必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光说无济于事,不如多花点时间泡图书馆。"想往高处走,确实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与努力。但在如今,"往高处走"就等同于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成为"博士",成了年轻人心里唯一追求的目标,从而出现了"内卷",形成了无意义、无价值的内耗。"内卷"消耗时光,消耗生命。难道人生的意义只有考上名校吗?只有成为"博士"吗?难道除了名校与博士,我们就一无是处了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干点别的吗?
那么,在这个盛世时代下的青年,应该如何去避免所谓的"内卷化"呢?
我们应该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价值目标,拥有更清晰、更明确的自我规划,要有独立的思想。这么一说并不是逃避社会竞争,而是为了让我们避免盲目、不必要的跟风行为,不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或许在很多时候,只有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名利双收,才称得上"有出息",于是人们把目光集中到一处,在"内卷"中拼尽自己的青春年华,耗尽自己的全部精力。但是,那样的做法却失去了拼搏原本的含义,最终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收获,也褪去了青春该有的色彩。
我们应该时刻充盈自己的内心,开拓自己的视野,充实自己的思想。记得曾经在校运会上老师的鼓励:"输赢并不重要,重在参与。"事实确实如此,等我们的内心足够强大,我们就不会把"赢"当作唯一的价值,唯一的追求。生活亦是如此。在这个"内卷"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迎风成长。
这是最好的时代吗?是,也不是。但我们仍可以与之共舞,去面对、探索、抗衡、冲破、呐喊,永远不要停止逐梦的脚步。
这句话,常常响彻在我心头。我常让这句话提醒、勉励着自己。发展的赛道会随时"天降正义",机会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愿每个目标坚定的自己,在未来都能无惧"内卷",自信昂扬,与时代共舞!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四篇
这些天,天气很不稳定。坐在窗前,看着湛蓝透亮的天空,真让我不得不怀疑刚才的一场大雨不过是梦一场。想到梦,又不得不让我想起那个曾经像梦一样从我人生的旅途中消逝的那个女孩。
她比我大几岁,所以我总是追着她叫她小姐姐。有一年,她得病了,大人们告诉我,她得的是癌症,好不了了。懵懂无知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癌症,一直坚定地相信着她一定会好起来。
我去医院看她了。她有着吹弹可破的白皙的皮肤,红润欲滴的樱唇,浓密乌黑的长发,可我见到她时,她苍白的病态让皮肤不再白里透红,而是透着一种可怕的僵白,红艳的嘴唇覆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白纱,头发似乎变得稀疏泛黄。她安静地坐在病床上,像一个破碎的娃娃,双眼空洞地望着窗外,似乎在想着什么。那一刻,我害怕她就像梦一样从我眼前慢慢透明,然后消失。我急忙跑到她跟前,揪着她的衣袖,问她:"小姐姐,你病了好久了,都不能来看我,所以我就来看你了呢!"她笑着抚摸我的头发,说道:"那真是谢谢你了。"我又接着问:"姐姐,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对不对?"我睁大双眼期待着她的回答。她愣了愣,转瞬坚定地回答道:"对!一定会好起来的!"。那一刻,她眼中闪着像梦一样坚定的光芒。
她接受治疗,不停地吃着药,也不停地忍受着病痛带来的折磨,但无论有多痛,她始终坚强地忍着。可最后,她还是走了。
她只比我大几岁,却无法像那时的我一样,无忧无虑。她就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什么也没有留给我,唯一教会我的就是她的坚强。
多少年过去了,我忘掉了她的声音,忘记了她的名字,忘却了许多有关她的东西。她就像梦一样消逝在我的人生里,但我仍旧记得她那双闪着坚强光芒的眼睛。
若真有天国,若她能听见,向她说一句发自内心的问候:"小姐姐,你还好吗?"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五篇
每当我孤单寂寞之时,总是有你相伴,带我遨游诗词的海洋,每当我失败气馁之时,总是你鼓励我坚持。有句话总想对你说:文学,我受你。
是你,让我足不出户就带领我周游天下,领略美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塞北的荒凉悲壮。"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是江南的缠绵情思。"飞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瀑布飞学泻的壮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山巅之上的豪迈。浏览了祖国河山,总有句话在心头:文学,我爱你。
是你,让我身临其境般感受到了古人们的复杂情感。"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这是李白将内心的豪放情感发泄了出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是杜甫的亡国之痛。"人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李清照对人生的感慨。"了确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生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是辛弃疾对因年老不能抗金的悲伤。是你,文学,引领我一步步走进古代文人墨客的心里,亲身感悟文学的魅力,我爱你。
是你,使我获得了不少对人生的感悟。"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这是在教我分别时不悲伤,有朋友的地方到处都是温暖的家。"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能用自己的不足而哭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教会我们大自然新陈代谢的道理,亲人总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所以要坦然面对。是你,使我感悟,让我成长,让我更能坦然面对人生。我想说:我爱你。
感谢你,带领我饱览祖国风光,感谢你,让我亲身体会古人的意境,感谢你,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理。有句话儿在心头,我想对你说:文学,我爱你。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六篇
当微风轻轻拂过我的脸颊,当夕阳洒下最后一缕余辉,当河水荡漾起一波波的涟漪。有句话儿在我的心头,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在一个个枯黄的树叶缓缓飘落之后,又迎来一个寒冷的冬天。
那是一个零下五、六度的大雪天。
外面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争着抢着投入大地的怀抱,到处是一片银装素裹,雪姑娘把这一切打扮得十分美丽。北风呼呼地吹着,人们艰难地顶着伞抗着飞舞的雪花,一边跑,时时还得跺跺脚,好一个冷酷极品天气!
起床上学的闹钟响了,不得已的我慢腾腾地爬起来,走进爷爷的房间,发现爷爷不见了,心想,这么个坏天气,怎么爷爷不在家给我做早饭呢?我继续梳头打扮,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十分熟悉的车铃声,走近阳台朝外望去,原来是爷爷的车从外面给我买早饭回来了,我尽速下楼来到车库。
还没走到门口,便闻到一股十足的牛肉面条香味。再看看这天,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只见爷爷的雨衣和衣服的部分部位,被大雪打得湿透透的,晶莹的雪花沾在爷爷的脸上,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白胡子"爷爷。
以前我的爷爷最怕过冬天了,一般都起不来,但自从我上了学后,爷爷就改掉了这一坏习惯,再冷都会很早起床给我准备早饭,送我上学。我的眼眶不知闪过多少次泪花,那是被感动的眼泪。
天上依然下着大雪,面对如此恶劣的天气,我对爷爷说:"今天你就不要送我了,我一个人坐公交去学校。"爷爷哪里放得下心,果断地对我说:"大雪天,公交难等,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快,把雨衣穿上,路上还没结冰,我们还是骑车去,上车!"
电动车在大雪中艰难地开着,那熟悉的铃声又一次传入我的耳中,终于到学校了,我下了车转过身来,对着你笑,说了句"爷爷,有你真好!"
这是一次难忘的记忆,我永远不会忘。
有句话儿在心头,"有你,真好!"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七篇
胡雨洁
放学后,校门外人潮涌动。
家长们有的挥动着手上的小红旗;有的双手围在嘴边呈喇叭状高呼着;有的踮起脚尖呼唤着孩子的乳名,热闹极了。我远远看到爷爷站在离我最近的消火栓旁,高昂着头,在人群中一遍遍搜索我的身影。"爷爷,我在这呢!"四目相对的瞬间,皱纹也随即在他脸上绽出花来;我像迷路的小鹿找到归途,跑着跳着让书包里的笔在文具盒中撞得叮当作响。
我背上顿觉一轻,爷爷拽着书包肩带往后一甩,在空中描绘了一条优美弧线的书包稳稳当当地挂在他背上,"咱走啦!"说着牵起我的手。当时只觉爷爷的手指格外粗大,暖暖的,只是手心上铁锈一般的根深蒂固的茧子硌得慌,几次想挣脱,却被爷爷像保护宝物一样握得紧紧的。
"哇,是橘子!"爷爷从口袋里变出两个黃澄澄的橘子来,果叶未完全摘去,顽皮地在风中一下一下地点着头,格外可爱。剥去尚留余温的橘皮,必先举到爷爷嘴边。爷爷只是掰下一瓣放到口中,边吃边享受地点着头:"好甜的橘子!"那时候,爷爷的瞳孔里倒映的是橘子的金黄,还有举着橘子的我,亮亮的,如金黄色般热烈、明丽。
这一定是世界上最甜的橘子。
那一年,我8岁,他已过六旬。
后来,长大了些,我早已能独自上下学。爷爷总不放心,总会在我放学时倚在阳台上看着我走完这不到一百米的距离。起风时,风总会抚平他的鬓角,隐隐的显现出几缕花白;总会抚平他脸上的沟壑,挤出更多的欢喜;下雨时,雨帘从他眼前排排垂下,他的视线总能穿过数百万条的雨丝而后落在我撑的小小的雨伞上。
一年四季,爷爷一直在那里,杵着手,读晨曦,品落日,感微风,听雨声。他会冲我挥手,我便调皮地压低伞檐不看他;他会对我微笑,我便故意低下头摆弄手指玩;他会打开嗓门催促我快些回家,我便偏要慢下步伐……那一年,我豆蔻,他年近古稀。
许久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了。爷爷突然兴起说要来接我。我只应下,策划着如何越过爷爷偷偷溜回家,现实是不允许的。因为他总站在离校门口最近的地方,也总能丝毫不错地揪住我的书包,随即往肩上背。
"长这么大还被爷爷牵着手,还让爷爷背书包多羞啊!"转眼爷爷已快我几步走在前头,他时不时抬抬肩膀,许是书包太重了,显得有些不协调,脚下还是大步流星。
远远地,爷爷弯瘦的脊梁挤进人群中。在人高马壮的壮年家长群里,我的爷爷原来如此矮小;在肩上能扛动孩子的家长旁,我的爷爷只能抬起我的书包。我未曾发现他早已两鬓斑白,步履早已不甚轻快。寒风凛冽,我张了张嘴,希望把这风儿吹得温柔些,再温柔些,只吹起他的衣角,好让我的爷爷能走得更加稳健些、从容些。溢满眼眶的泪水,被风抹去,早已不见踪影。我飞奔上去,时间仿佛回到几年前,我又牵起爷爷的手……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余光中如是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永远不会放开你的手,因为与你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平凡而隽永。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八篇
林海鑫
又是云淡风轻,找出一本旧书,轻翻扉页。有那么一行墨字——书香氤氲、如蔓、如藤,缠于我心头生长。
忆起五年前住在外公家的时光,内心总是涌起一片暖意,印象中,外公对我和弟弟很严,对外人却反常的平和。外公白日里晒谷米,不免有鸟雀来啄食,他竟也不恼,只是偶尔吆喝几声罢了,而我也目睹过邻居如怀深仇大恨般地将偷吃的鸟雀毒害,便愈发产生一种对外公的敬意;外公还常常爱种些花草,倘使邻居的小孩跑来打闹,就是把初开的花儿碰掉了不少,外公也是只一皱眉头,嘱咐那些孩子要小心些。如此一来外公的院子便成了鸟雀与孩童的乐园。
那天记得是刚放暑假不久,我又被送到外公家。老师要求要阅读一本课外书作为假期学习任务,外公便踩着自行车载我到村外的书店买书。
那时是阴天,天气不热。自行车载着我穿梭于绿叶蝉鸣之间,外公穿着白衬衫,哼着曲儿,双脚伴着节拍上下踏动着。"过了前面的路口就要到了!"外公笑着说道。忽然间,另一辆自行车"唰"地便从一个小巷口里冲出,跳动摇晃着,如同一尾蛮横的慧星,狠狠朝外公的自行车撞来,外公一惊,身体一斜,我们便同车子倒在地上。那辆自行车也发出几声无助的车铃后,猛地向一旁躲避,结果侧翻滑到了路边去了。
外公将我搀起来,我们都没什么大恙,只是外公那雪白的衬衫如同丢进泥水中揉搓过一般,外公连车也不扶,赶忙撑地爬起,迈大有些蹒跚的步履,直奔路边,托住那个双眼呆滞的年轻人的双肩,将他一把扶起。他回过神来,面色通红,用几近哭腔的语气连连道歉,双手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七零八落的钱币要给外公赔偿,外公不肯要,硬生生塞回了他的衣袋,说道:"没事,下次再急也别开这么快了,危险!"外公搀着他坐到路边,又扶起他的车,将他散落的东西拾起交给年轻人,年轻抹着泪连连道谢。外公之后也不再提及此事了。隐约只记得他说过:"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斤斤计较。"
与外公离别时,他赠了我一盆黄花和那本当时买的书。花开花落,我将一朵凋落的黄花夹在书中一页,那上面写着的一句话——"贤者有剑,不斩蝼蚁。外公的话常常盘据我心头。
莫名地,我忆起了外公,只见窗边黄花依旧,清风正好。
这句话在心头儿作文800字 第九篇
经过一星期的苦闷生活,迎来了双休日。凌晨,太阳早已高高的挂在天空,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了房间。我从睡梦中渐渐苏醒,伸了一个懒腰,摆脱了困倦,伴随着托鞋在地上的磨擦声,我来到了妈妈的卧室。看见妈妈还在睡梦中,心存疑惑的想:今天不是约好一起去买乌龟吗,怎么还不起?我轻轻的把妈妈叫醒,妈妈带着困倦的眼神看着我,突然想起了约定的事,向我点了点头。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和老妈准备好要拿的东西就出发了。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新,我们一路上欢声笑语。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宠物店了。
到了地方,我兴高采烈地下了车,妈妈也随我一起进来了。各种各样的宠物在我眼前呈现,我和妈妈就花了十元钱买了两只乌龟。
就这样,乌龟进入了我的世界。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星期乌龟就生病了。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看见姐姐手里拿着一瓶药水在治疗生病的小乌龟。我漠不关心的问:"药水在哪买的,多少钱?"姐姐说:"就在那个店里,十块钱。"我看了一眼,说:"十块钱还不如再买两只乌龟。"只见姐姐放下手中的药瓶,意味深长地说:"生命无价!"我顿时愣了一下,不知该说什么,心里似乎从这四个字中明白了许多。
这一晃,一个冬天就过去了。星期六的那天,小乌龟离我而去了。它静静地趴在水池中,往日明亮的双眼也已经深陷下去了。我心痛万分的把它埋在小区一角。是它,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
从那以后,我懂得了生命的价值。"生命无价"那句话一直在我心中,我将永不忘记!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