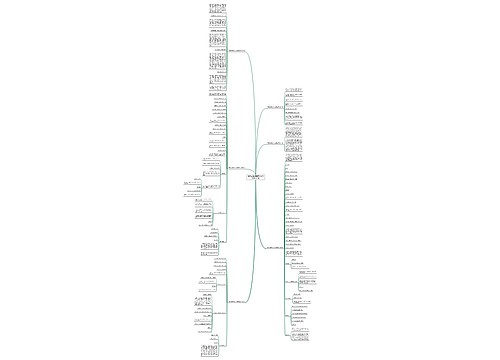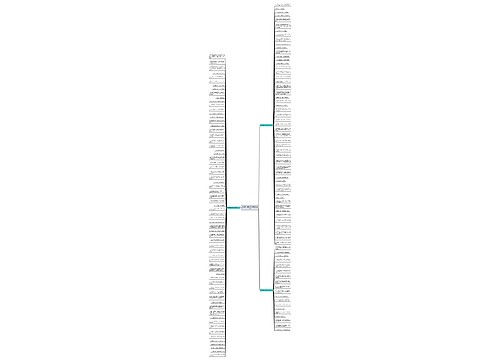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通用十篇)思维导图
迷人小天后
2023-05-06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通用十篇)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一)XX街道(社区):我叫XXX,男(女)XX年XX月出生。原系XXX公司职工,XX年XX月退休后移交到XX街道XX社区。XX年XX月患尿毒症,每周透析XX次,爱人、子女工作生活情况(略),由于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家庭生活因病致贫,现申请大病救助。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通用十篇)》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通用十篇)》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63f26ccb8f7873abff0fbade7ae409c0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通用十篇)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一)
XX街道(社区):
我叫XXX,男(女)XX年XX月出生。原系XXX公司职工,XX年XX月退休后移交到XX街道XX社区。XX年XX月患尿毒症,每周透析XX次,爱人、子女工作生活情况(略),由于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家庭生活因病致贫,现申请大病救助。
根据我县城乡医疗救助文件规定,低保对象可申请医疗救助。
一、救助标准为:按个人自付部分的30%给予救助。
二、申请和审批程序:
1、个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城乡医疗救助申请表》,并提供本人户口,身份证及相关证件,并提交医院正式医疗收费收据,疾病证明等相关资料;
2、送交居委会评议;
3、街道办审核;
4、县民政部门审批。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教师,亲爱的同学们:
我叫xx,是xx大学人文管理学院20xx级学生。20xx年寒假期间,我因患上了可怕的尿毒症被迫停学。经过肾移植手术和2年多的住院治疗,病情已经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今年新学期开学之际,我又回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我要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因为这是我的梦想和期望。
我能够回到大学继续我的学业,首先要感谢校领导的鼓励和帮忙。学校领导十分关心我的病情,百忙当中,校党委书记张金钟教授捐款1000元,并写了慰问信,校长张伯礼院士捐款2000元,鼓励我树立与病魔做斗争的信心,早日恢复身体健康。我还要感谢相识和不相识的教师、同学及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在得知我不幸罹患尿毒症的消息后,中大的教师和同学们在向我表示慰问的同时,也表达了要求捐助的强烈愿望。20xx年3月7日,捐款活动首先在我所在的班级----人文管理学院20xx级公共事业管理班展开,仅一个课间的时间就募得善款近8000元。3月8日,在人文管理学院的统一组织下,向全校师生发出了"请伸出你的援手,让生命在爱中延续"的爱心捐款倡议,随即在学校东院、南院、北院开展了全校规模的募捐活动,很快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响应,纷纷解囊相助,并向我表达各自的良好祝愿。开展募捐仅一周的时间,即募集到善款50000余元。与此同时,一部分同学还自发组织到超市、商场募捐。爱心无止境,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募捐活动结束后,许多教师和同学多次追加捐款,许多爱心人士经过《每日新报》、新浪微博等途径了解到我的病情后,主动地联系到我或我的'同学,奉献爱心。至我在医院做肾移植手术时已经得到爱心捐款80000多元。
有一句歌词唱的好: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爱的世界。这爱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爱让我真的很感动: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大学生,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当被查出患上尿毒症急需手术来挽救生命时;当因其家庭贫寒,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而一愁莫展时,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爱心人士给了我生的期望——第二次生命的期望。我是不幸的,在人生最灿烂的时候却与病魔羁绊前行;但我又是幸运的,因为有人间大爱在伴我同行。这爱不仅仅在物质上帮忙了我,更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与病魔斗争的勇气,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这爱使我战胜了病魔,再次回到学校,回到教师和同学们身边!我必须不会虚度光阴,不会辜负父母、领导、教师和同学对我的期望,我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继续完成我的大学生活!我要把这份爱变成将来对祖国、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再一次多谢你们!真心的多谢你们!感谢你们的爱心捐助和鼓励,是你们,给了我重新拥有生命和完美人生的期望!
写信人:
日期: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快乐的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在大多数人眼中,大学生是青春洋溢的、充满朝气的,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然而,就在我们快乐地工作、愉快地学习,享受这一切美好生活的时候,就在我们身边,有两位同学正在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尽管如此,他们仍用顽强的意志和病魔斗争,用他们单薄的个体力量同命运抗争。
他们其中一位是动物科学系宠物13-1班学生魏青杰,河南省项城市位集乡人,家中五口人,父母,长姐和弟弟。父母务农,长姐在吉林上大学,弟弟在新疆上大学。母亲有腰伤,刚做过手术,不能干农活。长姐在____年元旦时查出肝病。魏青杰同学____年10月22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被确诊为尿毒症后,家庭重担全落在父亲一人肩上。如今,魏青杰确诊尿毒症,让这个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父母怕她心理压力过大,一直对她隐瞒病情,因家庭困难,目前已经转院到老家医院继续透析治疗,一周透析三次,透析非常痛苦,而且还有休克的危险,处于尿毒症晚期的她,亟待做肾移植手术。动科系的全体师生纷纷向她献出爱心,已捐款16000余元。
园艺园林系花卉12-1班李垒同学是平顶山叶县常村乡下枣园村人,今年暑假期间被检查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经过在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已经具备骨髓移植的条件,且和其哥哥的骨髓配型已经成功,并于11月份转入河南省肿瘤医院等待骨髓移植。由于家在农村,祖母已80多岁,父亲20多年前下岗后因身体不好一直未找到稳定的工作,仅靠当小学教师的母亲每月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原本就非常贫困的家庭在高额的医疗费用下已经是举债累累、无力承担了,目前仅在肿瘤医院无菌室每天的费用达4000余元。无情的病魔,加上巨额的费用,几乎是瞬间让这个虽然贫困但原本充满希望的家庭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园艺园林系全体师生于____年9月13日举行了募捐活动,共捐得爱心款元,并及时送到了医院,但与骨髓移植所需的几十万费用相差甚远。
老师们、同学们,咱们就这么忍心看着他们走向另一个不知是否存在的空间吗?为此,党委宣传部、院团委向全院师生倡议:少买一件衣服、少吃一次零食,甚至少喝一瓶饮料,献出每个人的一份爱心,让这两个不幸的家庭感受到一份温暖!伸伸手,让我们大家一起帮助他们击碎这层命运的薄冰,共同拉他们一把!让我们为同学点盏爱心灯,为友情牵根丝线,为生命搭建座希望的桥梁!
用我们的爱,我们的心,点亮一盏盏希望的灯,为他们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生命如此珍贵,人生仅有一次,当我们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享受生命乐趣的时候,在连云港有一位青年人正在与尿毒症进行殊死搏斗!他叫张甫荣,毕业于镇江粮校8921班,今年38岁,正是有所作为奋发图强为家为国有更大贡献的年龄。
据医生介绍,肾移植是根治尿毒症最有效的办法,但光肾移植这一项就需要费用30万元左右,后续治疗费用也比较昂贵,巨额的医疗费使他的家庭不堪重负,蒙上层层阴影,也使他在精神上造成了巨大压力!从他母亲从他亲人憔悴而逐渐苍老的脸上就能看出病魔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万般痛楚与无奈!
也许您与他素不相识,但爱是没有界限的!希望您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帮这位青年人吧!也许这些捐款对您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是这些积少成多的爱心,就能换回他同我们一样阳光的笑容,换回他同我们一样健康的身体,让他同我们一样接受未来生命中的挑战和收获。
请献出一份爱心,成全一份勇敢的支持,传递一份生命的热度!毕竟,有你我真诚的帮助,风雨之后的张甫荣必定会再次扬起生命的风帆,一路前行,一路高歌!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帮助也许很微小,可是团结就是力量,也许我们这次募捐就是张甫荣再次生命的起点!
xxx
20xx年xx月xx日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五)
尹筱琪,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三年前的她有着同龄孩子一样的爱发小脾气,爱闹,不太讲理,但是由于家庭的变故,她变了,变得有主见,有想法,有孝心。
三年前,她的妈妈被诊断为尿毒症,三年的时间,为了给妈妈治病,家庭的经济条件一年不如一年。而年仅七岁的她,也想要有自己心爱的玩具,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和漂亮的衣服。但懂事孝顺的她,自从她妈妈生病以来,她很少主动提出要买东西!她知道妈妈的病需要很多钱,她想自己把省下的钱给妈妈治病!如果实在需要,很想买的东西,她会问爸爸我想买这个可以吗?而不是我要买这个。妈妈是个尿毒症患者,有很多需要注意的。而她基本上都能记住,有时候她会回家问妈妈今天吃药了吗?今天喝了多少水?今天吃什么东西了?今天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脚疼吗,我给你捶捶……就像一个大人问孩子的语气了。
她在一天天长大,她学会了很多。爸妈做饭的时她会主动帮忙洗菜,爸妈洗衣服的时她会把小件的拿到自己的身边洗,也会自觉地把地扫干净拖干净,会把放在床上的衣服叠好放到衣柜里……她就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女孩,她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孝道……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六)
我记忆中的王先生是什么时候存在的?不记得了。
你读过他的多少篇文章?这个好像早就忘了。
我不知道他的话有什么吸引力。我只知道,受他影响后,我开始把他的书从书店一本一本搬到我家。甚至连的《让生活去吧》和孙的《史铁生小姐》我都一一研究过。
我想这对我老公的残疾一定是沉重的打击——他之所以选择留在国内,是因为在清平湾插队时对当地风景的眷恋,错过了治疗。那一年,他才二十一岁,还是他一生中最狂妄的年纪。对他来说,残疾是梦想的毁灭。有一段时间他有自杀倾向,在朋友劝说下才选择留下。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他:
当他被认为是最傲慢的青年时,命运夺走了他的双腿;在他最颓废无助的岁月里,笔墨把未实现的梦想还给他。
但也许王先生的残疾足以改变他的生活:如果没有残疾,估计王先生这个时候就当英语老师或者翻译了,对地坛公园的生活也就没有什么想法了;如果没有残疾,估计患尿毒症的丈夫得不到读者作家协会的支持,也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来维持生活。
可能就这样吧。他用坚强的意志重新获得了生命——什么样的意志?从肾病到尿毒症,一周三次,每次四个半小时,很清楚。经过1000多次针灸,他的动脉和静脉已经变成了蚯蚓状,但他仍然在业余时间以职业生病和写作自娱自乐,最终用破碎的身体表达出最完美、最丰满的理想。
那么,我呢?如果他命运多舛,我会怎么推断?在这种幸福的环境下,我不应该为自己感到难过。!我只是在孤独中没有被发现和理解。如果我能像一个绅士一样放空自己,放下这些,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信仰,我怎么能真正的因信仰而孤独呢?
既然王先生已经走了,死者安息吧!珍爱生命!
我应该做的是不要学我老公的豁达。我应该做的是坚持自己拥有的不被别人理解的东西?
我觉得。对,对!我应该放下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继续向着梦想的彼岸奋进!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七)
设计(报告)题目 1例尿毒症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护理
设计(报告)题目来源 自 选
设计(报告)题目类型 临床研究
(内科护理) 开题时间 20xx年8月30日
一、 设计(报告)研究意义
该病例是本人在实习期间亲自护理的患者。该病是尿毒症最常见的并发症,病情复杂,病死率较高,患者出血呕血、贫血、头晕乏力等症状,是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和相应临床表现的综合征。
该患者临床治疗多以通过血液透析清除血液中的代谢废物、纠正电解质和酸碱失衡,清除体内多余水份和药物止血治疗为主,同时配合氧疗、改善呼吸状况、心理护理、饮食护理,等实施有效的综合护理措施,高质量有效的护理对改善患者的上消化道出血、贫血休克状况,有效抢救生命和转危为安至关重要。
本课题(报告)研究对减轻患者痛苦、促进舒适,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和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
二、 设计(报告)主要研究的内容、预期目标
(一)主要内容
1、尿毒症合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临床护理干预方法与效果观察。
2、氧疗与药物止血治疗等综合护理措施对提高尿毒症合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二)预期目标
针对患者具体病情给予氧疗、药物止血治疗、病情观察、生活护理及心理护理等综合性护理干预,促进患者舒适、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进一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三、 设计(报告)的研究重点及难点
(一)研究重点
尿毒症合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临床护理干预方法与效果观察。
(二)研究难点
输氧的操作方法与注意事项。
四、设计(报告)研究步骤(进度安排)
起止时间 阶段内容
① 20xx年7月~8月 选题与科研设计(含报告开题)
③ 20xx年1月~2月 报告写作、完成初稿
④ 20xx年3月~4月 反复修改后定稿、打印装订报告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八)
贪玩调皮,本应是13岁少年的特质,而命运却没有给文龙这样的机会。没有父亲的相伴,他每天扫地、做饭,照顾患有脊椎裂和尿毒症的妈妈。面对生活的艰难,从不抱怨。他说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要让妈妈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3岁,正是一个男孩贪玩儿好动、顽皮叛逆的年龄,可在赵文龙脸上,这些特质都没有,很多时候他都在默默地沉思。不在校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陪着妈妈去医院透析。虽然只有13岁,赵文龙几乎会做所有家常菜。因为妈妈患有脊椎裂和尿毒症,这么多年,他几乎从未有过玩耍时间,最大的乐趣就是生日那天去趟八一公园;他是包钢八中一名普通的初一学生,而他每天需要承担的却是一般学生父母双倍的责任。
来到位于少先路31号街坊的赵文龙家,家里几乎没什么电器,只有卧室里摆放的一台老式冰箱,这是为了给李英存放药品用的。李英正在整理医院的收费单,与妈妈的大床相隔一张桌子的小床是赵文龙的,床头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几本书,虽然陈设简单,家里却收拾得一尘不染。李英说,每天早上,即使时间紧张,龙龙也会收拾完家,给她做好早饭再走,他自己则在学校买早点吃。
虽然家庭负担如此沉重,可赵文龙在同学和老师的眼中却是天真、开朗、幽默的,只要学校有什么开心事,龙龙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妈妈,母子俩总会开怀大笑。在这样的说笑中,龙龙常常因为忘记了正在烧菜而把锅烧糊。
医生告诉李英,她的病目前无法治愈,最基本的维系就是一个星期三次透析,每次需要700元左右,每个月8000多元。为了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李英只得一个星期透析一次,每次透析,文龙都像丢了魂似的守在抢救室门口,李英每次都觉得心疼。但只要看她转危为安,赵文龙还挂着泪珠的脸上马上会露出笑容,他告诉她:"妈妈,您一定要好好活着,只要您陪着我,再苦的日子都是甜的。"
赵文龙打算考一所自己心仪的军校,当军人是他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国家还会补贴学费。"省下一分钱,妈妈的病就有一分治愈的可能"听着儿子这番言论,李英沉默了,生活让儿子过早地承担了太多的沉重,她除了支持,什么都帮不了他。每年六一,李英都会带龙龙去八一公园玩儿,有时龙龙会说:"妈妈,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将这里的游乐设施都玩儿一遍啊?"李英听了心里酸酸的,龙龙就立即转换话题安慰妈妈说:"等我工作挣钱了,咱们就好好出去玩儿一趟。"对于李英和龙龙来说,这样类似的对未来的期望已经成了他们母子俩的约定。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九)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生命如此珍贵,人生仅有一次,当我们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享受生命乐趣的时候,在连云港有一位青年人正在与尿毒症进行殊死搏斗!他叫xxx,毕业于镇江粮校8921班,今年38岁,正是有所作为奋发图强为家为国有更大贡献的年龄。
据医生介绍,肾移植是根治尿毒症最有效的办法,但光肾移植这一项就需要费用30万元左右,后续治疗费用也比较昂贵,巨额的医疗费使他的家庭不堪重负,蒙上层层阴影,也使他在精神上造成了巨大压力!从他母亲从他亲人憔悴而逐渐苍老的脸上就能看出病魔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万般痛楚与无奈!
也许您与他素不相识,但爱是没有界限的!希望您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帮这位青年人吧!也许这些捐款对您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是这些积少成多的爱心,就能换回他同我们一样阳光的笑容,换回他同我们一样健康的身体,让他同我们一样接受未来生命中的挑战和收获。
请献出一份爱心,成全一份勇敢的支持,传递一份生命的热度!毕竟,有你我真诚的帮助,风雨之后的张甫荣必定会再次扬起生命的风帆,一路前行,一路高歌!
尿毒症低保申请书范文(篇十)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我叫王继光,是天津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20xx级学生。20xx年寒假期间,我因患上了可怕的尿毒症被迫停学。经过肾移植手术和2年多的住院治疗,病情已经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今年新学期开学之际,我又回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我要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因为这是我的梦想和希望。
我能够回到大学继续我的学业,首先要感谢校领导的鼓励和帮助。学校领导非常关心我的病情,百忙当中,校党委书记张金钟教授捐款1000元,并写了慰问信,校长张伯礼院士捐款2000元,鼓励我树立与病魔做斗争的信心,早日恢复身体健康。我还要感谢相识和不相识的老师、同学及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在得知我不幸罹患尿毒症的消息后,中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向我表示慰问的同时,也表达了要求捐助的强烈愿望。20xx年3月7日,捐款活动首先在我所在的班级----人文管理学院20xx级公共事业管理班展开,仅一个课间的时间就募得善款近8000元。3月8日,在人文管理学院的统一组织下,向全校师生发出了"请伸出你的援手,让生命在爱中延续"的爱心捐款倡议,随即在学校东院、南院、北院开展了全校规模的募捐活动,很快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响应,纷纷解囊相助,并向我表达各自的良好祝愿。开展募捐仅一周的时间,即募集到善款50000余元。与此同时,一部分同学还自发组织到超市、商场募捐。爱心无止境,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募捐活动结束后,许多老师和同学多次追加捐款,许多爱心人士通过《每日新报》、新浪微博等途径了解到我的病情后,主动地联系到我或我的同学,奉献爱心。至我在医院做肾移植手术时已经得到爱心捐款80000多元。
有一句歌词唱的好: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爱的世界。这爱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爱让我真的很感动: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大学生,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当被查出患上尿毒症急需手术来挽救生命时;当因其家庭贫寒,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而一愁莫展时...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爱心人士给了我生的希望——第二次生命的希望。我是不幸的,在人生最灿烂的时候却与病魔羁绊前行;但我又是幸运的,因为有人间大爱在伴我同行。这爱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了我,更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与病魔斗争的勇气,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这爱使我战胜了病魔,再次回到学校,回到老师和同学们身边!我一定不会虚度光阴,不会辜负父母、领导、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期望,我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继续完成我的大学生活!我要把这份爱变成将来对祖国、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再一次谢谢你们!真心的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爱心捐助和鼓励,是你们,给了我重新拥有生命和美好人生的希望!
查看更多
《红星照耀中国》第十篇:战争与和平思维导图
 U279940135
U279940135树图思维导图提供《《红星照耀中国》第十篇:战争与和平思维导图》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红星照耀中国》第十篇:战争与和平思维导图》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29aaed1ec06a547207426b6c4dd49c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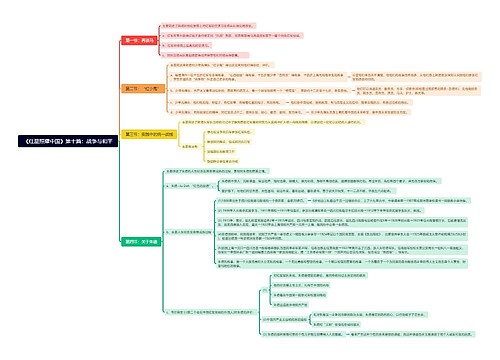
2.1桥梁结构形式与通用施工技术思维导图
 U466030502
U466030502树图思维导图提供《2.1桥梁结构形式与通用施工技术》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2.1桥梁结构形式与通用施工技术》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559daeffa921043afccd817fee2a5987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