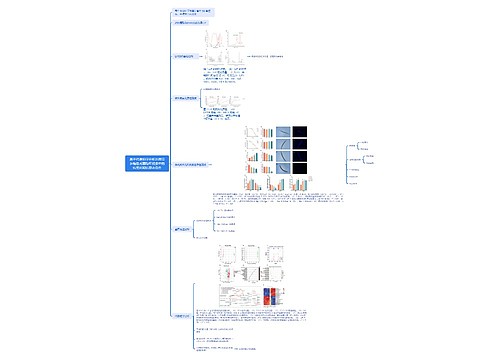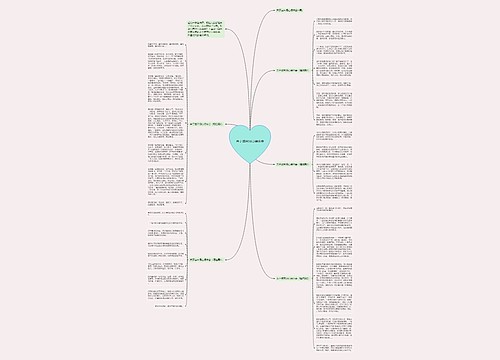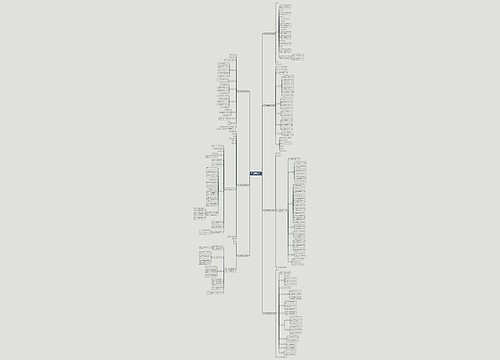那时,我刚刚接过初二年级的一个乱班。面对着如自由市场般杂乱不堪的课堂,面对着存心与我作对的学生,一向以性情温和自诩的我突然变得暴躁易怒。我几乎就已认定,我非栽在这帮学生手里不可。
因为经常伏案,我的一件红毛衣的肘部有了明显的磨损。大概在我写板书的时候,磨损的部位会更鲜明地呈现在学生们面前。
元旦快要到了,许多学生开始互送贺卡或小礼物。那一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扁扁的牛皮纸袋,袋子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撕开袋子,里面露出一副天蓝格子套袖。这时候,同教研组的老师也进来了。他看着我手中的东西,开玩笑说:"哟,谁送来的新年礼物?可惜颜色太难看,做工也粗糙。"我必须承认,它的颜色确实不好看,做工也不精细,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竟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副套袖,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它戴了起来,拿上教案,神气十足地朝教室走去。
走在去教学楼的路上,我想:不会错的!这一定是我班里的学生送的。可它究竟是谁送的呢?究竟是谁这么有心,给我送来了这样一份既实用又别致的礼物?
推开教室的门,迎接我的是一片波澜壮阔的笑声。我知道,大家是在为我的"红配蓝"而发笑。离上课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决定先做个调查。我说:"请大家不要笑。你们知道吗?这副套袖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新年礼物,只是,这个人没有留下姓名,我心里的感激之情不知该向谁去诉说。不过我十分清楚,送礼物的人一定在你们中间!我还知道,你们大都不会用缝纫机,这副套袖,很可能是你央求妈妈或奶奶、姥姥做的。就算你不愿意接受我的谢意,你总不该拒绝我对你的长辈的敬意吧?所以,请送套袖的同学举一下手,让我们从此成为知心朋友,好吗?"没有人举手。教室异常安静。大家看着我,静静地微笑。
从一副套袖开始,我和我的班级迎来了崭新的生活。那似乎是一件极有魔力的"镇班之宝",只要我戴着它出现在教室门口,大家顿时就会安静下来。50双宝石般的眼睛带着共守一个秘密的神圣感望向我。幸福的花儿,从我的心头开上眉头。我注视着每一个都有送套袖"嫌疑"的学生,心中泛起说不尽的怜爱与温情。
直到他们毕业,我也没能查出送套袖的人究竟是谁。那是一副耐用的套袖,我几乎四季都戴着它,但它美艳的蓝色硬是不退不减。在我看来,它是在以自己的某种坚守告诉我这样一个人生哲理:只要用爱去面对、用爱去求证、用爱去感染、用爱去消解,每一颗看似坚冰的心灵都可能融为春水。
多少年过去了,我那个班的学生不少人有了大出息。有时他们回学校看我,有的人我一时叫不上名字,但只要他(她)笑着说"幸福的套袖",我就会将他(她)拥进怀里,和他(她)重温一个让我们无比激动感怀的美丽故事。
台上,学生们正在演课本剧《茶馆》。我身边坐了一位特邀嘉宾——演"康六"的那个演员的母亲。她举着相机,不停地拍照。康六出场了,走投无路的他,要把十五岁的女儿康顺子卖给庞太监当老婆。当康六说"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我听到那个母亲开始叹气——旁若无人地大声叹气。我偷暼她一眼,只见她满脸的气恨,举着相机的手定定地停在空中,忘了拍照。康六再次出场时,台词是:"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么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弄不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演员演得非常投入,悲恸,羞愧,绝望……自扇嘴巴时,扇得啪啪作响。突然,我发现身边那个家长有些异样,侧脸看时,却见她满脸通红,满脸是泪。我轻轻握住她的手,示意她"平静",但是,她非但不能平静,反颤栗起来!我吓坏了,趁着第一幕落幕,拉着她离开了现场。她坐在我对面拭泪,不好意思地说:"真抱歉!我……我是不是很可笑啊?我看过好多遍《茶馆》,也听过我儿子在家里背诵台词,但是,当我看到他卖女儿的时候,我……我真的觉得是我孙女被卖了呀!你想啊,一个人,得难倒什么程度,才会把十五岁的女儿卖十两银子,去给太监当老婆啊……"
看一档节目,内容是关于"打拐"的。五岁的小女孩点点随妈妈去甜点店吃甜点。妈妈说有点事需要出去一下,嘱点点乖乖等妈妈回来,点点答应了。妈妈走后,即进入了旁边的监控室,通过大屏幕观看点点的一举一动。不一会儿,"骗子"演员登场了。他亲切地跟点点搭讪,叫出了她的名字,并声称是她妈妈的好朋友。"你妈妈让我来接你呢,走吧。"点点听了,竟毫不犹豫地就跟着"骗子"走了。大屏幕前,妈妈无声凝噎。节目一结束,她就疯狂地冲了出去,一把搂住"失而复得"的女儿,嚎啕大哭。
许多年前,我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别问》:"别问我为什么一早醒来/就死死地抱住你/别问我为什么抱着抱着/眼里就滑落了泪滴/别问我梦到了什么/我死都不会说/我只感谢蜜一般的阳光/瞬间消融了枕边那黑色的惊悸。"——别问那被我"死死抱住"的人究竟是谁,母亲?爱人?孩子?都不是,也都,是。
娇柔的爱,禁不起一个虚拟。至爱的人被卖、被拐、被梦魇劫掠,明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吹拂即破,但自己的口硬是劝说不了自己的心,轻松卸下那份累赘般的哀伤。当我们将自己摆在那个假设句旁,我们立刻一头扎进去,假戏真做,不能自拔。痴愚的心,执拗地将一场毫无悬疑的"虚惊"读作了"真骇",然后恫惧,然后淌血,然后摔个稀巴烂。
天光有些暗,我侧脸照了一下镜子,竟被镜中的影像吓了一跳。那个瞬间的我,像极了自己的母亲。一愣神儿的工夫,我越发惊惧了,因为,镜中的影像,居然又有几分像我的外祖母了。我赶忙揿亮了灯,让镜中那个人的眉眼从混沌中浮出来。
母亲有一件灰绿色的法兰绒袄子。盆领,掐腰,用今天的话说,是"很萌"的款式。大约是我读初二那年,母亲朝我抖开那件袄子说:"试试看。"我眼睛一亮——好俏气的衣裳!穿在身上,刚刚好。我问母亲:"哪来的?"母亲说:"我在文化馆上班的时候穿的呀。"我大笑,问母亲:"你真的这么瘦过?"
后来,那件衣服传到了妹妹手上。她拎着那件衣服,不依不饶地追着我问:"姐姐,你穿过这件衣服?你真的那么瘦过吗?"
现在,那件衣服早没了尸首。要是它还在,该轮到妹妹的孩子追着妹妹问这句话了吧。
人说,人生禁不住"三晃":一晃,大了;一晃,老了;一晃,没了。
倒退十年,我怎能读得进去龙应台的《目送》!那种苍凉,若是来得太早,注定溅不起任何回音,好在,苍凉选了个恰当的时机。我在大陆买了《目送》,又在台北诚品书店买了另一个版本的《目送》。太喜欢听龙应台这样表述老的感觉——走在街上,突然发现,满街的警察个个都是娃娃脸;逛服装店,突然发现,满架的衣服件件都是适合小女生穿的样式……我在书外叹息着,觉得她说的,恰是我心底又凉又痛的语言。
记得一个爱美的女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揽镜自照,小心翼翼地问候一道初起的皱纹:"你是路过这里的吧?"皱纹不搭腔,亦不离开。几天后,再讨好般地问一遍:"你是来旅游的吗?"皱纹不搭腔,亦不离开。照镜的人恼了,对着皱纹大叫:"你以为我有那么天真吗!我早知道你既不是路过,也不是旅游,你是来定居的呀!"
有个写诗的女友,是个高中生的妈妈了,夫妻间惟剩了亲情。一天早晨她打来电话跟我说:"喂,小声告诉你——我梦见自己在大街上捡了个情人!"还是她,一连看了八遍《廊桥遗梦》。"罗伯特站在雨中,稀疏的白发,被雨水冲得一绺一绺的,悲伤地贴在额前;他痴情地望着车窗里的弗朗西斯卡,用眼睛诉说着他对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的刻骨珍惜。但是,一切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我哭啊,哭啊。你知道吗?我跟着罗伯特失恋了八次啊!"
多年前,上晚自习的时候,一个女生跑到讲台桌前问我:"老师,什么叫‘岁月不饶人’啊?"我说:"就是岁月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她越发蒙了:"啊?难道是说,岁月要把人们都给抓起来吗?"我笑出了声,惹得全班同学都抬头看。我慌忙捂住嘴,在纸上给她写了五个字:"时光催人老。"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回到座位上去了。其实,再下去几十年,她定会无师自通知晓这个词组的确切含义的。当她看到满街的娃娃脸,当她邂逅了第一道前来定居的皱纹,当她的爱不再有花开,她会长叹一声,说:"岁月果真不饶人啊!"
深秋时节,握着林清玄的手,对他说:"我是你的资深拥趸呢!"想举个例子当佐证,却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他《在云上》一书中的那段话:一想到我这篇文章的寿命必将长于我的寿命,哀伤的老泪就止不住滚了下来……这分明是个欢悦的时刻,我却偏偏想起了这不欢悦的句子。
离开腮红就没法活了。知道许多安眠药的名字了。看到老树著新花会半晌驻足了。讲欧阳修的《秋声赋》越来越有感觉了。
不再用刻薄的语言贬损那些装嫩卖萌的人。不经意间窥见那脂粉下纵横交错的纹路,会慈悲地用视线转移法来关照对方的脆弱的虚荣心。
柳永有词道:"是处红衰绿减,冉冉物华休。"这样的句子,年少时根本就入眼不入心。于今却是一读一心悸,一读一唏嘘。说起来,我多么为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两个演员庆幸,如果他们是在自己的青葱岁月中冒失闯进《廊桥遗梦》,轻浅的他们,怎能神奇地将自我与角色打烂后重新捏合成一对完美到让人窒息的厚重形象?
不饶人的岁月,在催人老的同时,也慨然沉淀了太多的大爱与大智,让你学会思、学会悟、学会怜、学会舍。
去探望一位百岁老人。清楚地记得,在校史纪念册上,他就是那个掷铁饼的英俊少年。颓然枯坐、耳聋眼花的他,执意让保姆拿出他的画来给我看。画拿出来了,是一叠皱巴巴的仕女图。每个仕女都画得那么难看,像幼稚园小朋友的涂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兴致勃勃地欣赏。
唉,这个眼看要被"三晃"晃得灰飞烟灭的生命啊,可还记得母校操场上那个掷铁饼的小小少年?如果那小小少年从照片中翩然走出,能够认出这须眉皆白的老者就是当年的自己么?
我们回不到昨天,明天的我们,又将比今天凋萎了一些。那么,就让我们带着三分庆幸七分无奈,宴飨此刻的完美吧……
那天,我正看一个挑战类的电视节目。当一个叫卡尔布的德国人登场的时候,我丢掉了手里的家务。
那是个大块头的家伙,拎着一把红色的电锯,慢吞吞地出场了。他要表演的是,用不超过150秒钟的时间,将一截木桩制作成一个可以承受他自身重量的小椅子。
木桩是普通的木桩,跟扔在我家后院的一截木桩没啥两样。
我看见卡尔布将木桩竖了起来,然后朝主持人晃了一下电锯,示意准备好了。于是,计时开始。
卡尔布娴熟地使用着电锯。笨重的身体一点也不妨碍他灵活的手。电锯与木桩亲密接触,嗡嗡的响声中,被淘汰的边角料一块块应声坠地。一时间,我根本看不出卡尔布究竟是在做椅子的哪一部分,只看到屏幕左下角的电子计时器在不停地跳字。两个主持人忘记了解说,只管前倾了身子、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看卡尔布的精彩表演。到了后来,连边角料都看不到掉下来了,卡尔布的电锯用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语言说着轻重深浅。在我眼中,卡尔布不像是在做木匠活,倒像是在进行一场"行为艺术秀"。
观众一片欢呼!卡尔布从木桩的顶端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椅子——用时仅仅95秒钟!
卡尔布得意地将那个靠背上带有镂空花饰的小椅子放在地上,然后,单脚悬空站了上去。演播大厅又是一片欢呼。
我多么喜欢那个瞬间诞生的迷你椅子啊!我设想着如果把它稍稍打磨一下,刷上清漆,上面再安放一个花儿一样的孩童,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不由想到我国宋代那个画竹高手文与可,他画竹的秘诀是,先让竹子在胸中长出个样儿来,再按那胸中的样儿将竹子搬到纸上。我想,对卡尔布而言,又何尝不是先在胸中制成了一把现成的椅子呢?那个小椅子原本就是藏在木桩里了,卡尔布只是花费了95秒钟的时间,将它从木桩中"找"了出来。
在尘世间,"创造"这东西永远是最迷人的,颖慧的心,灵巧的手,常能对凡庸的事物做出非凡的解读。没看卡尔布表演前,我只会将我家后院的木桩叫做木柱,它们呆头呆脑,只不过是木头一截、一截木头;看了卡尔布表演之后,我看那些木桩时的眼神倏地变了!我设想那庸常的木桩里面正藏着一批精美的迷你椅子,只待一把富有灵性的电锯一声轻唤,它们即会列队翩然而出!
其实,又何止是木桩呢?被我们凡庸的眼与心怠慢了的事物尚有很多很多吧?山水里藏着画意,四季里藏着诗情,有谁,愿意带着激情将这旷古的画意与诗情从混沌的背景中解救出来,让它们以一种无比美好的姿态,恒久地存活于喧闹人间!
我在审视母亲走过的人生轨迹时,发现它是枣核儿形的:起初,母亲的世界在南旺村那个狭小的院子里;后来她的世界延伸到了晋州文化馆;再后来,她的世界竟然还曾延伸到了椰风海韵的湛江……
然而,大约十年前,母亲的"枣核儿"开始悲凉地收拢,慢慢滑向比先前那一端更逼仄的另一端。随着母亲的膝关节炎的加重,她的世界从县城,缩小到西关,再缩小到院落、房间……
母亲越来越离不开人了。有时候,弟弟弟妹出去片刻,她都会惊慌不已。她心中藏着一种尖锐的怕,就算她不说,我们也猜得透。
这次回家,我问母亲:"妈,你可还记得怎样盘那种蒜疙瘩扣么?"母亲黯然道:"记性越来越差,怕是早忘啦。"我便找出事先备好的各色丝绳,递与她。
母亲背光坐着,喜爱地摩挲着那些滑腻的丝绳,慢慢拈起一根,不太自信地将两头搭在一起,又慌乱地扯开。
我鼓励她说:"妈,你还记得我那件玫红色法兰绒的坎肩不?那不就是你盘的扣子吗?每年秋天我都要穿一穿它呢!我一直想跟你学盘扣子,一直也没学会……"
母亲听了,数落我道:"手指头中间长着蹼呢——拙呀!"我摊开手掌,装傻道:"啊?蹼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母亲仿佛在数落我中汲取了力量,脸上有了明快的自信,继而,这自信又蔓延到了手上。只见她兀自笑了一声,两只苍老的手笃定地动作起来。
扭,结,抽,拉,母亲的手从容地舞着。神助般地,她终于盘成了一个完美的扣子!
母亲越盘越娴熟,那过硬的"童子功"毫不含糊地又回到了她的手上。
母亲是多么快活!她对来借簸箕的邻居大声说:"这不,我家大闺女稀罕我盘的蒜疙瘩扣,非让我给她盘!你看看,都盘了这么多了!"
我毫不吝惜地赞美母亲的作品,毫不掩饰地表达想要更多扣子的愿望。母亲则因为帮我做了我无力做成的事而开心了整整一天。
我悄悄跟自己说:"母亲那尖尖的‘枣核儿’能吸附些微的快乐,该有多么不易!所以,在母亲的有生之年,我不能学会盘扣子,绝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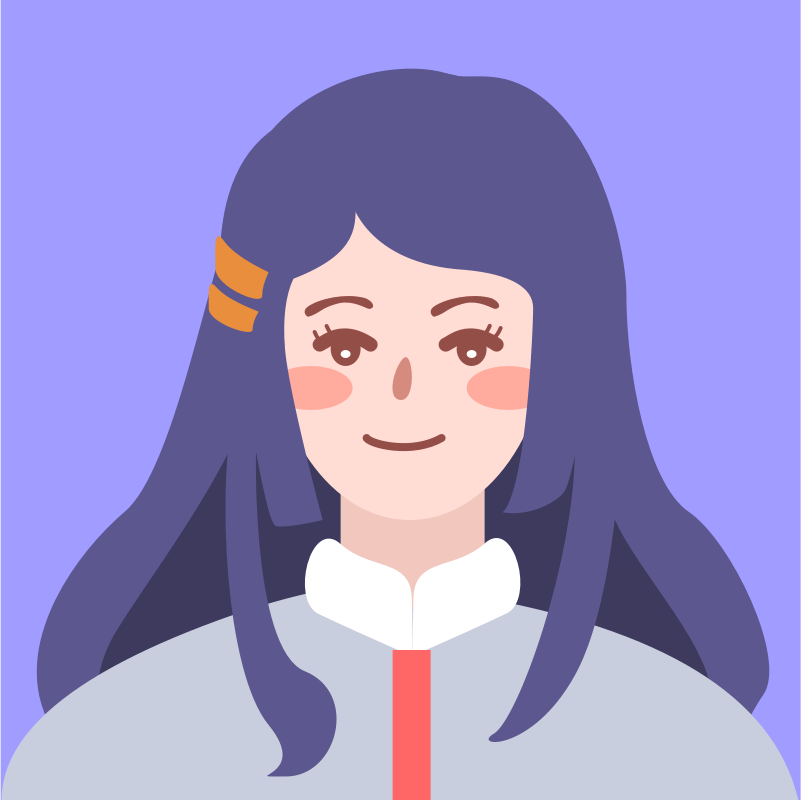 U782058360
U7820583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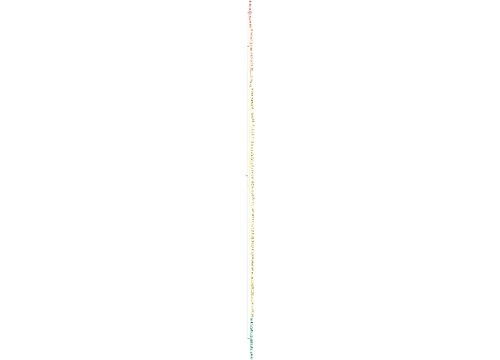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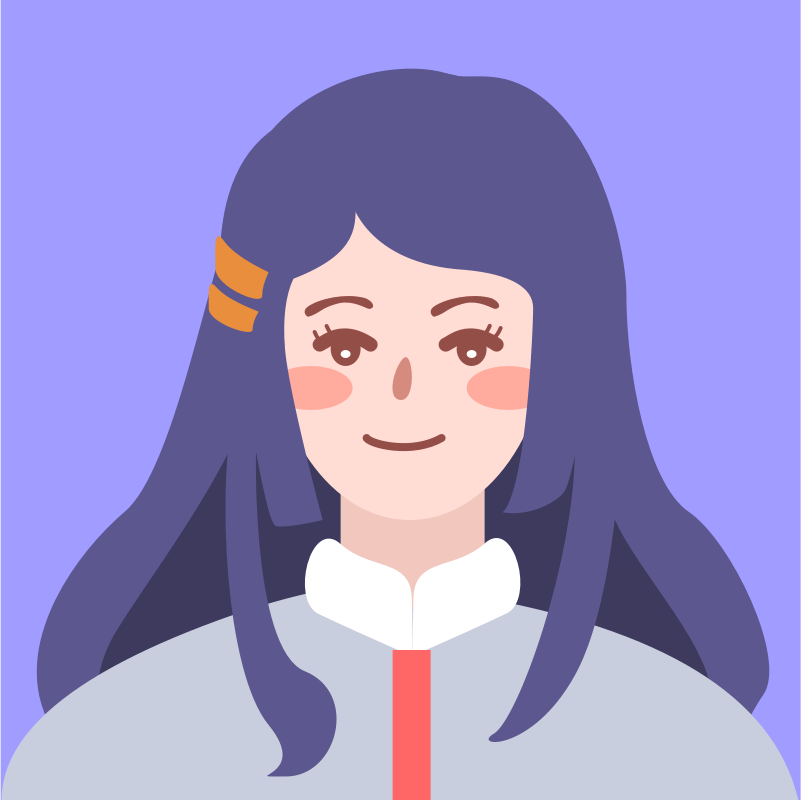 U181668800
U181668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