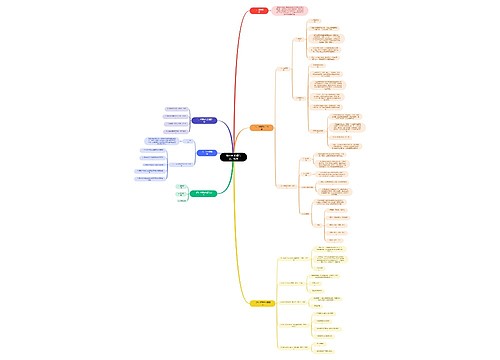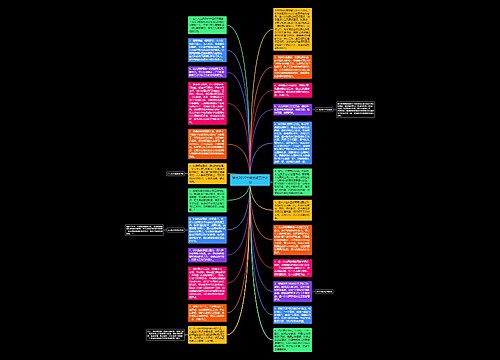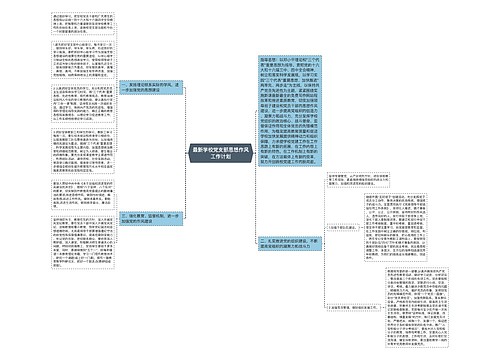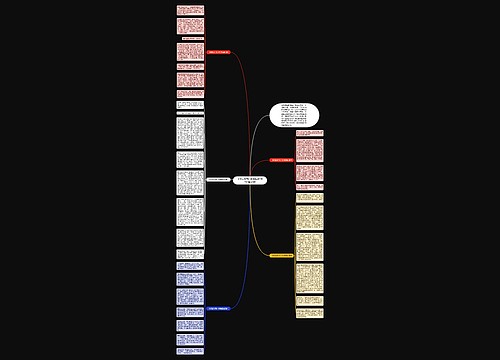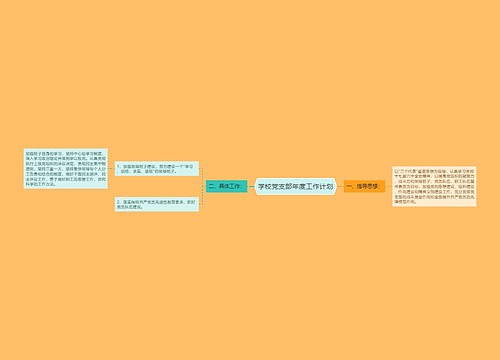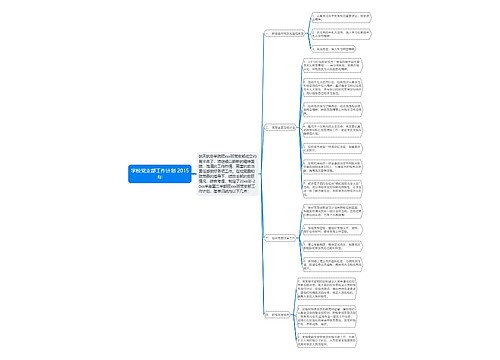《呼兰河传》在中国三十年代的小说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独有的诗化小说形式开创了中国三十年代小说历史上的写作先河,在结构上与其他小说完全不同。以一般小说的概念去衡量它,它不具备贯穿全书的线索,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中心人物,而是以儿童视角吟唱了那个年代悲苦的诗;同时,这部堪称萧红经典的小说以揭露旧中国人性的扭曲及人格的辱没、人们自我意识的麻木和淡薄为主题,在当时抗日的背景下对唤醒国民意识具有重要启蒙作用。
小说共分为七章,再加尾声。各部分之间没有情节和叙述上的必然联系。萧红以孩童视角去看待八十多年前的呼兰城,增添了真实感,丰富了小说意蕴;将童年记忆作为书写对象,具有很强的怀旧情结。笔触自然清新不造作,部分章节流露出孩童的纯真和童趣。正是这小孩子的纯洁无邪和欢乐无忧反衬出呼兰河成人世界的愚昧与复杂。
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和禁锢,村民们即使活在自己亲手编织的不幸中仍不知觉醒,对落后的礼教教条及顽冥不化的迷信陋习引以为然、不思变通。文章多处细节描写折射出呼兰城人思想的腐朽愚昧。地上的大坑吞噬了鸡鸭猪,使马车和人陷入泥坑不能自拔,但是人们在惊恐和议论之余不会想着去填掉它,反而为市场廉价的瘟猪找到购买的理由;村民热衷采用跳大神的迷信方式来治病,把鬼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为各种神仙举办庙会。一系列过分的迷信活动和信念让人们读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绝望,在跳大神搞笑把戏的传神描写中读出一股恶作剧般的悲剧意味。
更甚,呼兰城人对生命轻薄和漠视,对生老病死的习以为常、麻木迟钝。老头子跌倒在天寒地冻的雪地里,馒头还遭人抢吃;村民们看戏似地戏弄傻子疯子叫花子。对待他人的不幸就是以看热闹的形式表明事不关己的态度。卖豆芽的疯女人每天哭哭闹闹,但仍然会按时去市场卖豆芽,这又反映出村民们不但对待别人的态度是无关痛痒的,对待自己也是屈服在现实的残酷和生命的枯燥循环当中。没有创新的模式只会导致生命力的固化和消亡,这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呼兰河人却不以悲剧为悲剧,这种麻木不仁超然冷漠才是真正的更大的悲剧。
小说对小城人麻木愚昧以及传统文化心理、旧的礼教吃人的批判最集中地体现在小团圆媳妇的悲剧上。这个十二岁天真活泼的小女孩被卖到老胡家当童养媳,因生性活泼大方、不怕羞、勤劳能吃的性格特点和过于高大引来婆家的不满。因她的不符合男权社会的基本要求而引来左邻右舍的评头论足和无端指责。顽固不化的婆婆誓要把小团圆媳妇整成传统妇女的形象,丧心病狂地折磨虐待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女。小团圆媳妇最终在众人非人的治疗下被开水烫死。婆婆们作为同性,不仅不怜悯小团圆,反而主动组成一个杀人团,以堂皇的理由,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一个个像人的女性剿灭虐杀了,令人发指。这使得作品的悲剧意味更加浓重,揭示出在一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下的相互同化和异化、扼杀人性。
对于集闭塞、保守、愚昧之大成的呼兰城,萧红没有采取疾言厉色、匕首投枪般的正面批判,而是把穷形尽相的揭露和鄙视憎恨的态度,包藏在调侃反讽、苦涩悲凉的乡土叙述之中。综观全书,大半以上的叙述,都是调侃反讽的语调,都有弦外之音、弦外之旨。
作者在小说中四次写到荒凉,表现出她对呼兰河深深的孤寂和苦闷之感。她笔下的呼兰河无知、愚昧、苦难、悲凉,荒凉的土地上弥漫着绝望。然而在小说没有一个积极的人物的背景下,幼年的作者可以说是小说中最欢乐最无忧的角色,但是她的眼中看到花草树木能随心所欲地疯长,而人特别是女人反而受到很多莫名的压迫和拘束;荒凉的自然空间,乐趣也受到强调,例如草屋上雨后长蘑菇也引来大家的驻足观看。我自由活泼的天性为后面的悲哀埋下了伏笔。该小说的描写对人的世界悲悯与反讽兼具。
小说中还提到老光棍有二伯,他属于压抑人格类型,性格古怪,把牢骚和偷窃作为对现实不满的宣泄方式。他上吊和跳井的闹剧成为人们的笑柄。他是多余人的形象,没有美化和拔高,其行为无法构成对现成体制的颠覆。即使他抱怨这个世界的现实和人情的冷落世态炎凉,但是他终究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手无寸铁无法改造这世界。作品就是这样一部关于小人物的悲剧,但它又不完全是小人物的悲剧,更像是为那个时代而唱的一曲悲歌。
透过这部小说,我们看到呼兰城闭塞、落后的人文环境,生命力出现了弱化与萎缩,一切仅仅是为了漫无目的地活着,像动物一样地活着,虽然背后是急剧变化的大时代。这死水般的生存状态下透出国民的弱点和病态,形成了作品悲凉的情感创作基调。
《呼兰河传》在讲故事的同时启发我们对周而复始的生命的思考,如何才是生命的敬重,如何才是人格的保全,如何才是价值的道德和真正的人生信条。我们都太年轻,而历史太苍老,如果没有去读一读那个年代悲苦的诗,厚重的历史使我们太渺小也使我们愈加地无知。破除无知愚昧落后的思想仍旧需要每个时代的人们去努力,世态炎凉、漠视生命、荒凉良心是我们每个时代都应去消除的迷障。这部小说具有时代意义,生命不息,便叩问不止,前行不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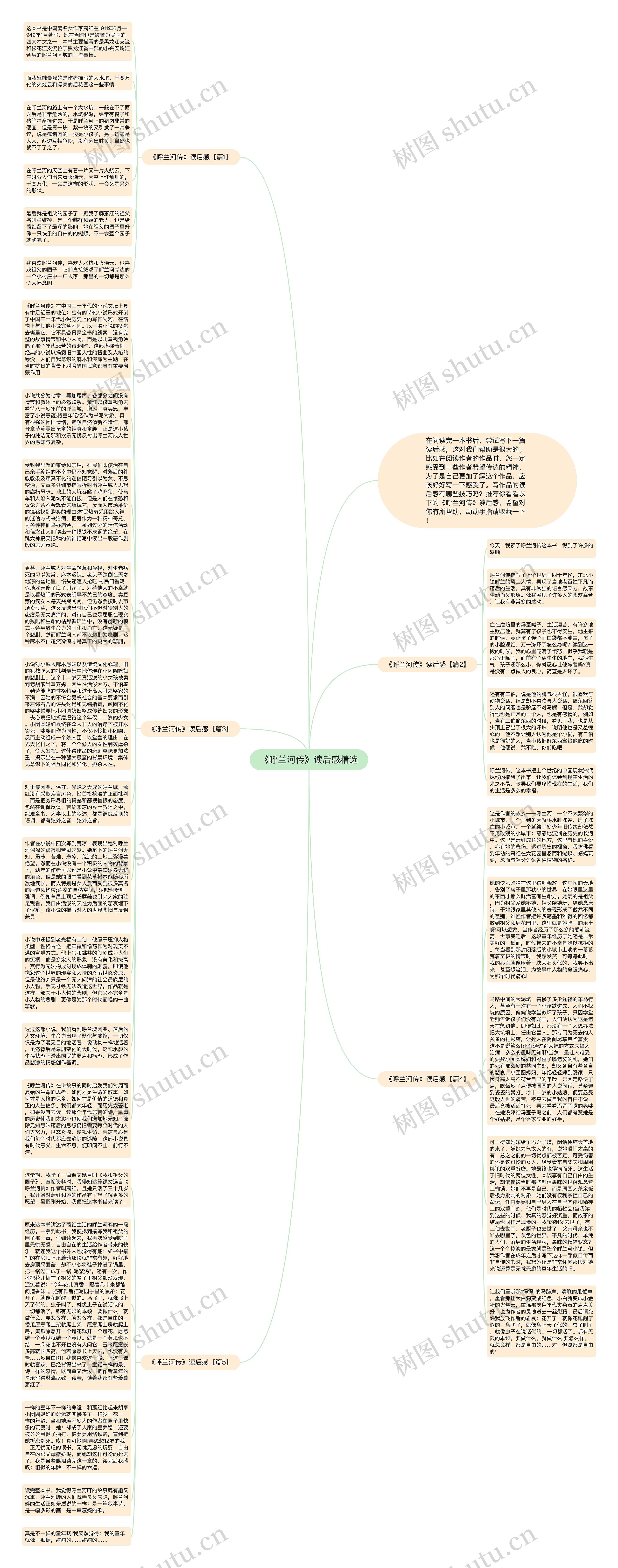
 U882673919
U88267391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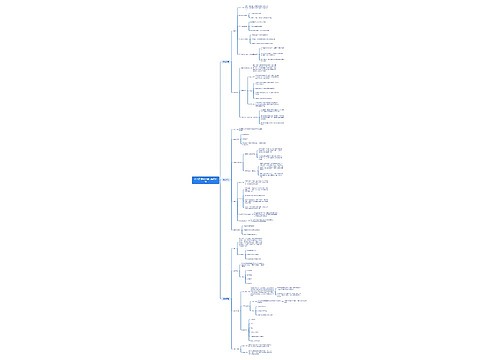
 U482034820
U482034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