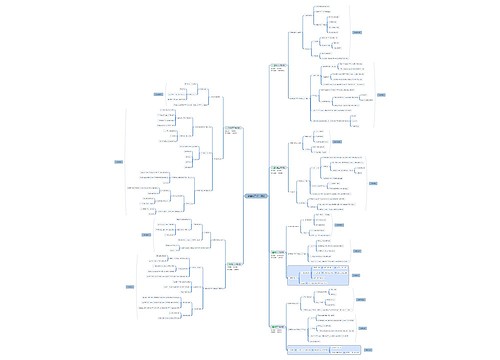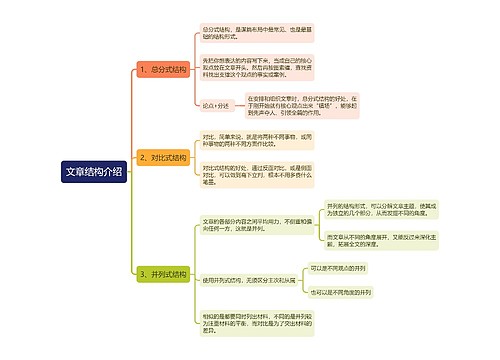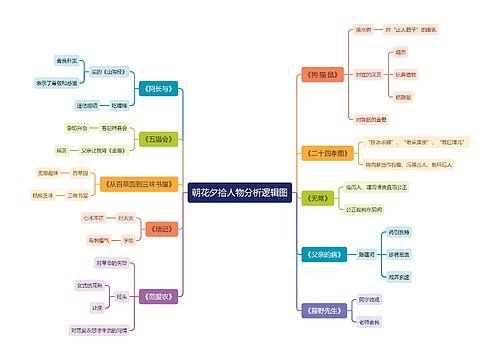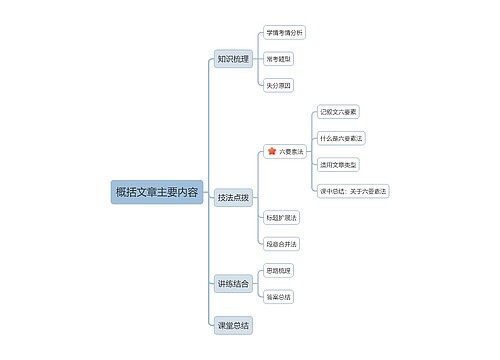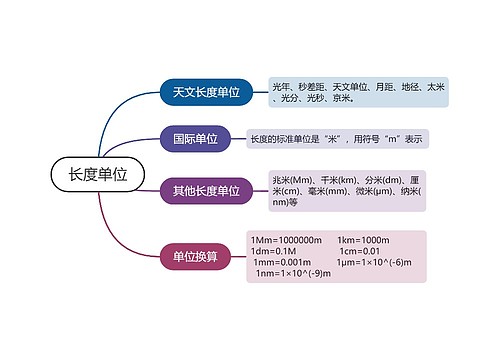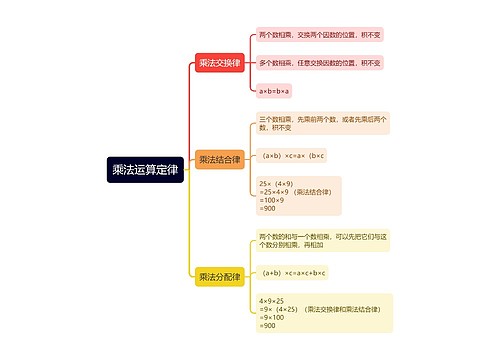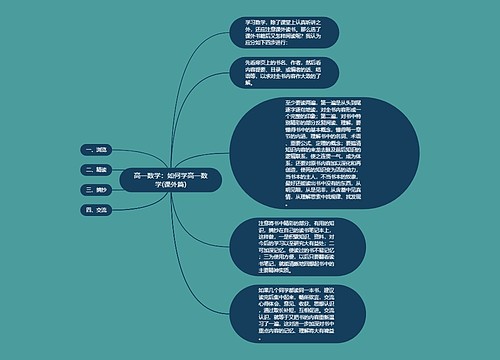听到她考入市重点高中,心中也没有什么惊讶的,只是暗自为她高兴,望一望窗外泛黄,零星的落叶,思绪一沉,为她的命运慨叹。
这便是丫,一个我儿时玩伴,共度着学前时期的童稚时光,我清晰记着母亲说着的这句话"丫给的东西不能吃了她的水也不能喝,"因为太过年幼,只是一切遵从母亲说的,却不知为什么,我们依旧在一起玩着,只是不曾接受过她手中的一点吃食,就这样我们步入小学一同背着小书包啊,走在上学的乡间小路上,你一句我一语,我跑着,她追着。她个儿还比我高一点,超过了同龄年龄的身高可以让她在嬉笑追逐时任意打一下男生几下,总之我记的她的笑声挺大,攥紧的拳儿打在后面很有力很疼。
三年级吧,丫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我想这也是她心中最低谷的时候吧,爷爷奶奶的去世,这意味着从小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她又再次沦为孤儿,她被患有轻微残疾的姑姑抚养。伴着她家两次的发丧队伍,家门口的人儿便开始叹惋丫,这个苦命的孤儿,便开始谈起了这个孩子的悲惨,大抵也是在母亲嘴里听到了许多吧,我便开始了解她。
翻一翻家里的相片,有很多张我儿时的照片,大概我一岁吧,和一个我不熟识的男人的合影,身旁还站着爸爸,母亲告诉我相片中的那个男人就是丫的爸爸,父亲与丫的爸爸是很要好的朋友,她爸爸患有肝病,在丫爸肝病晚期的那几天因药物与精神压力吧使他特别的烦躁,随即也就和父亲争执了几句。几天不曾来往,也就是这几天,传来了丫爸的死讯,如五雷轰顶的砸在了父亲头上,更打在了丫的母亲与年幼的她身上,砸在了年迈的爷爷奶奶身上,竟要白发人送黑发人,随后丫的母亲便改嫁了,那时的丫才两三岁,便开始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了,可不幸并未就此停止,年幼的丫被确诊为肝病,应该是被父亲遗传所致的吧,她开始往返于市中各大医院,诊断医治可终不见效,这种病怕是付不了那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从此,在接种疫苗的队伍里,我从未见到她的身影,因为特殊体质是她不能接种各种疫苗,而她的病仿佛也具有传染性吧,家门前的小孩都不会接受她的吃食。
在她被姑姑抚养后,一直待她很好,姑姑是个很矮很慈祥的人,总是笑着,也很憨厚,她不能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孩,女孩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偷家里的钱在外面与一些社会上的人接触,后来就不回家了。到了姑姑家,从奶奶去世不到一周,她像是瞬间长大了似的,放学的路上她步伐很快,留给我的也只是他渐行渐远的背影直至前方的岔路口他消失不见,在家里,她总是要做家务的,洗锅洗衣,整理家务,因为姑姑的忙碌,有时午饭也要自顾自,偶尔去几次她家,总见她挽着袖子忙碌着,作业还那么多,有时间做吗?可每次她的作业都是老师夸赞的对象,在一次与她做作业时,她伸手拿笔的那一刹那,我不经意间看到她已微微泛黄的手心和茧子,啊,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我没有询问,只是在心中黯然沉默了。姑姑和姑夫靠卖一些市集小商品为生,家里有几亩地,就这样丫在这里得到了一份来自心间浓浓的爱,但她总是冷冷的,扎着一个马尾辫。鼻梁直挺,嘴唇在一吸一吐间微微颤动,她总是穿着干净,衣服显旧,颜色变淡了,却依着整洁,不见污物,牛仔裤已经明显有些小了,裤管已无法遮住脚腕了,一双十分普通的布鞋,那时已经没有女生愿意穿那么不漂亮而廉价的的布鞋了吧,可她并不在意,鼻梁直挺,嘴唇在一吸一吐间微微颤动,水汪汪的大眼睛是那样的清澈仿佛滴一滴水进去还能击起涟漪一般,这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啊,噙含了许多的泪,噙含了太多的伤痛,也许噙含了命运对她的歉意。
在学习上她表现的总是那么积极向上,名列前茅。考试成绩下来了,很多人面露难色不知如何向父母交代,而丫一如既往的平津,以为他的成绩似乎总是第一。当父亲询问我成绩时,我如实说了,其实也不差,他喝着茶冷冷的问了一句"丫又是第一吧",我没抬头恩了一声,这样的话我司空见惯,却又反感这样的问话,耳旁"你知道呀每天要干多少活吗,可他就那么懂事还那么用功。。。。。。。"听着听着我心头有了一丝愤意,凭什么呀就学的那抹好,我也在努力学习啊,可当再见到亚视,我心中的内疚惭愧已无以言表了。再想想父亲的话,她每天要干多少活啊,多少家务,映入眼帘的是我忘却不了的她的那双微微泛黄的手。
她总是坚强的女孩儿,她很少哭,没有其他女孩那么多的泪,一部略显冷的表情,只是你逗她时,笑几下与你嬉戏,我见过丫哭的的不顾面目那大概是五年级吧,还在家里,却听到屋外哭嚷,只见一个三十左右的女人与丫站在一起,丫哭的不能自己,嘴里嘶喊着"吗,你不要走。"那女人也已是泪流满面,给丫说着什么,一转头拭泪迈步时,丫拉扯着女人不肯放手,更是一通撕心裂肺的哭喊,任这路口旁人如何看待,路旁试过的汽车放缓速度伸出脑袋张望,这些都已全然不顾,丫的身后不远站着丫的姑姑,抽泣着,站在那儿看着这母女离别的场面,一只手不停的拭着眼泪,嘴里发出不大的声音带着哀求吧"丫,你让妈走吧!"僵持了一会,大概是丫觉得留住母亲不现实吧,她放手了,让母亲回到了那个城里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让一个自己同样陌生的弟弟贪婪的肆意的享受母亲的疼爱,而自己蹲下身子在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后才被拭着泪的姑姑拉回屋里去,久久不能平息。
转眼初中,我偶尔去与她写写作业,一起探讨一下问题,一边写一边相互逗笑,我也愈发觉的她与我不是很亲近了,大概是女孩普遍早熟吧,她开知羞涩了,不再像小学那样大声笑了,而是抿一下嘴,露出几颗洁白的牙齿,也可能是见面的机会太少,间隔太久,彼此有些生疏了吧。初中,我们仿佛在现实与虚幻中迷离,愿意自己不羁一切,用敌视眼光宣扬着清纯的叛逆,穿着彰显着成熟的衣服,逐渐的活跃在同学朋友生日的酒吧里,烟味弥漫的网吧里,忘记了闷热的补习班,忘记了书包里还未见字迹的作业,更忘记了时间的指针已悄悄地逾过了十二点的禁区,推开屋门在父母的谩骂中以一种厌烦的态度坐在闷热的教室里。但我在这样的状态里度过了几个月后,我开始落寞了,我开始孤寂了,当一个个看似青春美丽的女孩在朋友身边拿着话筒故作姿态的唱着一首首情爱的歌时,落寞从心头泛起,震耳的音箱声,炫目的闪光灯,装上浅黄色在杯中摇曳的液体,我开始恐惧,我开始心神不定,我甚至能听到我粗重的喘息,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推开房门,我狂奔着,随着身后震耳的音箱和朋友的呼喊淡去,停下呕吐,在一个昏暗的路灯下,坐在路边望着自己的影子,质问自己。路过那个依旧熟悉的路口,却莫名其妙的停下了脚步,片刻她跑了出来,依旧微笑着,马尾在身后荡漾,一件淡色的短袖和一条浅色的牛仔裤,她用一种青春欢快的语气问我怎么了,我一笑说了句想你了,她半捂着脸含羞地低着头,依旧是那我很久都不曾听到却渴望听到的明朗的笑声,望着她清纯洁净的脸,那双透彻明亮的眼睛,我的心里是那样的平静,听着她讲着自己的琐事,聆听着,此刻她仿佛散发着光芒,照亮着我心中逆青春的阴影,再坐在教室里,心中平静如水,没有了落寞,没有了烦躁,我感受到了做一个学生的正青春。就这样,我开始做着以前的自己,在题海中度日,在书本中拼搏,在同学的激烈的讨论声中寻求快乐,只不过在闲暇时就会给丫讲讲自己的状态,讲讲同学老师,在他的笑声中寻求满足,当同学们在一起时,我为他们讲起了丫,讲起了那个命运坎坷的丫,那个他们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一个女孩子,我在用我低沉的嗓音,坦然的心歌颂着她,歌颂着这样一个出生在秋天的女孩子,在我眼里,她如金子一样珍贵,即使踏出校门,当她从一个个身着华丽搽抹淡妆亮丽的同龄女孩面前低着头走过时,那看似微不足道的卑微,在我眼中,却戳着我的心,但却又是她可贵的地方。
又过了许久,我站在她家门口叫她,她应声出来了,见我还是那样笑着,而这次她的后面多了个扭扭妮妮的小家伙,依偎在她的身后露个脑袋"咩咩"的叫着,她用手轻轻的推了几下小羊,可小羊依旧紧紧挨在她身后,她向我笑着说才刚满月的小羊,她每天都用奶粉或牛奶去喂它小羊就带她如母亲一般,她到哪儿小羊就到哪,我听了冲她笑了笑,她应着我的笑儿,那一笑之际夹含着她的羞涩,她的不好意思和对小羊死缠的无奈,虽是一只小羊,可她却用爱去喂养,也是她能感受到小羊那种失去母亲的孤寂吧,和那种急于寻求母爱与奶水的心情吧!在小羊的世界里她扮演着一个母亲。
在她面前,我永远给予她的是鼓励,是奋进,她一定不曾感受到那时我发自内心的赞颂,她的命运,让我对她的并非是同情,她的品质,让我对她的并非只有仰慕,我呀就这样站在她的身后,心甘情愿的做了一个歌颂着,在我每次的写作中,笔下疾驶却从未留下她的半点墨迹,我想歌颂他,可我却不知道把她比拟成什么,寒梅吗,雪松吗,还是名人笔下坚强、立志、不屈命运的主人公,总是在思付着,却迟迟不肯下笔。当别人给予她掌声时,而我透过这浓重的赞颂中看到了伤痛,我开始不愿给她赋予另一个喻体,因为她不需要这些,无需修饰,无需点衬,我只给予她属于我的歌颂。伴着一声沉沉的落笔声,可思绪还停留在那个时空里,窗外的星很亮,我盯着入神……"一个模糊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她正端坐在课堂之上,一副不深的近视镜嵌在她挺直的鼻梁上,眼睛闪着光芒,目不转睛的盯着老师清晰的板书,聚精会神的聆听着老师的一字一句,时不时的低下头,笔下疾驶,一行行清新秀气的字儿跃然纸上,就在她那一低一仰之际,马尾辫儿飘荡了几下,散发着阵阵的清香……"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121265
U58212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