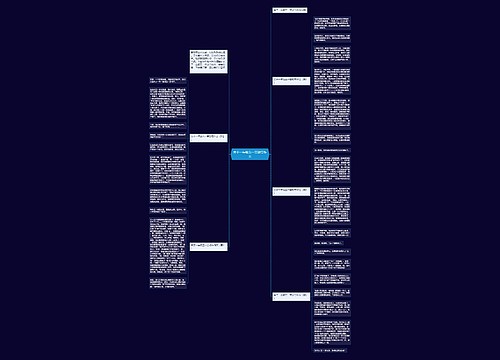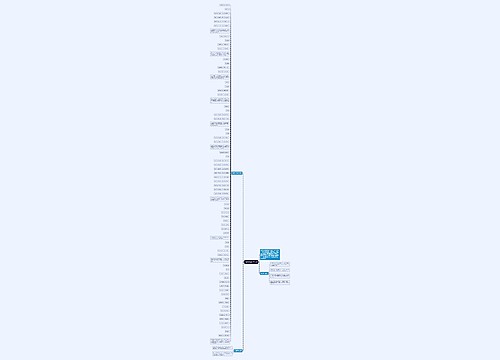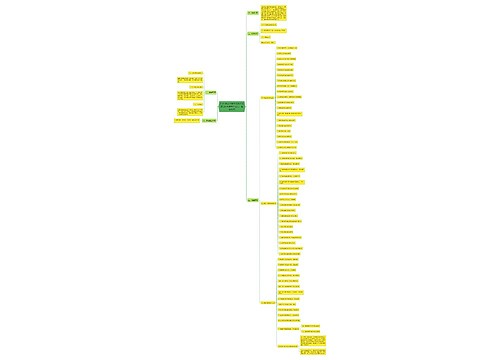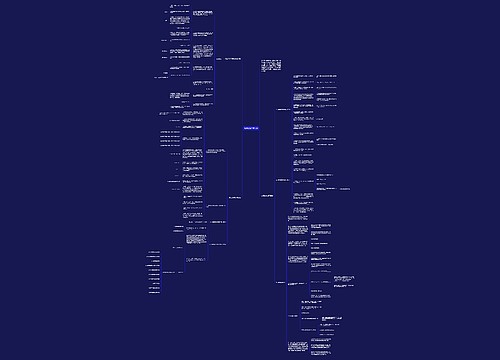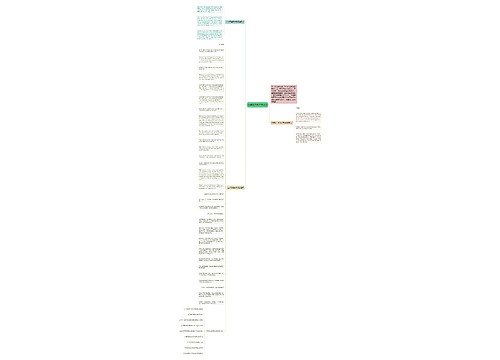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是指公有住房承租人(出让人)经产权人同意,在不转移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按规定程序将房屋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受让人),由受让人对出让人予以经济补偿的行为。
2001年《常州市区直管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试行办法》出台,其规定:直管公房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但须依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允许公房使用权有偿转让,其目的是为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搞活房地产市场,促进城市住房合理配置,引导居民住房消费,改善居民住房条件。
但是,公有住房毕竟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房,公房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还必须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原则。因此,上述《办法》规定,直管公房使用权有偿转让应当以调剂住房余缺、提高房产使用效能、改善居住条件为目的,并按照“自愿、诚实、公平、规范”的原则进行。
二、王夕是否可依物权法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取得讼争房屋的使用权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从上述法条规定的善意取得要件来看,物权法认定受让人是否系善意遵循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因为,“善意”本身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必须结合各种相关证据对行为人的外部行为进行综合判断从而予以认定。
本案中,李金祥与王夕均认可,转让协议签订前不久李金祥曾向王夕借款3万元。李金祥称,签订公房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应王夕要求对借款行为设定的担保。而王夕对此予以否认。担保法规定,抵押法律关系的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况且,公房使用权并不属担保法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可抵押财产的范围。因此,李金祥所称转让公房使用权系为借款担保的说法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从转让协议可见,李金祥向王夕转让公房使用权的对价是3万元。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公房使用权的转让价格固然由转让双方自行议定,但3万元却远低于同时期同地段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合理市场价格。而且,公房使用权转让后,李金祥始终未将房屋实际交付王夕使用,王夕对此亦未表异议。因此,认定转让行为系李金祥真实意思表示、王夕系善意受让人证据不足;而王夕以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抗辩,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即本案中的转让行为不能以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生效。
行政诉讼的立足点是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物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2001年《常州市区直管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试行办法》规定了转让直管公房使用权的基本程序,其中第一项程序即“出让人征得同住成年人的书面同意,填写《常州市区直管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情况表》。”
如前所述,公房使用权之所以允许有偿转让,其目的是调剂住房余缺、提高房产使用效能、改善居住条件。出让人转让公房使用权,如若没有取得同住成年人的同意,势必损害同住成年人的知情权与居住权,有悖公房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初衷。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地方规范性文件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操作意义。该文件对公房使用权转让程序的规定虽然效力位阶较低,适用地域范围仅及于常州市区,但市房管局作为常州市区公房使用权转让的有权登记机构,对上述规定系明知和应知。而该文件对公房使用权转让程序的规定,是对登记机构审查范围和步骤的明确和细化,非但不违反上位法物权法的规定,更与前述物权法规定之“其他必要材料”暗合。因此,市房管局未尽合理审慎职责,在申请人李金祥未提供同住成年人李俊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向王夕颁发公房租赁证,其颁证行为欠缺合法依据,应予撤销。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