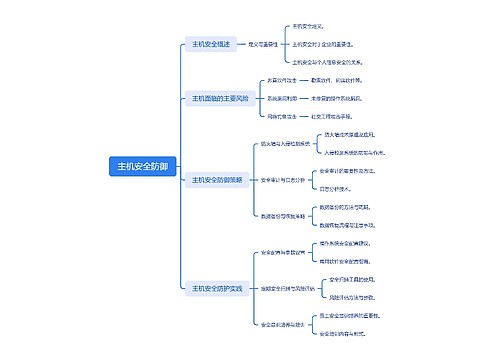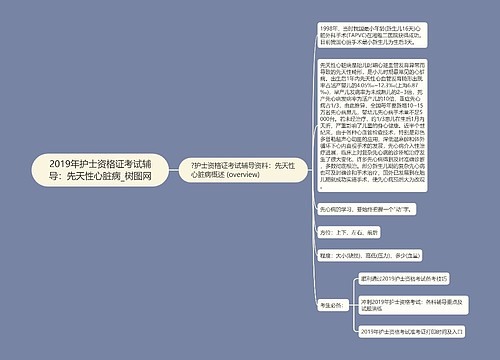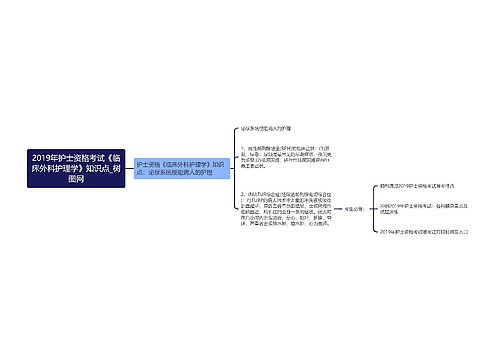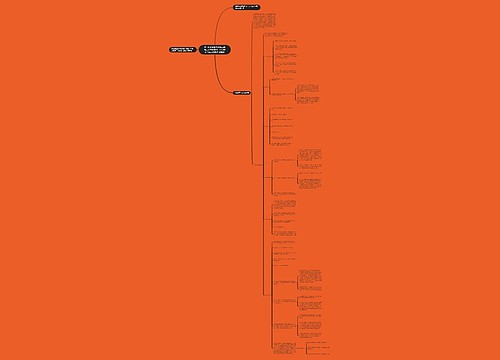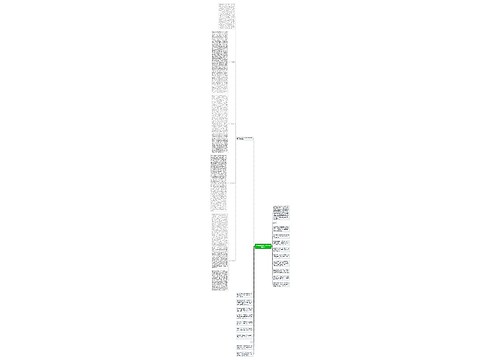前不久,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就治安进行部署时的讲话――“民警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引发了人们对警察开枪问题的广泛争论。许多人包括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都认为,在警察人身受到生命威胁或者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警察可以果断开枪;也有人认为,“开不开枪应由法律说了算”;有的法律专家则认为,“该开枪时就开枪,可开可不开时就不能开”。笔者无意介入这一争论,也无法立即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断。笔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争论?面对这一争论,法律人应该作出怎样的回答?
坦白地说,对于“民警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枪”这一提法,笔者的第一反应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广州的社会治安确实令人堪忧,采取一些包括开枪在内的果断措施制止犯罪行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笔者去年曾去广州上课,课间休息时,不少学员都善意地提醒我:尽量不要一个人单独逛街,更不要轻易在大街上打手机,以免遭“两抢”。弄得笔者在广州的两天连过马路都小心翼翼,更别说有什么心情“闲逛”了。因此,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笔者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有近万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八成以上的人会赞成“警方要敢于开枪”了。毕竟,警察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必要措施,对于实现对犯罪――尤其是一些特定的犯罪诸如抢劫、绑架等――的有效控制,从地方确保公民能够享有基本的社会安全,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确保公民享有基本的社会安全,这既是国家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任何一个公民对于国家的合理期待。
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笔者又对――“警方要敢于开枪”――这一提法深为担忧。毕竟,法律人的使命之一,就应该是关注如何防范国家权力尤其是警察权力的滥用,使一国的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享有基本的法律安全。所以,尽管笔者也同意,警察可以在包括自卫、解救人质、维护公共安全等法定情形下有条件地使用枪支,但,作为警察所有权限中的一种最极端、最严厉的强制性权力,使用枪支的权力又必须予以严格控制。否则,其一旦被滥用,不仅会对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权乃至生命权造成侵犯,而且还可能造成一些其他无法预料的严重社会后果(包括国际形象的贬损)。实际上,如果说犯罪行为所破坏的只是公民所享有的社会安全的话,那么,国家权力的滥用尤其是警察开枪权力的滥用,则将破坏公民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安全。而且,相对于社会安全的破坏而言,法律安全的破坏更值得我们法律人的关注。因此,一个国家可以确立什么样的开枪原则,这既是一个极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也绝不是一个市的领导人讲话就可以解决的。
尽管笔者缺乏必要的实证数据,但却不难推测甚至断定,就防范警察滥用枪支的效果而言,“鼓励开枪”与“限制开枪”将是明显不同的。而且,由于在我国现阶段,警察的法律职业化程度普遍还不高,尚不具备基本的法律职业家的理念,加上,警察权的滥用在中国本身就极为严重――侦查讯问过程中刑讯手段的广泛采用和屡禁不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个大市的政法委书记明确鼓励甚至要求――且不说她是否有这样一种权力――“民警面对砍手党要敢于开枪”,恐怕是不妥当的,其后果不仅是背离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彻底剥夺了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宪法权利,更将使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也是每一个公民失去最基本的法律安全。然而,让每一公民都能享有最低限度的法律安全,而不仅仅是社会安全,这事实上应该成为一个逐步走向法治化的中国所追求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可见,广州市政法委书记的这一提法之所以会引起广泛争论,既与其过多地关注了社会安全――其本质上是强调对犯罪的控制――而忽视法律安全存在着紧密联系,也是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重大区别分不开的。
是关注法律安全,还是关注社会安全,这可以说是法律人与普通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不同之所在。在社会安全和法律安全之间,法律人所孜孜以求的应该是法律安全的实现,至少也应该注意在社会安全和法律安全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所以,尽管我对广州市政法委书记的上述提法能够理解,甚至也表示相当的宽容,但却无法予以“协调性”地认同和接受。换句话说,对于警察使用枪支的权力不仅原则上不应提倡,还要予以严格地限制。即只有在――诸如当警察或他人正在面临可能危及生命或严重伤害的不法攻击行为等――法定情况下,警察才可以――当然不是必需――按照必要性原则的要求选择开枪。即使是在那些社会治安状况相对较差的地区,也不应对警察使用枪支的条件放宽标准。否则,恐怕――借用广州市政法委书记的说法――就将是民众的悲哀了。更何况,社会治安状况的彻底好转,需要的或许是“综合治理”之路,岂是“敢于开枪”就可以彻底解决的?

 U633687664
U633687664
 U882642901
U882642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