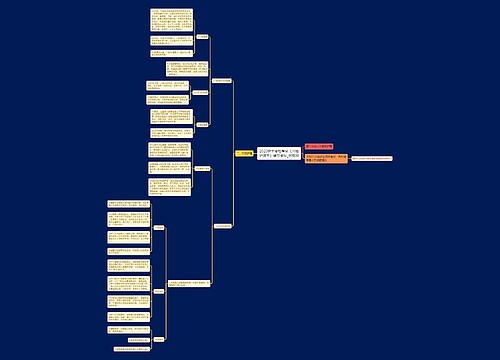作为行政裁量“法外”依据的公共政策思维导图
何苦孤独
2023-04-04

作为行政裁量“法外”依据的公共政策
论述分析
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教授曾言:“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部行政法的历史也就是行政裁量日益扩张及对其控制的历史。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作为行政裁量“法外”依据的公共政策》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作为行政裁量“法外”依据的公共政策》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d9b77d24e77172686f3f192165abb922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作为行政裁量“法外”依据的公共政策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教授曾言:“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部行政法的历史也就是行政裁量日益扩张及对其控制的历史。在行政裁量的控制模式上,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从程序机制角度看还是从权威性的决定规则角度看”,但通过立法控制、行政自制及司法审查实现行政裁量的规范运作却一直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主题。就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而言,无论是早期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三重控制说”,还是晚近围绕行政裁量基准兴起而展开的热烈讨论,都没有摆脱“法内控制”的基本范式。如何突破行政裁量控制研究的固有?如何在法律之外更为广泛的视野中寻求规范行政裁量运作的智慧与技术?正是这些追问激发了笔者对作为行政裁量“法外”依据的公共政策的关注。本文的研究显示,在行政裁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诸多的政策考量,而公共政策在行政裁量过程中的导入则具有正负双重影响。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公共政策的规范来实现行政裁量的正当运作。
一、隐藏在行政裁量背后的公共政策
简单来说,行政裁量就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规范赋予的权限范围内所进行的判断与选择活动。毫无疑问,法律规范是一切行政裁量活动的首要依据。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政策治国积习甚久的国家,公共政策依旧在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就行政裁量的实际运作而言,公共政策在很多情形下都是裁量者不得不考量的基本要素。以2009年发生的三个社会热门事件为例,人们不难感受到隐藏在行政裁量背后的公共政策。
事件一:“浙江工商新政”。为帮扶浙江民营企业脱贫解困,2008年12月30日,浙江省工商局出台了《关于促进全省民营企业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浙工商企[2009]1号),提出特殊时期对民营企业特别助动的“19条新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谓的“三不政策”:不处罚、不追缴、不吊销。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不无合法性质疑的“浙江工商新政”依旧因为适应特殊时期的现实需要而得到了同情的理解。从运作效果来看,2009年上半年浙江省工商系统针对各类轻微违法行为发放《行政告诫书》2万余份,做出口头告诫3万余次,对5万余起轻微违法行为未予行政处罚,绝大多数违法行为经行政告诫教育劝告后,当事人都能及时自行纠正。
事件二:“重庆吸烟被拘”。据2009年8月29日《重庆晚报》报道,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56岁男子赵某,在重庆市朝天门金海洋批发市场内吸烟被行政拘留5天,成为重庆市公共场所吸烟被拘第一人。面对媒体的广泛质疑,重庆消防部门祭起公安部“8・20”通知的大旗,表示要严格按照要求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保障国庆安全。根据公安部“8・20”通知的规定,在具备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吸烟者,一律行政拘留5日。尽管这一严罚措施与《消防法》第63条的规定不相吻合,但各地消防部门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对通知的拥护。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吸烟被拘案”在湖南、四川、辽宁等地相继上演。一些法律界人士对公安部“六个一律”规定是否合乎新消防法立法精神、是否合乎比例性原则提出质疑,有的学者还从裁量基准制度功能的正确定位上反思“吸烟被拘案”的是非。
事件三:“南京曝光醉酒驾车”。据2009年11月7日《京华时报》报道,近日,南京交管部门正式通过媒体曝光醉酒驾车者,首批公布的名单上共有106人,都已被拘留过。交管部门称曝光还将不定期发布。针对有人提出醉驾者拘留后还要被曝光是否过于严厉、是否涉嫌侵权一说,交管部门认为,曝光可以使醉驾者受到震撼,以后不敢再有类似行为,同时给其他司机以警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曝光醉酒驾车”事件发生之后,《检察日报》等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并组织了数次讨论。肯定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肯定的理由在于坚持媒体曝光“具有正面意义”,是对处罚结果公开原则的落实和延伸,能够有效遏制醉酒驾车行为;否定的理由在于曝光醉酒驾车不仅缺乏裁量的法律依据,也会助长选择性执法,无异于是对醉驾者实施更为严厉的“二次处罚”。
上述三个热门事件所反映出的共同问题都是行政机关对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的某种“变通”:在“浙江工商新政事件”中,工商局文件实际上是对免于处罚情形的适度扩大;在“重庆吸烟被拘事件”中,公安部通知及重庆消防部门的做法实际上是以“一律式”的裁量基准完全取代《消防法》第63条所规定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罚款――五日以下拘留”的“阶梯式”处罚规定;在“南京曝光醉酒驾车事件”中,交管部门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处罚结果公开方式上的一种裁量。无论褒贬如何,这些事件的背后都体现了行政机关根据社会情势变化针对具体行政管理事项所进行的处罚裁量。尽管这些或具体或一般的裁量可能还存在合法性质疑,但裁量活动的背后无不彰显出行政机关对特定时期公共政策的考量。具体来说,以“三不罚政策”为代表的“工商新政”体现了行政机关对中央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政策的充分考量,试图通过免予处罚的裁量积极贯彻“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公共政策;“吸烟被拘”的严厉处罚则是对建国60周年国庆安保政策的回应,试图通过“一律式”的铁腕执法起到立竿见影的震慑作用;“曝光醉酒驾车”则体现出交管部门对当下酒后驾车交通违法形势日益严峻的清醒判断,试图通过具有“示众情结”的曝光手段的运用遏制酒后驾车违法行为的发生。
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行政执法活动过程中,公共政策事实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透过行政机关的裁量活动,不难看出公共政策始终隐藏其中。大体上来说,公共政策是以两种方式进入行政裁量过程的:一是行政机关基于对特定时期社会公共政策的判断直接援用作为个案具体裁量的依据,“南京曝光醉酒驾车”即属此类情形;二是较高层级的行政机关根据特定时期社会公共政策的现实需要,制定具有裁量基准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供一线行政执法机关使用,“浙江工商新政”和“重庆吸烟被拘”即属此类情形。虽然影响方式有所不同,但公共政策对于当下行政裁量活动的导引却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一般的解释,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就政策的下位概念而言,公共政策指的是国家公权力主体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为解决特定公共问题、完成特定公共任务所制定的行动准则。公共政策基本的价值衡量标准在于设计出“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和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观念,即具有社会可行性,又符合政策者的既得利益和意识、目标,即组织可行性的政策”。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大体上来说,中央人民政府所制定的宏观政策(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政策)及专项治理政策(如部署对某项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行动)、地方人民政府所制定的区域政策(如北京等特大城市对车辆限行的政策)及临时性政策(如春运等特殊时期的临时性政策)都可能成为一线行政执法机关重要的裁量依据。
公共政策为什么能够左右行政机关的裁量?在我国的现实语境中,也许可以寻找到很多直接原因,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与行政裁量的实施者往往具有高度的重合性,灵活应变的公共政策对僵化法律规定的补充性,行政官僚系统内部长期存在的“依政策行政”的路径依赖性,等等。进一步的观察则显示,公共政策与行政裁量在价值追求上的趋同性则是这种影响作用的根源。按照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拉雷・N・格斯顿的解释,公共政策的创造完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公共政策的产生,是问题累及社会的一个部门或若干部门达到了要采取行动的程度,问题的产生先于政策,人们在一段难以接受的时期中都有相同的问题而迫于应付,却无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一项公共政策的形成往往都代表着政策制定者对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形势的冷静判断和特定行政任务的总体宣示。毫无疑问,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这种决断能力来源于其公共利益代表者身份的正统性、信息收集反馈机制的灵敏性和价值追求上的个人偏好性。正如美国学者克鲁斯克等人所言:“公共政策的价值观,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涉及决策过程的人的共有的偏好、个人愿望和目标价值观,还可能包括一个人的政治信条、个人偏好、组织目标及政策取向等。政策制定的目的可能反映了那些涉及政策制定过程的人的内心主观愿望和他们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看法。”如此一来,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即为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和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描绘出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任何与法律实现有关的活动,无论是公民的守法还是国家机关的执法和司法,又都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完成的。因此,公共政策对特定社会时期行政任务的宣示,实际上就已经为行政机关的裁量活动、勾勒出基本的社会场景,与其说此时的行政裁量活动是按照法律规范进行的,还不如说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支配行政裁量活动事实上的“帝王条款”。
二、公共政策导入行政裁量过程的消极影响
在当下中国,公共政策在行政裁量过程中的导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作为行政裁量基准生成的智识源泉,还是个案具体裁量活动的理由说明,公共政策都真实地嵌于行政裁量的过程之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公共)政策作为规范和控制行政自由裁量行使过程的结构性处分,起到连接和沟通宽泛的裁量权和具体个案之间的桥梁作用,是行政自由裁量实践离不开的一种要素,它对于贯彻法律,对于稳定、连贯、准确地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来讲,无疑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事实上,除了具有引导行政裁量活动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及滞后外,公共政策导入行政裁量过程还能够有效缓解一线行政执法人员的社会压力。现代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人际交往乃至个人社会发展的重要武器。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当行政相对人遭遇行政处罚时,大多会动用社会资本去影响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决断。而执法者的心理防线一旦被社会资本所突破,则“同案异罚”、“处罚不公”、“滥用裁量”等现象就几乎无法避免。然而,在裁量过程中引入公共政策的考量则能够有力抵挡社会资本的侵蚀,执法者可以遵循公共政策为由实施相对公正的处罚,进而消解现实生活中人情因素的影响。
虽然公共政策导引行政裁量的优点十分显见,但过多依赖公共政策的行政裁量却同样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还会引发行政裁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例如,在前述“重庆吸烟被拘”和“南京曝光醉酒驾车”事件中,人们所普遍诟病的是:对于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的吸烟行为法律已经规定了明确的阶梯式处罚幅度,为何个案处罚偏偏一律选择最为极端的处罚种类?对于醉酒驾车行为法律同样明确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执法机关为何又在法外另行施以更为严厉的曝光制裁?进一步的观察则显示,公共政策导入行政裁量过程之中极易助长裁量怠惰和运动式执法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
第一,公共政策导入行政裁量过程容易助长裁量怠惰现象的发生。裁量的存在为行政机关提供了在法律约束之下自主做出决定的机会。裁量的终极意义无非是为了实现特定个案的正义。即使是作为约束具体裁量权行使的裁量基准,其目的也仅仅是限制而非消灭裁量空间。例如,在德国,“当裁量基准与个别裁量发生冲突时,应当审查裁量基准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适法性。较为平衡的方案是:行政机关应当接受有关裁量基准的约束,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撇开这个约束”。可见,无论是否存在规范意义上的裁量基准或公共政策,行政机关仍然必须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选择并做出最终处理决定。然而,当下的行政执法实践却正在走向与传统裁量滥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行政机关动则以公共政策为由,完全放弃对个案具体事实的细致考量,不加任何思考地做出与上级命令、通知、文件完全“对号入座”式的决定。如在前述“重庆烟民被拘案”中,执法部门对赵某吸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情节不加任何考虑,仅以非常时期安全保卫政策的形势需要为由而直接适用公安部“8・20”通知做出拘留5日的处罚。这种完全忽略个案具体情境的简单格式化做法从根本上违反了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目的,属于典型的裁量怠惰现象,与裁量逾越、裁量滥用等情形一样构成了裁量瑕疵。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叶俊荣教授甚至还认为:“法规授权行政机关针对具体案情为裁量,该主管机关便应全力以赴,若因其疏忽、误解,乃至有意认为对该事项没有裁量权,死守僵硬的政策、方针或‘上级’之要求,根本未深入具体案情为裁量,仍属裁量权的滥用。”令人担忧的是,类似吸烟一律拘留式的处罚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呈现蔓延之势,“一律取缔”、“一律关停并转”、“重拳出击”、“绝不手软”等词语充斥于坊间,行政机关对此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了。可见,过分依赖政策进行执法不仅会使法律规定被束之高阁,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裁量的本意,完全超越了社会容忍的限度,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第二,公共政策导入行政裁量过程加剧了运动式执法模式的蔓延。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运动治国传统的国家,运动式思维也渗透进行政执法过程之中,“选择特定时期、特定对象,集中执法力量进行专项整治行动”便构成了运动式执法模式的基本内涵。运动式执法的优点在于能够针对特定领域的违法情形迅速形成高压态势,从而在短时期内有效遏制违法情形的发生,尽快恢复特定行政管理领域的基本秩序。例如,前述“南京曝光醉酒驾车”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近年来醉酒驾车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已经对公共安全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为此,自2009年8月15日起,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可见,南京交管部门的曝光“创举”是与当下特殊时期的酒后驾车违章处理政策所营造的社会情境分不开的。但是,运动式执法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其内在的随机性和选择性。也就是说,运动式执法只是选择在一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对象施以重罚,等到运动结束之后,高压之前的违法情形便再次涌现。这也正是当下中国行政执法的困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动式执法就是选择性执法的代名词。在运动式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裁量几乎都是机械援引公共政策的结果。以“曝光醉酒驾车”为例,撇开其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暂且不论,是否需要曝光、针对哪些违法者进行曝光,都完全听凭于行政执法者的一己好恶。这种政策导引下的裁量不仅会造成行政处罚的不公,而且还极易引发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可见,过分渲染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的导引,容易加剧运动式执法的蔓延,进而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执法不公。
三、行政裁量过程中公共政策的规范路径
上文分析已经显示,公共政策无论对个案的具体裁量还是一般基准的制定都存在事实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本身也是正负双重的。对于这一社会客观现象,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而一概排斥,也不能唯其马首是瞻而一味容忍,正确的态度是通过一系列有效法律机制的建立,将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的导引作用纳入到法律可控的范围之内,进而实现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运作的良性指引。深入的分析显示,事前预防、事中说理和事后审查三重机制的建构有助于实现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的正确导引。
首先,通过有序和有效的公众参与,保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防止非正义的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的误导。行政裁量过程中公共政策的规范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就在于“如何形成好的公共政策”,因而事前的预防机制分外重要。事实表明,没有充分而有效的公众参与,不仅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难以保证,即便公共政策本身的合法性也存在质疑。例如,最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面对公众的广泛质疑,不得不发文“暂缓实施”原定于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等4项标准。按照这一标准,“重量在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两轮车”(一般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将被划入机动车范畴,实现与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无缝对接”。然而,一旦启用这一新标准,国内目前2000多家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将面临倒闭危险,1亿多消费者的出行将成为难题。正是由于“电摩”行业发展政策的形成根本就没有充分听取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因而才出现了上述尴尬收场的结局。仔细审视当下的行政执法活动,作为裁量依据的诸多公共政策都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础。以“烟民被拘”系列处罚案件为例,作为其直接依据的公安部“8・20”通知不仅没有正式对外发布,而且也从未听取公众的意见。这种封闭的政策生成模式切断了公众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公共政策民主性的缺失几乎注定了依其进行的裁量活动无法获得起码的社会认同。所幸的是,依托公众参与增强公共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已经逐渐得到官方的积极认可,并已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要文件之中。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应围绕“有序”和“有效”两个维度展开,避免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而缺乏实际效果。此外,鉴于当前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的导引大多是通过融入裁量基准的制定过程之中而实现的,因而可以通过裁量基准生成模式的变迁来防止非正义的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的误导。总的来说,事前预防机制的建立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形成起到重要的过滤作用,尽可能避免瑕疵公共政策的出台。
其次,通过事中充分说理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行政机关个案裁量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共政策导入裁量过程的负面影响。正如前文所言,过分依赖公共政策容易导致裁量怠惰情形的发生,进而违背裁量追求个案正义的要义。为此,就必须建立完备的说明理由制度,保障行政机关能够在具体个案的裁量中综合权衡法律规定、政策要求及特殊情境,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大体上来说,需要充分说明理由的事项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个案裁量是否需要考虑特定公共政策,这涉及法律规范的明确性程度与公共政策的补充性、拓展性之间的判断;二是个案具体情境是否构成公共政策的例外情形,这涉及公共政策预设情形的普适性与个案情形的特殊性之间的判断;三是个案决定是否能够逃逸浸润政策意旨的裁量基准,这涉及公共政策、法律规定及裁量基准现实效力的判断。以前述“烟民被拘”案为例,在对赵某吸烟行为如何处罚的裁量过程中,执法者就必须完整地考虑如下因素:《消防法》第63条所规定的三个处罚格次与公安部“8・20”通知一律拘留5日顶格处罚之间的关系;“具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的不确定概念与赵某实际吸烟地点之间的关系;“情节严重”的不确定概念与通知中“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以及赵某个人申辩情节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从公开的报道来看,仅仅是上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在案件发生之后才通过媒体对“烟民被拘”的时间、地点、情节等因素进行了“补充性”说理。这种事后说理不仅在形式上不能证成先前拘留处罚的正当性,而且理由本身能否成立也不无疑问。很显然,离开了充分的理由说明制度,不仅无法保障行政处理决定的可接受性,而且会助长裁量怠惰情形的泛滥,最终必将导致法律之下的裁量为公共政策下的裁量所取代。因此,加强多维度的说明理由制度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最后,通过事后司法审查机制的完善,保障行政裁量过程中的政策判断取舍获得独立公正的外部评价,实现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的良性引导。与民事活动须遵守政策已经成文化所不同的是,公共政策对行政行为的约束作用在我国尚未获得成文法律规范的明确宣示。不过,极其有限的司法实践已经表明法官在处理行政争议的过程中开始对公共政策加以判断。例如,在“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的处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中就展示了对国家“西气东输”等公共政策的考量。事实上,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事前预防机制和多维度的事中说理机制即使再完备,也无法完全避免行政裁量争议的发生。因此,赋予司法机关针对行政裁量对公共政策判断的独立审查权殊为重要。在以往的观念中,似乎司法机关应当对行政裁量过程中的政策判断持尊重态度,不宜以自己的判断取代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诚然,法官不是行政管理的行家里手,不能完全取代行政机关在裁量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的判断。但是,法官是法律问题的专家,不仅有责任审查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更有责任维护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在我国目前大力宣扬司法能动主义观念的社会大背景下,行政审判更应肩负起公正化解行政争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神圣使命。因此,在围绕行政裁量活动是否合法、是否正当的争议处理过程中,法官应当怀着法律至上的理想,通过对法律位阶原理的运用和法律精神、法律原则的阐释,对行政裁量过程中的政策判断因素进行独立的外部评价,真正为公共政策对行政裁量的良性导引提供制度支撑。
四、结语:寻求行政裁量法外控制的尝试
欧洲法社会学的巨擘埃利希在阐释法社会学原理的精髓时曾言:“在当代以及任何其他的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按照这一理解,对行政裁量的控制―这一行政法学历史长河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破解也不能,或者说至少不能完全寄望于法律内部的资源和技术。事实上,行政裁量的运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除了法律规范因素的考量之外,公共政策、行政惯例乃至新闻舆论、信访等众多法外因素也正深刻地影响着行政执法者,甚至成为左右行政裁量的关键因素。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我国当下兴起的裁量基准制定热潮中,“违法事实被新闻媒体曝光或经群众上访造成恶劣影响的从重处罚”的条款频频出现。因此,在传统的行政裁量立法、行政、司法三重法律控制之外,能否寻找更为妥当的法外控制技术进而形成内外交织的行政裁量运作规范体系,便成为当下行政法学研究特别是行政裁量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对行政法学者智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考验,而且其间也蕴涵着行政裁量研究的某种契机。本文对公共政策进入行政裁量过程的初步观察和规范路径思考即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行政裁量法外控制更为深入的研究亟待展开。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