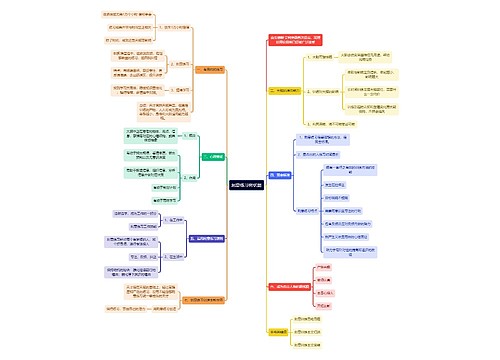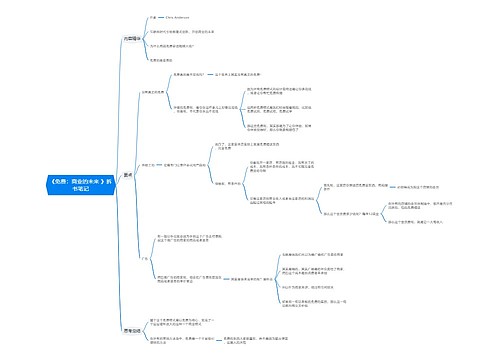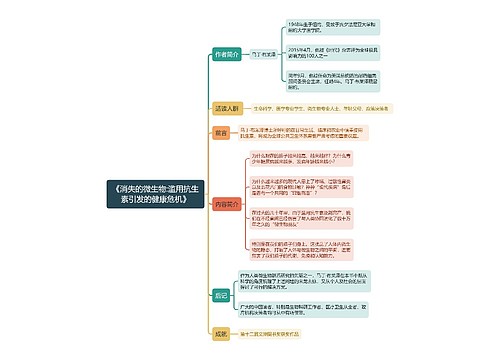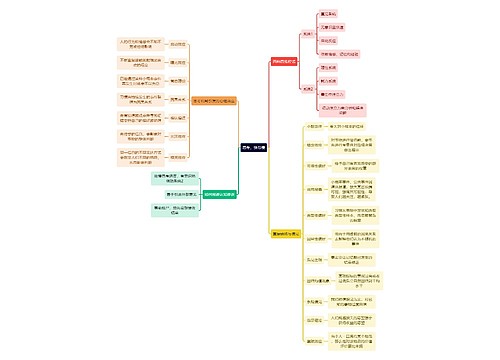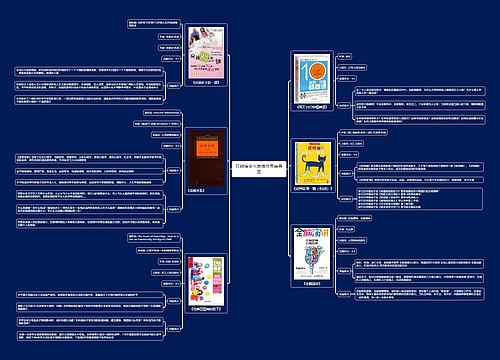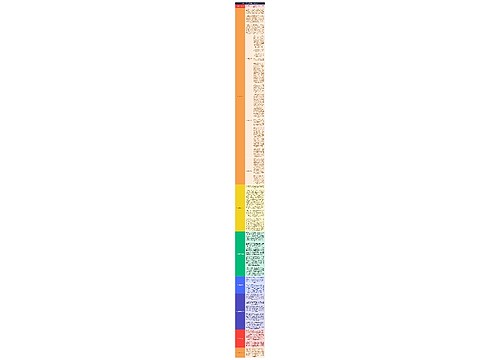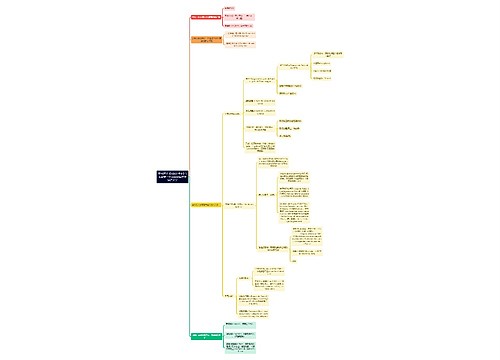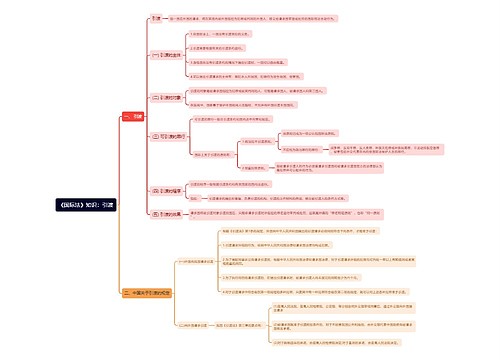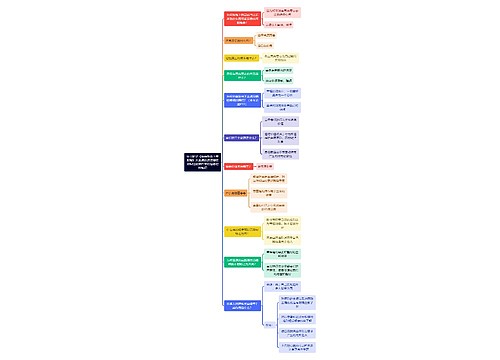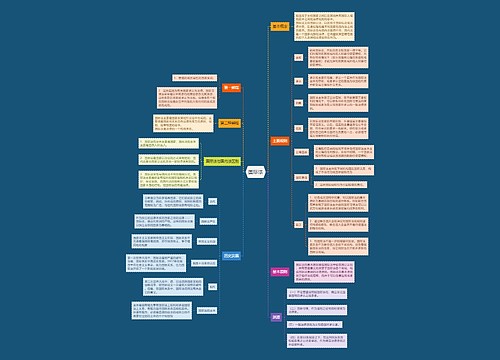读书笔记《第一哲学沉思集》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思维导图
ZYJ
2022-10-30

任何事务都可以被怀疑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读书笔记《第一哲学沉思集》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读书笔记《第一哲学沉思集》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a6a497959da60686de3927943464f307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