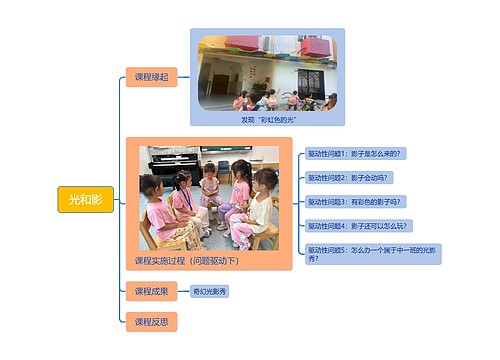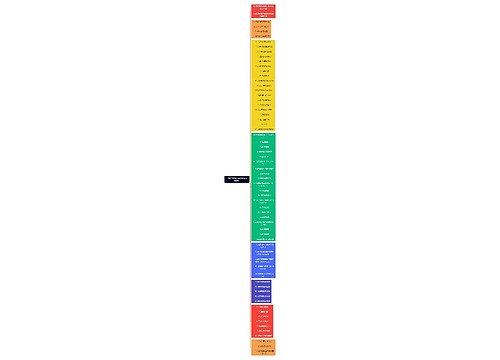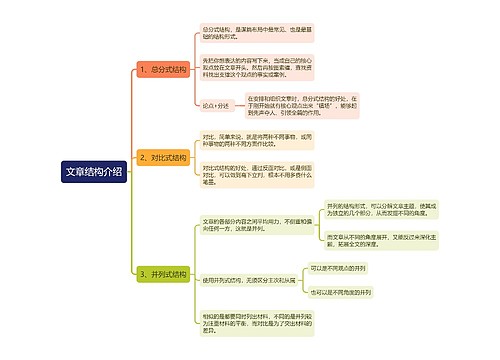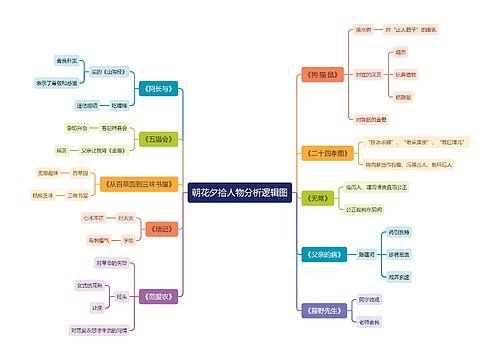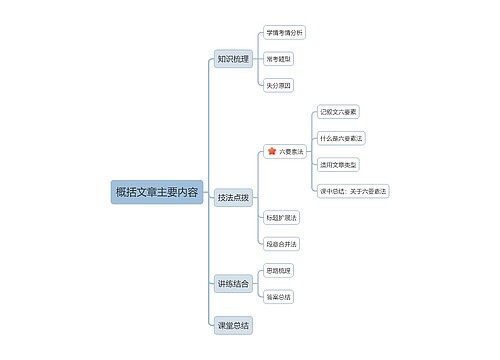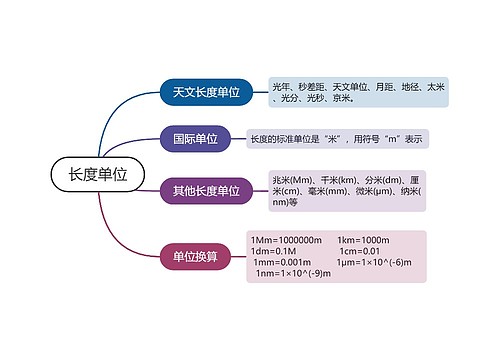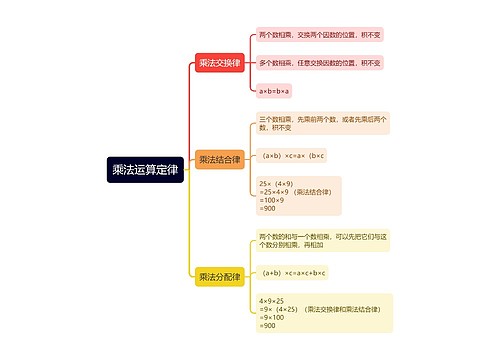路旁,零落的杏花沉沉睡去,残存的杏花瑟缩哭泣,于风中飘摇。春风吹过,激起心底的层层涟漪,撩拨心中的迷蒙情思。
小时候,您常带我去田里玩,田间小路是最有趣的地方。清晨,薄雾消散,太阳被水汽遮挡,圆圆的,红红的,像树上垂下来的苹果。路旁,刚刚睡醒的高粱稍稍抬起头,露出浅浅的笑意,成千上万的小麦仰着脸,吮着露水,吻着阳光。小路前头,蝶儿纷飞,好鸟相鸣。
园子中央搭建起一个过夜的棚子,一张床,一个手电筒,就再无其他了。棚外有两个木制躺椅,夏天,倚在躺椅上,木头的凉意浸入血液,头顶的丝瓜沿着架子向上爬,丝瓜秧挤成一团,在头顶密密麻麻地躺着。近处的菜畦种着自家吃的蔬菜,大多青绿色,有的已冒出花来,视线远处,彩蝶振翅飞舞,白云缓缓游过;近处,脚边伏着玩累的小狗小猫,鼻息微动,似已沉沉睡去。
每到这时,爷爷总是走过来舀一瓢井水,喝罢,就走到我身旁,搂着我,讲起往昔的故事,讲起曾经的绿军装,黄土地,难得的白馒头和头顶永恒不熄的红星。爷爷身上汗味混着泥土的气息,夹杂着淡淡酒香,让人的心神回到那一段光辉岁月。
秧苗筛过的阳光,薄薄细细,洒在脸庞上,晕染着时光的静好。爷爷累了,就递给我一把小镰刀,让我去割草。我赤脚走在田垄上,清清凉凉。我捏着小镰刀,嘀咕着野草长什么样呢?回想着爷爷割下野草的模样:长茎,头上顶着长长圆圆的穗子。于是,我就蹦跳着去割草,手里拿着一把青色的野草向爷爷跑去,轻轻摇醒爷爷,在他面前挥舞着“战利品”。
爷爷眨了眨眼睛,看看我手里的东西,笑容似花朵一样瞬间绽放。“爷爷,你看我干得好不好?”“好啥呀!”爷爷笑着看我。“怎么不好了?你看这不就是你天天割的杂草吗?”我急得想要跳起来。爷爷从我手中抽出两根野草,一手拿一个,说:“这个是麦子,有芒针的。”说完还摇了摇,“这个呢,毛嘟嘟的,就像狗尾巴,这才是野草。”
我低头看了看脚旁狗的尾巴,捏住摇了摇,说:“这也不像啊。”然后我就从爷爷宽厚的手掌中挣开,追着一只白蝴蝶,直到它轻飘飘地飞到阳光里。
窗外,绵绵细雨连成线,勾出一点惆怅。生命的长河中,我仍乘舟疾行,你已坐看岸上芬芳。一滴泪,随着雨,流过心尖。
小时听说人最终会化作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曾经的我总是仰望天穹,寻觅流星踪迹,却只能暗自叹息。此刻回首往昔,惊觉或有星光悄悄划过。是泪光?还是你在云际浅笑?
清明里,思绪飘过迷蒙烟雨,只想向你道一声:我很好。再问一句: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