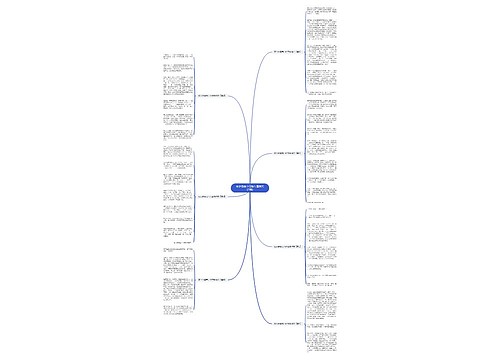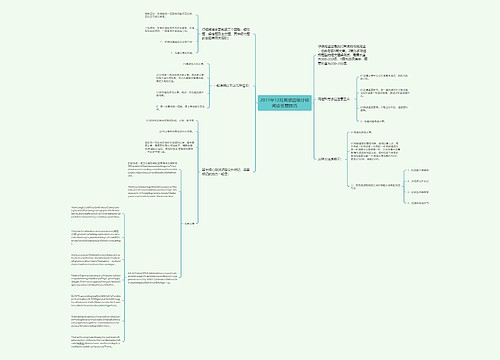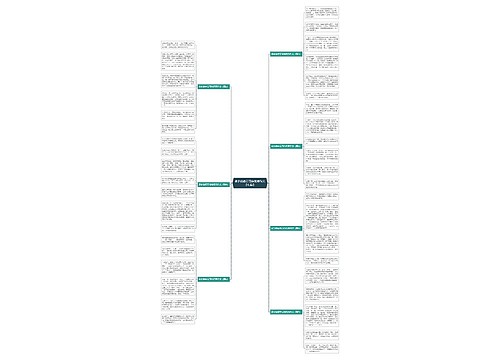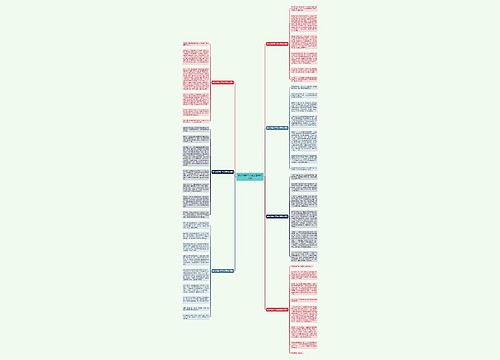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思维导图
活在故事里
2023-0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2 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这一规定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自首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党和国家一贯实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4bc9aead5d90a40370806c9da38c11df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