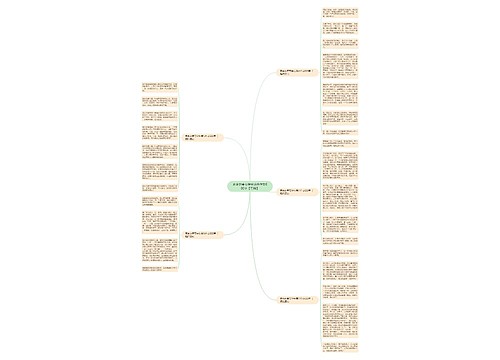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在新刑法中表述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而在学理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立法表述和学理表述在逻辑上具有互为逆否命题的关系。立法表述针对的主体主要是司法机关,而学理表述针对的不仅仅是司法机关。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这两种表述都把罪刑法定原则的“罪刑必须由法律明定”揭示了出来。
众所周知,刑法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犯罪和刑罚是其主要内容。一部刑法典在起草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对犯罪定义的界定,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怎样才能明确回答“什么是犯罪”这一问题,就成为一部刑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什么是犯罪”这个问题回答的科学与否,不仅是能否为判断罪与非罪提供科学的基准,更因为它是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能否具体贯穿整个刑法典的前提。
犯罪是一种社会法律现象。犯罪的定义应该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大前提下对犯罪内在外在特征的高度概括。一般而言,它是由国家以刑事法律形式加以明文规定的。西方国家从行为是否应受到刑事制裁的法律特征上界定犯罪定义。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规定:“法律以违警罪所处罚之犯罪,称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而我国新刑法则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实质特征,结合刑事危害性和应受惩罚性,界定了犯罪的定义,新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那么,对上述两个类型的定义比较一下,哪个更为科学呢?这里就涉及到以规范标准和以社会危害性标准界定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问题。
所谓规范标准,即是否犯罪以法律规定为标准。也即看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而所谓社会危害性标准,即罪与非罪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否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标准。规范标准的优点在于其具有明确性,而社会危害性虽然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属性,但由于其居于现象的背后,一般很难一目了然。
现代刑法的精神主要体现在罪刑法定上,而罪刑法定的要义在于:禁止事后法;除有利于被告的法外,法无溯及力;禁止类推;罪刑的明确性这四个方面。如果在犯罪定义的界定上,选择了社会危害性作为标准,那么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首先,社会危害性本身具有笼统、模糊、不确定性。有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很明显,如抢劫、杀人、放火等,而有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一时很难判断的。例如商业活动中的回扣、投机等行为,在过去,投机一直是作为危害社会的犯罪予以打击,而今,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却成为促使市场富有流动性和具有朝气的积极的攻击性有益社会的经济行为,有的人甚至认为行贿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他们认为贿赂是社会经济运转的润滑剂。据称,在当前有些政府机关,官僚作风严重影响行政效率。有的公司如果按正常正当程序,拿到批文,最少得三个月,一旦给具体主管官员行贿,不到三四天,批文就会到手。时间就是金钱,市场如战场,风云变幻,机遇稍纵即逝,交易机会不等交易者,因此给破旧得吱吱叫的行政机器一点润滑剂,或许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另外,社会危害性也有地域性,在有些地域如“金三角”地区,种植毒品原植物,对于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来说,是很有益的,因为其他农作物,根本在那个地方不生长,而毒品原植物在当地长得比其他地方较好。但对于其他国家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这种笼统、模糊、不确定性是不利于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
其次,社会危害性标准应是立法者、法学研究人员确立犯罪行为规范的重要因素,司法者和一般公民只能根据刑法规范一目了然地进行行为对照判断,而没有判断“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的注意义务,如要确立社会危害性标准,那是对司法者和守法者的苛求。
通常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因而,它并不是一个法律规范上的概念。如果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去认识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犯罪的本质属性-社会危害性,这是立法机关、法学家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对犯罪的认识。一般的行为人则是从本人的立场上对行为在既有的参照系前提下进行对照判断,而且行为人的认识水平各异,很难否定有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作各种自以为是的肯定评价。例如轰动全国的蒋爱珍杀人案。被告蒋爱珍,系一个未婚女青年,无辜遭受领导设套“捉奸”、画漫画侮辱、大小会“批判”等极端迫害,求告无门,遂无奈持枪报复杀伤数人。此案中,蒋爱珍本人并不认为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全国成千上万民众的强烈声援,普遍认为受害人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甚而认为死有余辜。因此,没具体规范标准的社会危害性认知,并不能很明确切实地告诉行为人“什么是犯罪?”
再次,社会危害性又是罪刑法定的对立面,即刑事类推适用的前提。刑事类推是指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法律制度。刑事类推的历史在我国源远流长,有些同志曾把其作为“中国特色”在修改刑法期间极力要求保留。其理由在于类推可以密罗刑事法网堵塞刑事立法漏洞,企图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刑事控制模式。然而,在事实上,刑法不仅具有社会保护机能,实现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力,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人权保障机能,保障社会公正和公民自由权不受无辜侵犯。刑事类推制度实质是选择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类推违背了立法与司法分权的法制原则,为司法权僭越立法权,法官造法提供了根据。刑事类推的存在大大缩小了公民自由的权利空间,背离了世界刑法发展轻缓化大趋势。
与罪刑法定相背离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存在”所确立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定义界定标准是其运作的基础。即:如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最相类似的犯罪程度,则适用类推。否则,就不适用。那么,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大小,就只能以既存的犯罪的具体规范标准来衡量,而不能以社会危害性为标准衡量是不是犯罪。因此,只能以犯罪规范来体现社会危害性,而不是相反。
在新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定义中使用了“危害社会”字样,突出了社会危害性,并用“危害不大”字样,强调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对罪与非罪的决定意义。这样,就反映出在新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存在社会危害性标准;
除此之外,这个定义在逻辑上也存在矛盾。“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从这样的定义分析,除了“一切”之后所列6类行为之外,均不是犯罪; 在“一切”这样的外延之下,但书是不应该存在的。要么,用“一切”就不用但书,要用但书就不应用“一切”。从另一方面看,在以规范为界定标准的情况下,“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这几个字所表达的内容完全可以把但书所讲的内容包含进去,如果再讲但书,就有重复之嫌。因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当然就不具有“应当受刑罚处罚”性,立法机关肯定不会把这种行为规范进刑法典之中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是不是犯罪,若刑法典认为是犯罪,就是犯罪;刑法典不认为是犯罪,那么这样的行为就不会写进法典,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的罪刑法定原则,但书所述行为肯定不为罪。故但书部分纯属画蛇添足之败笔。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并非只是废除刑事类推制度,将罪刑法定原则明文写进刑法典那么简单,在整个刑法中如何一以贯之地体现罪刑法定的原则精神,实现刑法的科学化仍任重而道远。

 U633687664
U633687664
 U482683014
U48268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