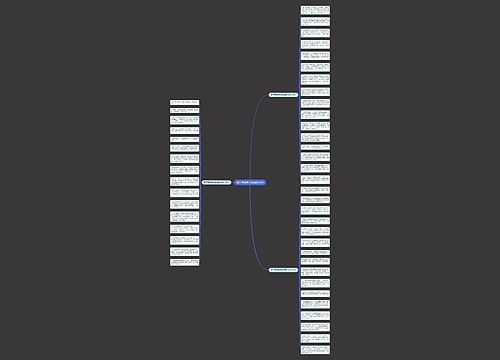宪法教学应重视“宪法人”的培养思维导图
不爱计较
2023-03-15

宪法
培养
教学
重视
法律
解释
宪政
我们
学生
法学
法律论文
宪法论文
关键词: 法学教育/宪法教学/宪法意识/宪法人/宪法教师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宪法教学应重视“宪法人”的培养》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宪法教学应重视“宪法人”的培养》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28506d07b5e62d7ab015688897d69d32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宪法教学应重视“宪法人”的培养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内容提要: 宪法人是指真心诚意地信仰宪法,具有宪法意识,并时刻按照宪法的基本精神去生活和工作的人。作为法学核心课程,宪法教学应重视“宪法人”的培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宪政的客观需要,是法学教育的当务之急,也是宪法教学的分内之事。宪法教师首先要成为“宪法人”,在教学中要注意对现行宪法文本的尊重,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要充分体现宪法精神,并重视宪法应用的教学。
一、什么是“宪法人”?
所谓“宪法人”,是指真心诚意地信仰宪法,具有宪法意识和思维,并且时刻按照宪法的基本精神去生活和工作的人,即具有“宪法生命素”[1]的人。较通俗、较具体地说,宪法人就是具有把每个人当作人,平等、宽容地尊重和对待每个人,时刻守规矩,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等宪法精神并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身体力行的人。
宪法是法上之法,法律的法律。应该说,真正的法律人应当也是宪法人,甚至首先是宪法人。显然,培养“宪法人”是法学教育的使命,是所有法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宪法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作为教育部法学教学委员会所认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宪法课程的教学更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宪法思维和宪法信仰,重视“宪法人”的培养。
二、宪法教学重视“宪法人”培养的必要性
1.培养“宪法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载入我国宪法。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正如温家宝总理2004年3月31日在主持国务院第三次学习讲座时所指出的:“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2]
实行依宪治国,实施宪法,不仅需要违宪审查制度的保障,而且要求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宪法意识,有遵守宪法、执行宪法和维护宪法的风气和习惯,人人都成为具有宪法意识的“宪法人”。这也是我国宪法的明确要求。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明文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胡锦涛总书记200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长期抓下去,坚持不懈地抓好。”“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一体遵行。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宪法,让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各级党校和干校都要开展宪法教育。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3] 显然,在大学法学教育特别是宪法教学中大力开展宪法教育,想方设法地提高学生的宪法意识,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宪法意识的“宪法人”,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2.培养“宪法人”是实现宪政的客观需要
宪政是立宪政治或宪法政治,是建立宪法之上的政治,是宪法在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充分实施所形成的民主政治体制。[4]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相应地,建设法治国家也就是建设宪政国家,实现宪政。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宪政呢?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梁漱溟(1893-1988)先生早在1944年就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宪政并不建筑在宪法上面。宪法不过是事情确定之一种形式”,宪政建筑在“势”和“理”上,建筑在“外力”和“内力”两种力量上。(一)所谓“势”或“外力”,就是“谁亦不敢欺侮谁”。他说:“宪之所以由立,盖有其不得不立者也。质言之,正为彼此都有力量而不可抹杀之故。既经要约而生了解,随后亦就只有循守遵行下去。”“宪政是建筑在国内各阶级间那种抗衡形势之上。”(二)所谓“理”或“内力”,就是精神力量。他讲:“自由平等,民主,并非全由外铄,而是人心所本有之要求。人类社会不徒有‘势’,亦还有‘理’。例如:对于某些道理的信念,正义感,容人的雅量,自尊心,责任心,顾全大局的善意,守信义的习惯,等等亦是宪政所由建立,及其所由运行之必要条件。我所谓内力,或自力或精神力量,即指此。假若没有这一面,宪政亦岂可能!” 由此,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没有产生宪政,中国近数十年宪政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既没有各种相互抗衡的“外力”,又没有精神力量即“内力”。他说:“宪政之出现西洋,实由西洋社会充满了各种力量,此为中国数千年不产生宪政对照来看,尤为显然。——我意盖指中国缺乏阶级。又若论英国宪政成绩之好,则不能不归功于其精神力量。——此又可与中国近数十年宪政运动之失败,相对照。”[5]
3.培养“宪法人”是法学教育的当务之急
早在1935年,近代著名法律教育家、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代理教务长(1933-1939年)孙晓楼先生在其《法律教育》一书中就指出:“法律的事业,是公益的事业,是社会的事业。”“研究了法律,不能为社会服务,为公众谋利益,而专为自己个人寻好处求享用,这不能叫人才,更不能算做法律人才。”“法律人才,不是在于做律师的大小,也不是在于官职的高低,更不是在于赚钱的多少,而是在于他所做的事业于社会公众的福利上到底有多少的努力和贡献。”[7]
然而,近些年来,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因违法犯罪而被抓、被判刑的新闻时有耳闻,其中一些还是省高级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2008年更有最高法院副院长被“双规”,令人震惊!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学法律出身的,毕业于正规的法律院校。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人知法犯法?正如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海峡交流基金会首任秘书长、我国台湾地区的国际法学会理事长陈长文先生所追问的:“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8]
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原因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故有必要特别予以关注,那就是法学教育本身的问题。在各大法学院校,法科学生有上课迟到的,有早退的,有旷课的,有考试作弊的,在食堂有不排队的,在图书馆有看书乱放的,甚至有撕书和偷书的,在校园里有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在大街上有乱闯红灯的。我们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在遵守规矩方面,学法律的学生与非学法律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在公益心方面,法学院的学生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相比,也没有突出之处。许多同学只想到自己,学法律的目的只是谋个好职业,只想在毕业后能赚大钱或者做大官,而有几人立志为我国的法治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呢?!我们的法科学生太功利了!我们的法科学生在法学院学习阶段没有养成守规矩的习惯和公益之心,其中一些人在毕业后从事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之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法学院的学生未能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各大法学院,我们的老师往往只注意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讲授和法学理论的灌输,而不注意法治理念的培养,法律没有真正成为我们法科学生的信仰,守法没有成为我们法科学生的行为习惯,更没有成为一种文化。由此可见,培养法科学生守规矩的习惯和公益之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当务之急。而宪法强调行使公权力者守规矩,要求人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成为“宪法人”,显然宪法学教学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是特别突出的贡献。培养“宪法人”,也就成为法学教育特别是宪法教学的当务之急。
4.培养“宪法人”也是宪法教学的分内之事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有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并严格得到遵守,违宪必究,要求公权力行使者必须守宪守规矩等。显然,这需要各方面的长期努力。任何一个人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固然,我们可以写文章,积极呼吁,或许会产生一些影响,但作为一名大学法学教师,其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培养法律人才!显然,培养“宪法人”是我们宪法学教师的分内工作,是能够做而且应当做好的工作!
三、我们在宪法教学中培养“宪法人”应做的工作
培养“宪法人”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我们至少可以做好如下工作:
1.宪法教师首先要成为“宪法人”
打铁还须自身硬!只有我们宪法学老师自己首先成为“宪法人”,才有可能把法科学生培养成为“宪法人”。我们不难发现,在全国各种大大小小的法学会议上,一些法学家包括大家所敬仰的法学名家、大腕在主持会议时往往喜欢客串承当一下评论人,在把握发言人的时间上则往往厚此薄彼,而在自己主题发言或担任评论人时却常常超时。在其他场合,甚至有个别法学家在平时面对学生以及发表法学论文时大谈自由、平等、法治和人权,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样喜欢享受特权甚至大耍特权。显然,这种法学家和老师是难以培养出“宪法人”、法律人的!由此可见,我们宪法学教师首先成为“宪法人”,是我们在宪法教学中培养“宪法人”的前提。
2.在教学中注意对现行宪法文本的尊重
在宪法教学中,我们老师不仅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宪法知识的讲授和宪法理论的灌输,而且要注意宪法理念的培养,使宪法真正成为我们法科学生的信仰。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宪法教学中要注意对现行宪法文本的基本尊重。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院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法学院的教师们对待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往往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在课堂上动辄采用一种不屑一顾甚至嘲讽的口吻,对我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中的弊端慷慨激昂地加以指责;相反,对于西方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则大加赞赏并自觉和不自觉地把其作为讲授的重点。[9] 当然,宪法学教学也不例外。说实在的,本人过去在宪法的教学中也常常这样做。近年来,我和国内许多法学老师一样也在反思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想象,这种对我国法律和法律制度一味批判的教学方式导致的结果极可能是:我们法学院培养的法律人才对本国的法律没有好感,缺乏起码的尊重,甚至是蔑视。然而,法科学生以这样的态度去从事法律职业,在工作中怎么会认真地执行法律呢?!而连执法者都不能尊重法律,不能认真地执行法律,我们又怎么能建成法治国家呢?!显然,批判式的教学方式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执教者对本国法律进行宣泄式地鞭尸的结果,固然可能获得不少喝彩,瓦解的可能是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当一个法学教师在课堂上尽情宣泄自己对本国法律不满的时候,他是否会想到、是否应当想到这种宣泄的不满会产生强烈的传染性,从而培养出新一代蔑视自己国家法律的‘愤青’而使法学教育走向歧途?”[10]
3.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充分体现宪法精神
在宪法的教学中,老师们不仅要在课堂上充分讲解宪法的基本理念,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宪政理念,而且在备课、到课、授课、提问、考勤、组织讨论、布置作业以及考试、批卷评分等各个教学环节都要充分体现宪法精神,都要充分体现宪法的规矩、宽容、参与、公正等精神。言传身教胜过简单的说教,老师在教学各个环节的“宪法人”身教有利于促进学生“宪法人”的培养。言行务必一致!
4.重视宪法应用的教学
适用法律,首先应当解释法律。“法律适用是以法律解释为前提的,因而法律适用就是意味着法律解释,没有法律解释就不可能有法律适用。”[11] 正如德国学者魏德士教授所指出的:“一切文本学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任何类型的文本如果要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要进行解释。这对法律工作意味着:任何法律、具体的法律规定以及受合同约束的协议在能够恰当地适用或执行之前都需要解释。”[12] 既然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必须解释法律,那么它们应当如何解释法律?一般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此外还有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和社会目的的考量的社会学解释。[13] 其中,主张依照宪法来解释法律的“合宪解释”(“合宪解释”,又称“合宪性解释”。为区别于一些学者把违宪审查中那种如果没有确切依据认定法律违宪则应推定该法律合宪的“合宪推定”也称之为“合宪解释”或“合宪性解释”,更准确地表达其含义,笔者称之为“依宪解释”[14])是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15] 也就是说,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又必须进行依宪解释。所以,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法律进行依宪解释,是适用法律的应有之义,是适用法律的自然要求。同时,在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尚未有效运作的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开展依宪解释,也是当下中国宪法能够得以实施应用的重要途径,甚至是除立法机关依宪立法之外宪法实施应用的唯一途径。
为此,我们的宪法教学应当充分重视上述“依宪解释”的作用,重视宪法应用及其方法的教学,让同学们认识到即使在当下中国,宪法也是有用的,培养“宪法人”的思维,养成时时刻刻考虑宪法的习惯,心中始终有宪法,并掌握宪法应用的基本方法,真正成为一名“宪法人”。
注释:
[1] 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并担任过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和院长,《联合国宪章》的中译者,1935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48年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世界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1904-1979)先生认为:“重法的风气乃是法律的‘生命素’”,而“所谓‘重法’就是‘真心诚意’的奉行法律,也就是信仰法律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一种风气。”同时,他指出:“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制宪’,而‘宪法生命素’的培养。”显然,杨兆龙先生所说的“宪法生命素”就是尊重宪法的风气,重视和信仰宪法、笃信力行宪法规定或原则的风气,在生活行为上培养一种合乎宪法精神的习惯。参见杨兆龙著:《杨兆龙法学文选》,郝铁川、陆锦碧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45、59页。
[2] 秦杰:《认真学习贯彻宪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1日。
[3]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5日。
[4] 上官丕亮:《论宪政及我国通向宪政之路》,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3年第2期。
[5] 梁漱溟:《宪政建筑在什么上面?》,原载《大公报》(重庆)1944年5月1日,现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468页。
[6] 梁漱溟:《谈中国宪政问题》,原载《民宪》(重庆)1944年第1卷第2期,前揭书《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491、492页。
[7] 孙晓楼著:《法律教育》,王健编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8] 陈长文、罗智强著:《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法律伦理与理想的重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自序。
[9] 参见侯欣一:《当代中国法学教育之我见》,载《法学家茶座》第14辑,第31页。
[10] 张建伟:《给法律一点敬意》,载《检察日报》2006年11月13日。
[11] 陈金钊著:《法治与法律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12] [德]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页。
[13] 参见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4] 上官丕亮著:《宪法与生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15] 一般认为,所谓合宪性解释,指以宪法及阶位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阶位较低的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简而言之,是以宪法上的规定来解释民法上的规定。参见梁慧星著:《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