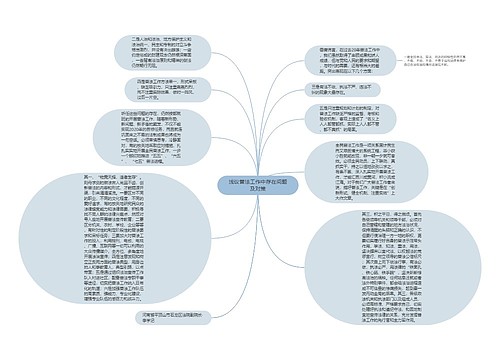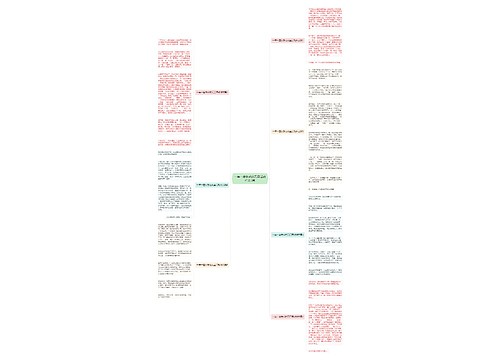从词源上考察,“理念”(英语:idea,德语:Idee)一词源自古希腊文(ειδs)/(eidos),原意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在其创立的理念论中剔除了“理念”一词的感性色彩,用来指理智的对象,即理解到的东西。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顶峰、最高的本体,认识只不过是对理念的回忆。这实质上是关于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他认为客观的理念并不与事物分离,它存在于事物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念有三种存在:第一,存在于事物之前,作为神心中创造世界的蓝图;第二,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本质(大体相当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理念”);第三,作为人心中的概念,即主观方面的思想。作为思想的理念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理念,意义有所不同,一般把思想的理念称为“观念”。
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重新规定了“理念”的含义。在康德哲学中,理念指理性所产生的概念,是理性应当追求的东西,但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是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所以,黑格尔说:“康德诚然使人知道重新尊重理念”,“但关于理念,他同样只是停留在否定的和单纯的应当阶段。” 黑格尔自己则将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是理性构成世界的元素。在自然哲学中,理念为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发展到人出现,而人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理念再复归为精神,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念。黑格尔认为人类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均为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虽然是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论述“理念”,但他那种融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于一体的“理念”,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最多。
在我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对“法律理念”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之理念。”以此为基点,史尚宽先生着重对法律理念与法律概念、法律目的、法律观念及法律理想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法律之概念,谓‘法律为何者 ’;法律之理念,谓‘法律应如何’。”而法律理念与法律目的的区别则在于“法律之理念,为法律的目的及其手段之指导原则。”“理念为理性之原理”,不同于感性的法律观念。至于法律理念与法律理想的区别,史尚宽先生则说得更为明确:“理念(idea)与理想(ideal)不同。理念为原则,理想为状态。理念为根本原则,为一无内容无色透明的不变之原则,基于理念作成理想状态,具体的实现理念之状态为理想。”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幸福”、“自由”、“博爱”、“平等”均带有感性色彩且动摇不定,均“不得为法律之理念”,只有“‘正义’为法之真理念”。史尚宽先生这最后的结论似乎又“皈依”到了新康主义施塔姆勒那里,加之他将法律理念看作“不变不易之原则”,有不少失之偏颇之处。
大陆一青年法学工作者则从本体论、知识论角度对“理念”进行“简略的清理”后认为,“法理念既是具体法形态的内在,同时也是法之本体的存有。差不多可以说,实在法、理性法、自然法都有自己的法理念或内在精神,然亦有交叉或综合的法形态的理念精神。”面对这一界定,另一青年学者看到了其中隐含“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指出“作者基本上是在与‘法精神’、‘法观念’含义相同的基础上使用‘法理念’这一概念的。”接着,他自己为法律理念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即“法律理念乃是指对一种法律目标指向的实现”。尽管这一学者对“法律理想”与“法律理念”作了专门的区分,但从其定义来看,仍然没有完全避免那种将 “法律理念”泛化为“法律理想”的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法律理念首先是对法律的本质、根本原则及其运作规律的理性认知和整体结构的把握。具体地说,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模式、法律信仰或信念、法律实践、法律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宏观性、整体性反思而构建的理性图型。作为其视域的对象、概念和方法,不是表层的、单向的、孤立的,而是本质的、立体的、普遍的,它摒弃人类关于法律的偏见,将人们关于法律现象及其本质的观念从感觉或经验状态提升为理性认知形态,从宏观和总体上把握法律的基本走势,图解法律与时代变迁的根本关系,为法律发展或进化提供理念准则和导引。简言之,法律理念就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一种理智的思想,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态度,是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第一,表征和指称功能,即法律理念具有对法律的表征和概念指称作用。法律并非向壁虚构的产品,而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产物,但又不可能自动生产出来。社会对法律的客观需要不可能直接具象化为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法律理念的表征和指称功能的转化。“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的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圆满的运用法律之原理。”法律理念首先反映和揭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然后通过法律概念的指称,再转化、整合为法律上关于各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认知,从而为法律创制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条件。
第二,中介和外化功能,即法律理念将立法动机具象化为法律创制工作,转换为法律规范。法律理念形成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认知形态上,必须外化才有意义。当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客观需要转化为立法动机以后,就要将这种法律动机转换为现实的法律规范。立法者通常运用法律理念对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模式进行评判和优化选择,使之客体化、定型化和制度化。可见,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法律理念构成了社会立法需求与法律制度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法律理念的外化使法律从思想上印证到现实中形成现实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法律理念,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模式。如我国古代以“泛刑主义”为其理念,结果形成了“民刑不分”的法律模式。而英美法律理念与欧洲大陆法律理念的差异导致重判例的普通法系与重法典的民法法系并行不悖。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法律理念仅仅是社会客观的法律需要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连接点,并不是法律产生的最终根源。法律的最终源头始终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关系。
第三,科学的预测功能,法律理念可以对法律制定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法律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只有依靠法律理念对现行或潜在的法律进行预测、认知和把握,才能对法律是否适应社会实际进行正确估价,及时作出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法律得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在论述立法问题时曾指出:“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这就是说,离开法律理念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洞察和科学预测,就可能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偏离社会实际,甚至出现“恶法”,造成法律实施的障碍。
第四,导引功能,法律理念对法律的运作有巨大的导引作用。法律理念不仅为法律发展指明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而且为人类实现这些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设计具体方案、方式和方法。要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运用法律理念对具体法律行为进行分析、评判以及对法律规范适用进行认知和优选,而且需要依据法律理念把握立法精神和对法律成本收益进行效益判断,以确立最佳实施方案。如果执法者和司法者缺乏正确的法律理念,非常容易出现执法或司法偏差,甚至出现执法或司法专横,而守法者一旦缺乏法律理念的引导,就不可能自觉运用和遵守法律,永远只能作“法律的奴隶”。
第五,文明进化功能,法律理念是推动法律制度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科学的法律理念有助于消除落后的法律文化,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扫除法律进化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障碍,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法治环境,充分利用民主法制机制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