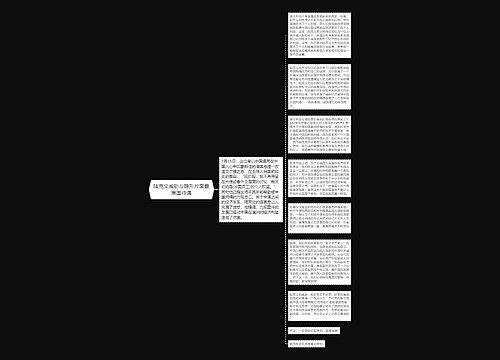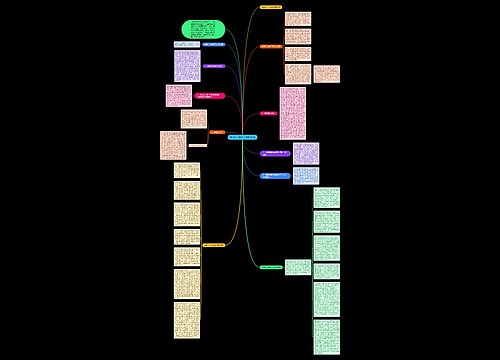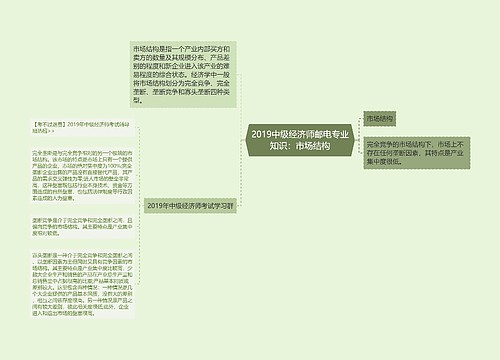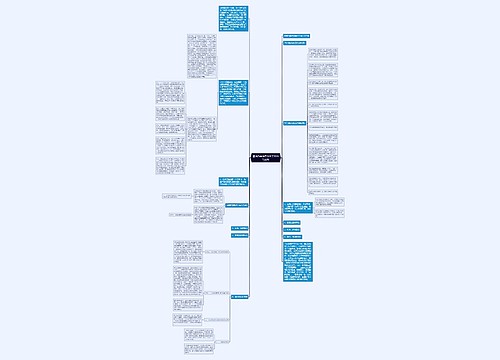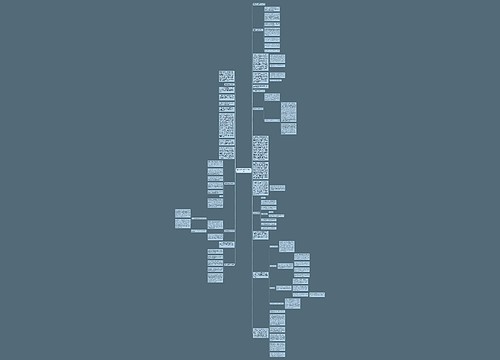条约制度:盗亦有道的现代解读思维导图
自我孤立
2023-03-14

解读
现代
有道
制度
条约
列强
国家
近代
主权
特权
WTO
最惠国待遇
片面最惠国待遇
“条约制度”:盗亦有道的现代解读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条约制度:盗亦有道的现代解读》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条约制度:盗亦有道的现代解读》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d036742cdd93a7119699944a95102f6d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条约制度:盗亦有道的现代解读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一
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是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国被迫和资本主义世界建立新的关系的产物。作为中国蒙受屈辱的标记,它产生和形成于两次罪恶的鸦片战争。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外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列强来说,战后签订的条约“揭开了对华事务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中国闭关自守的破产,同时标志着中国与欧洲‘掠夺成性的蛮夷’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3页。>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确实揭开了一个新纪元,这些条约正提供了保障列强在华特权的法律形式。用费正清更直截了当的话来说:“即依靠条约、法规使各种权利成为制度”。显然,这个新纪元就是列强用暴力在中国建立“条约制度”,以保障它们在华进行殖民掠夺的权益的开始。它并非使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列强建立新的关系。相反,列强用“条约制度”把中国纳入它们的“统治范围”,确定了对华关系的真正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正是“条约制度”的内核。
“条约制度”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并不等于它已获得稳固的地位,形成为确保列强特权的制度体系。它本身还不完善,还未包括列强在华的主要特权,其适用范围还有很大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它还没有最终取代“天朝体制”,并迫使清政府信守条约。因此,列强要求进一步充实“条约制度”的内容,改善实施“条约制度”的各种条件,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不可避免。通过战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列强实现了这一目的,“条约制度”至此基本形成。
1.“条约制度”的内容包括了列强在华的主要特权
列强在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得的特权,在这里得到了明确和具体的肯定,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特权。至此,它基本上囊括了列强在华的主要特权,尤其是经济特权,如英人伯尔考维茨所说,“它包括了商人们所要求的特权”,是“整个时期英国和中国外交及商务关系的根本基础。无论是1876年的烟台条约或1902年的马凯条约(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都没作出任何基本上的变动。”“条约制度”的内容和框架此时已基本上定型,除了少量几种新增特权之外,以后只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具体化。
2.“条约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清帝国的中枢和内地
《南京条约》时期,列强的特权局限在东南沿海五口,只是一种突破,还不具全局的意义。现在列强的触角已伸到了京师、长江腹地和北方几口,实现了马戛尔尼来华时提出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列强消除了全面对华进行殖民掠夺,建立统治权的障碍,掌握了为“条约制度”开辟广阔的前途的中心环节,“条约制度”也由此具有了全局的意义。此后,中国开始全面地置于“条约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内。
3.“条约制度”的地位取代了“天朝体制”,完全确定了中国与列强新的关系。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列强国名前面均冠以“大”字,表明“天朝体制”已被打破,但并非是确立列强对华关系的支配地位。《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则实现了这一点,如马士所说,“直至1839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条约中的种种原则,“曾在半个多世纪中成为支配中国对外关系的常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37、629、427、602,第2卷第481页。>。
4.“条约制度”的实施获得了内部保障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统治集团内部普遍“拒绝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继续批评这个条约并且敌视条约中的各项规定。”即使是被称为投降派的耆英,也“被迫自食前盲,并且背反他的立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则迥然不同,清政府内部提出了以“诚信”为原则的对外政策理论,出现了一大批执行这一政策的实权派人物,和遵守条约的趋向。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卷第323、324页。>。曾国藩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套理论,他反对在对外关系中“打痞子腔”,主张严格遵守条约。这种“诚信”的理论此后成为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无一事无一时不守条约”<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第23页。>。
综上所述,不论从“条约制度”本身,还是从其实施的各种条件来看,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条约制度”已基本形成。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制度粗具规模,尔后,“条约制度”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它的扩张,并日益在中国表现出它的作用和地位。至1901年八国联军之役结束,其中经过《马关条约》和瓜分狂潮中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列强新增特权使它获得进一步扩充,其大的内容和框架完全确定。因此,《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条约制度”的完备。
二
从内容实质来看,“条约制度”是列强对中国行使“准统治权”的制度。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任何国家都具有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如前所述,“条约制度”是列强用侵略战争损害中国的独立平等主权和自保权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其内容则明显地大量地体现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中国的管辖权,这种取代又加深了对中国独立平等主权的损害,使得“条约制度”作为列强的特权制度,成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即如奕訢所说:“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
1.列强在华侨民管理制度
这是列强在中国领土上管辖自己的侨民的制度。主要包括租界制度和治外法权制度。
租界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南京条约》确定了通商口岸制度,给予外人在通商口岸的居住权,由此产生划定地方租地建屋作为居留地的制度。其制为《虎门条约》所规定,由随后的《望厦条约》和《黄浦条约》补充。但是,列强通过非法侵夺,将这种制度演变为租界制度,即列强在此设立类似议会的机构,以及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行使各种主权国所具有的管辖权的制度。这一制度超过了条约上的居留地的意义,成了列强管辖外人居住的整个地域的“国中之国”的制度。在成为既成事实后,这一制度为“所订新辟租界之条约所许”<《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234页。>,转为“条约制度”的一部分。
领事裁判权制度又称治外法权制度,是列强对其在华侨民实施司法管辖的制度。由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开其端,《望厦条约》使之具有明确的意义,《天津条约》则更为详细、具体。这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各缔约国对此权的运用也各有区别,但不论民、刑案件,被告归其本国官员(领事)管辖。到1876年的《烟台条约》,又获得进一步的扩张,即规定了所谓的“观审”制度。此外还有所谓“会审”制度。
2.列强在华经济特权制度
这是保障列强从中国攫取经济权益的制度,从通商口岸制度开始,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侵夺中国对经济,财政的管辖权的特权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协定关税和协定内地通过税制度。这是列强剥夺我国关税自主权的制度。前者始于《南京条约》中的“秉公议定”规定,《望厦条约》进而规定变更税率须经美国“议允”,此后税率虽有变化,但须经列强同意。协定内地通过税,即子口税,其“协定”的原则确定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附约明确规定了2.5%的税率,以后的条约又规定了实施办法。
自由雇募制度。这是列强在经商中雇用为其服务的人员的制度。《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外商可以自雇引水,《望厦条约》则作了完整的规定。除了引水,跟随、买办、通事、书手、工匠、厮役等皆可自由“雇觅”,中国政府“应各听其便”,“勿庸经理。所谓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的含义是什么呢?奥本海说,“每一个属于文明国家之列的国家因此也就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就是国际人格者”,这无非是说,非文明国家处于国际社会之外,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也就不能适用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在列强的逻辑中,非基督教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非文明国家。中国法律的“野蛮”,制度的“落后”、官吏的“腐败”等等,这类在列强的言论中俯拾皆是的调子,被它们作为把中国打入非文明国家的依据。美国驻华公使劳文罗斯就认为,“中国与其它文明国家根本不是相等的国家;并且在优越者对待低劣者的关系上,必须是使用武力来使这个国家开放。”这是列强处理对华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谁稍有采取和缓政策的想法,就会被认为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有资格享受文明权利和特权的国家”而遭到嘲笑。
2.“主权是可以分割的”,通过中国的“让与”,列强可以“行使”中国的主权
奥本海就这样认为,完全主权国家和非完全主权国家的区别是基于主权可以分割的看法,由于这种可分性,与主权相关联的权力不必集中于一体<《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第36,105—106,第2分册第117,第1分册第278页。>。这种可分性又是依据什么呢?依据的是弱肉强食的既成事实。他们就是这样“论证”的:“在同一领土上只能有一个主权这个原则是有一些例外的”,因为它难于忽视这一事实,“即:实际上,主权是可以分割的”<《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2分册第2页。>他们所提出的“事实”就包括中国的租借地和租界等等,这些事实给他们“论证”了主权是可以分割的,所谓“分割”就是将主权本身与主权的使用割裂开来,“分割”的实现,是通过被“分割”国家的“让与”,但它“所让与的是主权的行使。而不是主权本身”。“让与”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条约取得,如果你不“让与”,就是“故意敌视本国的一种行动”。“则必须先令中国人民再罹兵燹之灾”<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第13页。>。不言而喻,主权的分割,就是暴力掠夺,然后披上条约的“合法”外衣。这种“分割”的理论,使列强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行使”中国主权的种种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大言不惭,甚至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持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真是奇妙无比!
3.根据国际地役规则,中国须开放它的领土为列强服务
国际地役也称国家地役,在传统国际法中是指“根据条约对一国属地优越权所加的特殊限制,着这种限制,一国领土的一部或全部在一定范围内须永久供另一国某种目的或利益之用”<《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第36,105—106,第2分册第117,第1分册第278页。>列强在中国的某些经济特权制度和驻军制度等等。都与这种规则有关。这一规则为列强取代中国的管辖权又提供了一个根据,如通商口岸制度和相关的租界制度,按这种国际地役规则的解释:“中国既划分租界,俾外人居住贸易,是弃该地管理司法权,并亦不能行使收税权”。<刁敏谦:《中国国际条约义务论》第2编。>租界作为免厘地区,即基于国际地役的规则。列强强制中国开放的内河、陆路边境的免税地区,在势力范围修筑铁路等等,都可以从国际地役的规则获得解释。
此外,还有所谓国际标准规则,即“外国人的人身待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最低的文明标准存在,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即须负国际责任,这是屡经确定的规则。”<《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第36,105—106,第2分册第117,第1分册第278页。%>这个标准即是欧洲的文明标准,这无异是给与列强在华侨民一种高于中国人的特权地位。
不难看出,上述理论和规则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际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以资本主义列强为中心的,反映了国际法领域扩展到东方时,是与殖民掠夺相伴而行的。准确地说,这些规则是殖民掠夺规则,而强权则是这些规则中的规则。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形象地说: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37、629、427、602,第2卷第481页>”。这些规则无疑与国际法中的进步原则大相径庭,西方列强又害怕中国利用这些进步原则来抵制这些特权制度。因而,当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来时,法国代办就气急败坏地说:“谁使中国人了解到我们欧洲国际法?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制造无穷麻烦。”<王铁崖:《国际法》第18页。>但同时,它们又利用国际法中“条约必须信守”的合理原则,来约束中国遵从“条约制度”,并赋予自己“有全权去强迫他们(指中国)遵守条约的义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37、629、427、602,第2卷第481页。>强权与“公理”结合得真是天衣无缝。
上述说明,惟有国家的强大,才能摆脱“条约制度”的约束。也正是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斗争,赢得独立,才使国际法的领域名副其实地包括所有国家,结束了这个用不平等条约将这些国家纳入国际法约束范围的时期,这些反动的规则也大多成了历史的遗迹。
四
无疑,“条约制度”使中国承受着巨大的灾祸,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如马克思所说,“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条约制度”在近代中国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半殖民地制度的主要标志,并与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促使这一制度产生具有近代性质的变化,从而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一种混合型结构。
列宁曾明确指出,半殖地国家“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这种“过渡形式”在意义上说,就是其社会结构的混合形式。马克思在谈到“征服”时认为,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即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混合形成的生产方式”。在另一处马克思称之为“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这些论述为我们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诚然,近代中国所蒙受的还不是那种“灭亡”意义上的“征服”,它是另一种类型的“征服”,即用“条约制度”行使“准统治权”的“征服”。这种“征服”也同样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混合形态的结构。这一混合结构包括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笔者所要阐述的主要是制度方面的混合结构。
从性质上说,这是一个具有封建性质、半殖民地性质和近代性质的混合结构。封建性质的制度仍占有统治地位,这是彰明较著,无须着墨的,需要阐明的是这一状况与“条约制度”有何关联。恩格斯曾说。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象接木那样接在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那么在中国,列强也同样需要这种嫁接,来保证取代中国一部分主权的“条约制度”的履行。如英国驻台湾领事波郎所说:“我们所能达到的合意目的,应该是通过北京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来强制各地方官员遵守条约并保护英国属民,使其能行使自己的特权”。可见,保存清政府的统治体制,并与之紧密结合,是“条约制度”赖以维持的条件;同时,也使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下来。
半殖民地性质的制度,是以“条约制度”为主干的。另外,中国本身的社会、政治制度为适应“条约制度”的需要,而出现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变化,也是其中的一个内容。从阶级实质来看,半殖民地制度所代表的是列强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利益。由于有“条约制度”的保护,也由于清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半殖民地化,“在1860年以后,他们作为清帝国的多种族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维持并扩大其作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85页。>
最后,我们看看这个混合结构中的具有近代性质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必讳言,中国与国际社会发生交往的同时,亦随之产生了某些具有进步性质的近代制度,这种近代制度与“条约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列强要求亚洲社会完成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第165页。>。破坏性使命,如恩格斯所说,侵略战争给了中国以致命的打击,“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1页。>。建设性使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共宣言》中所说的,“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推行所谓的文明”,是直接在“条约制度”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的。
清末的某些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制度改革,更是直接在“条约制度”的刺激下进行的。例如清末的司法法律制度的改革就是针对治外法权而来的。这些改革的近代性质是极明显的,它“基本上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改革传统的封建旧律”,“表现了某种进步的倾向”<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第347、346页。>。
列强在华的经济特权制度,还促使清政府试图颁行一些具有近代性质的管理制度,以防止权益外溢。如1898年发布了《矿务铁路章程》,提出“保华商之利权”,“此后总以多得商办为主”,并规定了华股基数,“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还规定一切路矿的行政管理权,“总应操自华商”,以及实行“专利”制度等<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中册第527—529页。>。尤其是1906年颁行的《奖给商勋章程》,规定“其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照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者,自应分别酌予奖励。”<《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4。>这些章程虽然不一定能收到“挽回利权”的效用,但它们是中国建立近代性质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开始。诚然,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近代化,有着多种因素,但“条约制度”的影响和刺激,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除了中国自己被迫推行西方文明外,列强还自己直接推行它们的文明。这主要体现为外人在租界所实行的管理制度,以及近代化的海关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较封建制度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当然,尽管它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借鉴,但却付出了国家主权的巨大代价。
总之,“条约制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在保持旧制度的前提下促使它趋于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又刺激它产生近代性质的变化。由此可见,中国由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进入国际社会时,它的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是相伴而行的。也正惟此,在这个混合结构中,近代性质的方面处于一种被支配而受限制的地位,以致它的进步性往往是很艰难地显示出来。因而,若要使中国的近代化获得广阔的前途,最终还须清除限制它的这两大障碍。
查看更多
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思维导图
 U633687664
U633687664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04名中国成年人第三磨牙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病史的横断面调查》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0b9a8a2dd2fb4593f8130ef16c320fc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相似思维导图模版
首页
我的文件
我的团队
个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