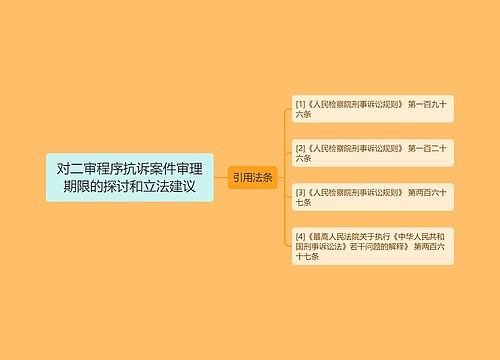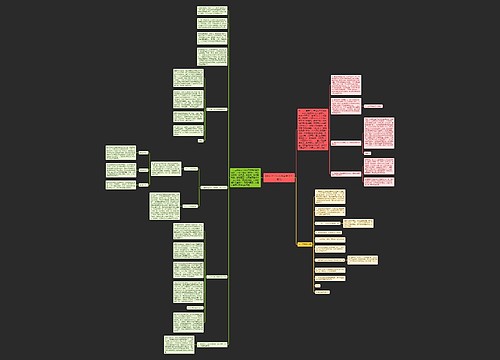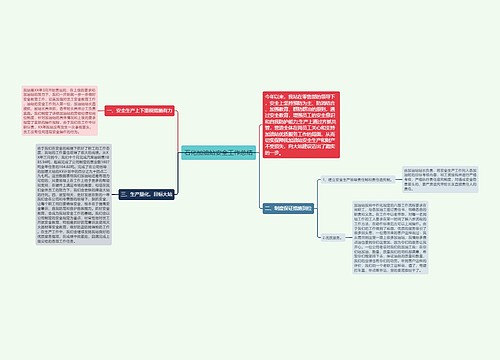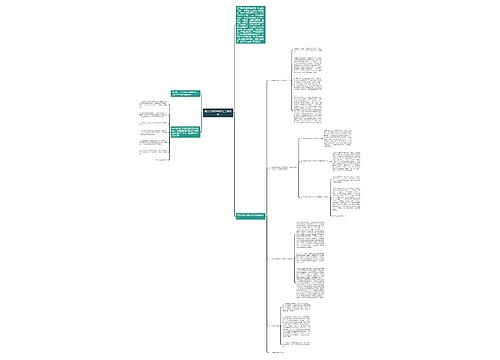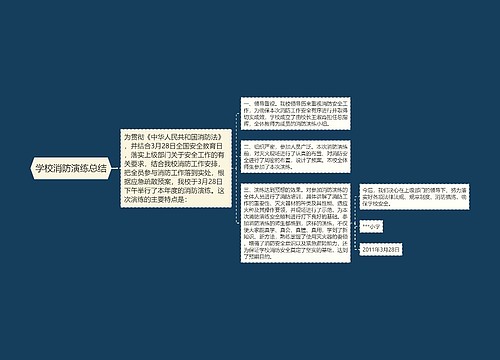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和判决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最终处理后果。由于证据立法不完善,证据的采信与否,证据的充分与否,不同的法官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1、证明标准。探讨证据标准,即要证明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裁判,必然会涉及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问题,本文认为,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律真实,需要研究的 是三大诉讼中是否适用统一的证据标准问题。刑事诉讼涉及公民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的剥夺,其证明标准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在给被告 人定罪时,法官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内心确信被告人已构成犯罪,否则,即应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布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民事诉讼是私法性的诉讼,其规 范和调整的对象与刑事诉讼有较大区别,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但通常理解为事实清 楚、证据充足。这一证明标准明显偏高偏严。“不仅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做到,而且由于双方负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的提高必然导致加重原告的证明责任,增加原告败 诉的可能性,使原、被告双方负担明显失衡,有失公正。”因此,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采用盖然性的标准,一方当事人持有有的合法证据相对另一方当事人持有的 合法证据占有优势时,法官应当作出支持前者的裁判,对于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案件,可采取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但亦不必达到刑事诉讼中确然的程度。行政诉讼又 有其特殊性,部分具体行政行为亦会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重大财产权利产生严重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可理解为“证据确凿”,近似于刑事诉 讼法中的“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具体行政行为达到证据确凿的程度,法院才可判决维持。但对限制人身自由(特别是劳动教养)、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 等对相对人权益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之外的具体行政行为,可适当降低对证明标准的要求,但亦必须达到较高程度的盖然性。
2、事实推定。在案件事实模糊不清时,是否采用推定以及如何进行推定将对司法审判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事实上,我国法律界对于推定制度是抱肯定态度 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正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明足以推翻公证证明 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 证,但不可否认,事实推定仍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或然性,适用推定原则得出的事实并非绝对事实,但从司法审判的功能考试,事实推定又是必要的,在据以进行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真实可靠的情况下,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应当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
3、举证时限。从理论上讲,举证时效制度与司法公正(主要是实体公正)是相矛盾的,但司法审判的特性决定了举证时效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法院不可能长 时间陷入个案的纠纷中,更不能被当事人持有而不予提供的证据牵着鼻子走,否则,司法审判定纷止争的功能将永难发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化举证时 效均已成较为普遍的一项诉讼制度。而我国三大诉讼法对举证时效的规定尚是空白。有所突破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 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 一审裁判的根据”。反观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随时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包括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程序中。“基于人的这种基本避害欲求,民事诉讼中就有了诉讼效率 和诉讼时间经济性的价值评判,也使诉讼的公正性不仅受制于 诉讼的经济性,也受制于诉讼时间的经济性。”重构审判监督程序,建立证据失权制度,限制当事人在二审、再审程序中的举证,乃是当务之急。尤其在民事诉讼二 审和再审程序中,当事人不得提出新证据,提出新证据的,法院不予采纳。但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法定事由不能举证的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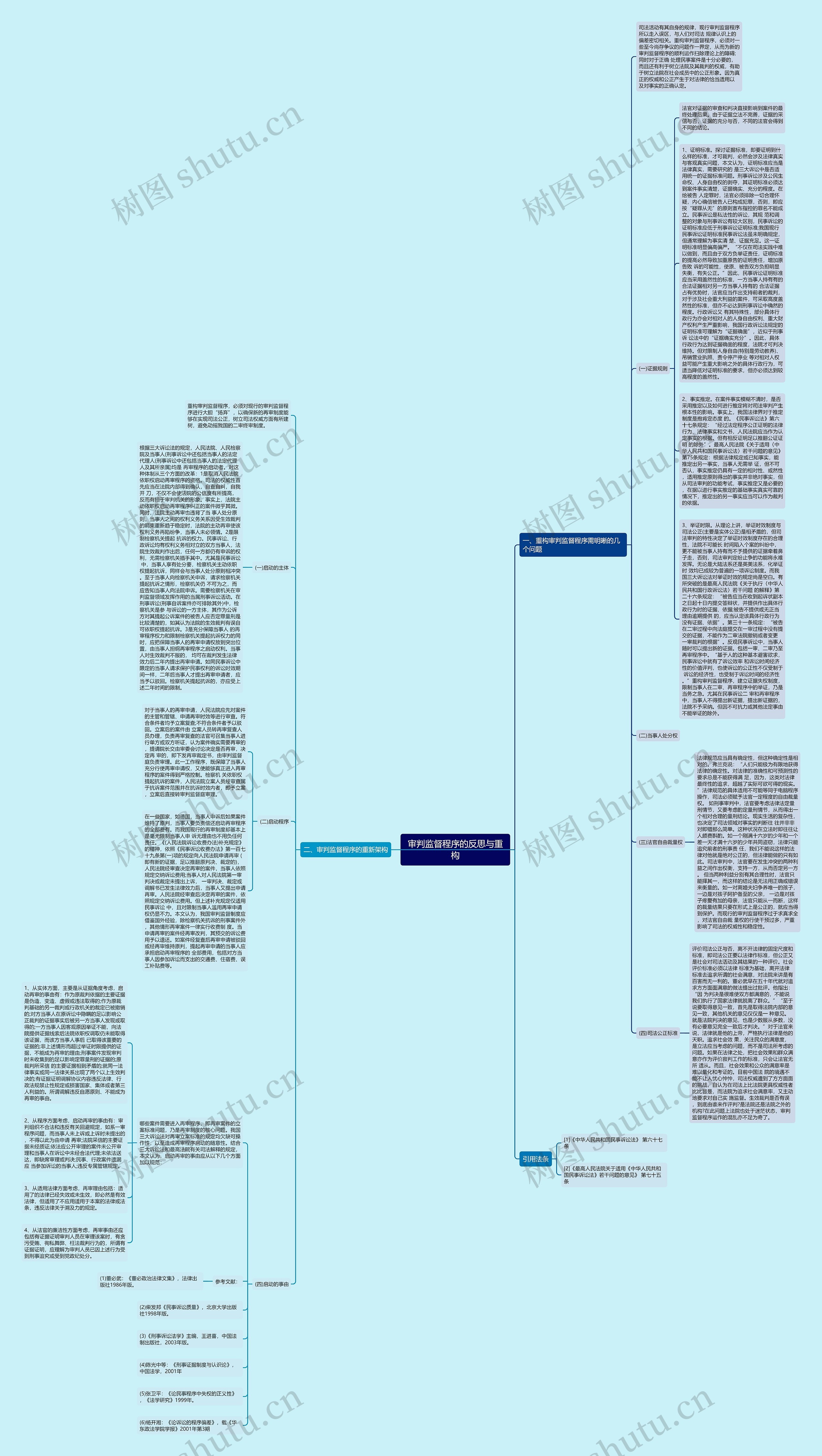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