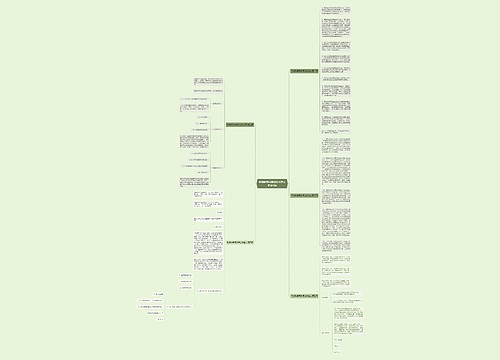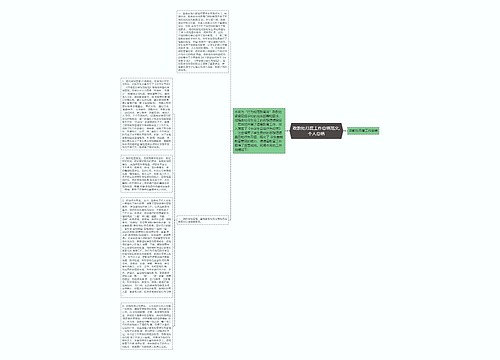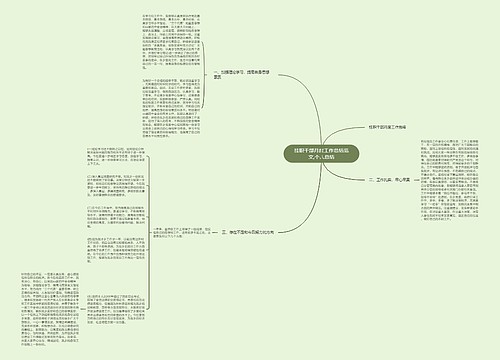又兼具民事侵权的性质,从而形成刑事与民事两种法律责任的竞合,已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为了解决这种因同一主体的同一行为依不同的实体法律规范而产生的不同法律评价及实体法律责任,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判定形式并不完全一致。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对因犯罪行为而引发的赔偿的处理,基本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即以日本为代表的“平行式”,以法、德为典范的“附带式”以及以英、美为表率的“兼采式”。我国与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采用第二种模式,即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被害人所提出的赔偿要求。
然而,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存在价值提出质疑,甚至主张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取消该项制度,将民事赔偿完全从刑事程序中分离出来以另行起诉的方式来取代。
笔者认为,虽然上述对于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质疑不无道理,但并不构成对该种诉讼形式存续基础的有力撼动。
首先,作为一种兼具刑事与民事内容的特殊的诉讼形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然不同于单一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两种不同的实体责任也并未要求以相同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一并作出,两种责任的诉求与处置存在一定的差异乃情理之中,这也正是这种诉讼形式的特殊所在。
其次,虽然这种诉讼形式以刑事诉求为前提,但并不意味着处理上必然要“先刑后民”、“刑优于民”,相反,司法实践显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先民后刑”。至于诉求范围的不尽合理乃至诉讼时效、缺席判决等程序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立法,以及对该程序进行一些特别的设计和处理来得到解决。
再次,虽然专门机关在侦查、起诉中一般不会将民事赔偿作为其主要目标来收集证据,但不排除在赔偿要求提出受理机关后专门针对有关赔偿问题收集证据,况且有关证明犯罪与刑罚处置的证据,不仅在查明事实方面具有相通性,而且甚至可以成为民事诉求的证据基础。至于特殊情况下的“刑事先行”,并不影响该种诉讼形式在将两个不同的诉讼置于同一程序之中来进行处理以避免诉讼程序的重复启动,从而在诉讼经济与诉讼效率方面发挥其不可否定的优势作用。不仅如此,由同一审判组织就同一主体的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置,可以关注到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处理结果具有其应有的内在协调统一性,避免因审判组织的不同而对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最后,更为需要强调且不可否定的是,这种诉讼形式的存在为受害者民事诉求的实现提供了较之另行起诉更具保障性的程序基础。
因为:一是该种诉讼形式弥补了受害人诉讼能力的相对不足。在国家追诉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刑事诉讼中,强调犯罪本质上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侵犯,公诉成为刑事诉讼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公诉案件的侦查和起诉都由国家专门机关进行,并以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作为基础和保障,在查明案件情况,充分获取证据方面有着被害人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天然的优越性。正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受害人和国家追诉机关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使得受害人能以国家专门机关的侦查、起诉为依托,借助国家专门机关通过有效的侦查手段所查明的案情与收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民事赔偿诉求,从而使其民事赔偿问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如果这一切完全由本来已经在精神上甚至身体上遭受伤害的被害人本人孤军奋战,凭借其自身的微薄之力来完成的话,成功率必然要低得多。
二是刑事审判程序中判处刑罚的威慑力也能对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动性产生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必须使这种局面得到改变,具体措施除了不同的国家权力之间应当相互制衡外,提升公民个人的权利以对权力形成制约已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成功经验。在刑事诉讼中,一方面必须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另一方面,必须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那种以为加强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就会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之间存在冲突的想法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误解。实际上,以往二者都受到压抑,其保护都很不到位,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而不是由于某一方面的加强而使另一方面遭到了贬损。正因为如此,世界不少国家又重新开始重视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意愿的尊重,并将对被害人的赔偿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来予以考虑。此种背景之下,与“恢复性司法” 存在联系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成为被害人获得赔偿的程序性途径,而且实际上也为被告人获得有利的量刑情节提供了机会。大部分被告人都会选择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被害人的损失予以赔偿以换取刑罚处罚上的减轻。这显然是单纯民事诉讼所望尘莫及的。

 眼眶很热
眼眶很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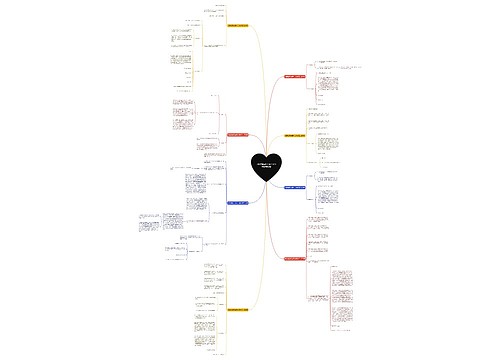
 情痞有泪
情痞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