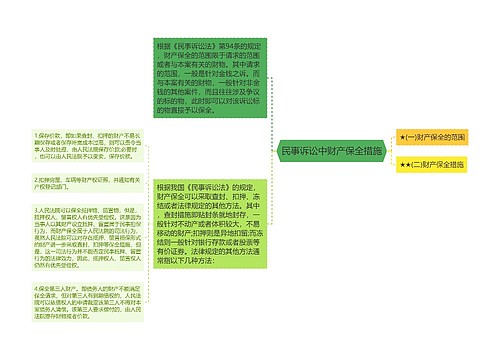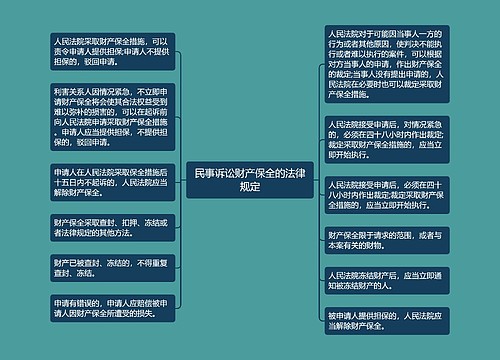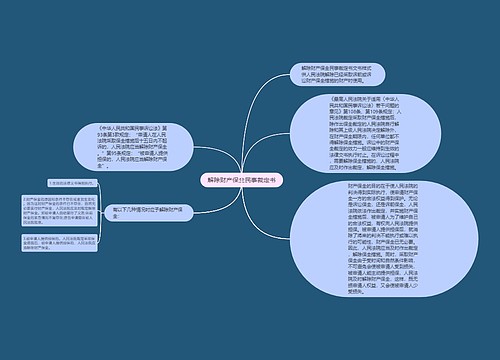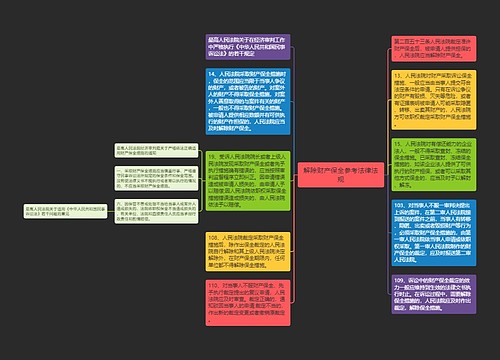仲裁法学界一般的看法是,由于“仲裁委员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不具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 [13]并且认为, “我国采取由人民法院采取仲裁保全措施的做法,突出了人民法院支持仲裁工作的重要地位,符合我国国情,不仅为仲裁裁决得以顺利执行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而且增强了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信心。” 这实在是对中国国情及仲裁的一种曲解。
1.以国情论,正因为我国是一个有二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缺乏民主与法制传统,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才更加迫切地需要立法赋予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所择定的仲裁机构以财产保全权。这样,不仅仅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变革或突破,不仅仅是对司法专横的一种抗衡,也不仅仅是多了一种有保障、可信赖的解纷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的切实实现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2.以仲裁权性质论,仲裁以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为基本特点,而仲裁权是以社会公信力为后盾的一种契约授权;同时,仲裁又受到国家法律的调整,因而仲裁权已从早期完全的私权性质转化成现代的公权范畴。换言之,不能因为仲裁权是一种契约授权并以公信力为后盾就得出“这种公信力并没有烙上国家意志的印记” [15]这一不当的结论。 追本溯源,既要有历史的眼光,更应具备前瞻的思维;既要肯定仲裁源于争议当事人的契约授权,既民间性的一面,也要肯定国家法律对仲裁予以授权、调整和支持即准司法性——现代公权的一面。因此,以仲裁权的主体既仲裁机构——在我国是仲裁委员会为“特殊事业单位法人” [16]属民间性,就得出仲裁权也只具有民间性,这是错误的;而由于对仲裁权的错误界定,导致运作仲裁权的主体无财产保全权力,更是错上加错!我们应当将仲裁权的权能与仲裁权主体的性质适当剥离,一如将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剥离一样,更利于仲裁事业的发展。
3.以仲裁立法论,采取职权主义仲裁立法模式的国家,以仲裁权主体为本位,强调仲裁权主体在仲裁过程中的作用,力图建立起与民事诉讼比肩的另一解纷救治系统,因而立法赋予仲裁机构以财产保全权。采取当事人主义仲裁立法模式的国家,除执行权外,在财产保全制度上却与职权主义国家的立法殊途同归。按理论的衡界,当事人主义仲裁模式的国家如欧美等西方国家,似应在仲裁上不能涵及财产保全的内容 [17],但立法实践恰恰证明,这些国家的仲裁立法以及联合国《示范法》都涵及和赋予仲裁庭以财产保全的权力。这从另一面也有力地反证了我国仲裁理论与立法整合同构的差失。
(二)修订仲裁法时,应当明确规定申请仲裁前,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涉外仲裁,当事人均可向仲裁申请人住所地或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仲裁前的财产保全。这样修订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打破内外有别的格局;第二,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第三,赋予仲裁法较高的地位,真正体现法院对仲裁的支持;第四,少环节、低成本,符合仲裁制度经济这一价值取向;第五,符合现实中出现的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势,有利于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