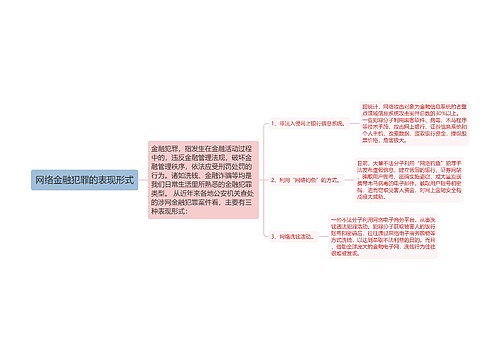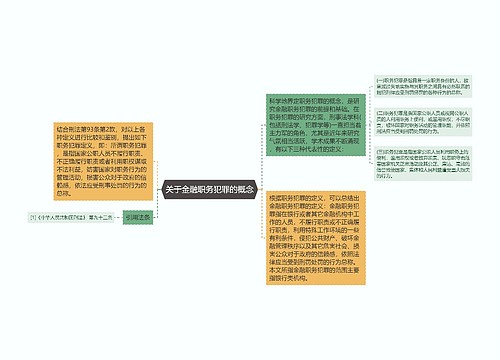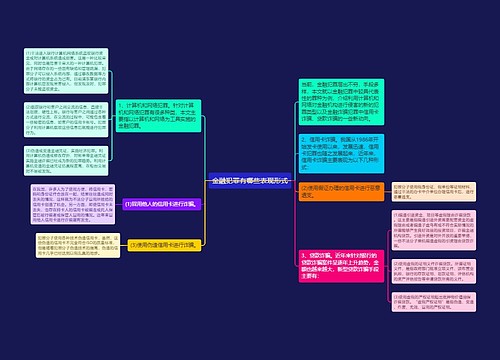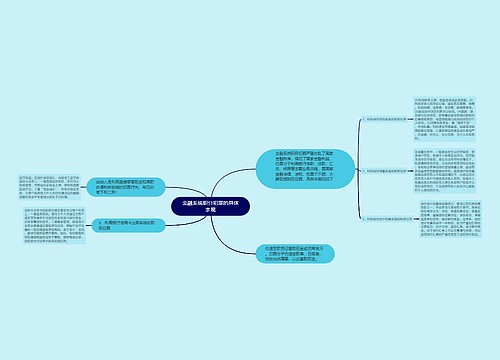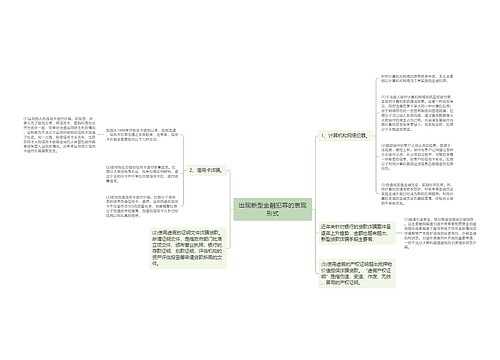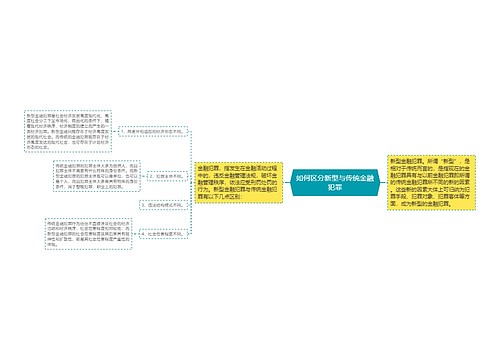我国《刑法》分则在犯罪分类上坚持以犯罪客体为主,以行为和对象为辅的分类方法。在《刑法》分则各章的划分上以及同一章中各节同类犯罪的区分上都是以客体为主要的划分标准,而在同类犯罪中的具体个罪划分上则以行为和对象为划分标准。这种以客体为标准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对经济领域的划分。这一点从我国《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每一节的设置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涉及到金融领域,第3章则有两节的规定,即第4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5节金融诈骗罪,对于这两节的罪名设置,有观点认为第4 节是明显按照客体标准来进行的分类,第5节则是按行为方式所进行的分类。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虽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都是发生于金融领域的犯罪,从广义来看都是对金融秩序的侵害,但是这两类犯罪之所以划分为两节,原因仍在于它们所侵害的客体是有区别的。金融秩序是一个相当大的范畴,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所侵害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这种秩序体现了国家对金融行业的直接管理,其行为直接违反了有关金融行业的管理规定,而金融诈骗罪所侵害的客体,主流的观点认为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次要客体为公私财产所有权。
笔者认为,对于金融诈骗的行为而言,所涉及的并非对国家金融行业直接管理的侵害。因为金融诈骗行为的直接受害人是被欺骗的金融机构,犯罪行为直接挑战的是金融机构本身,金融机关在业务运作中往往有一套监管体系,所以如果说这类行为侵害到国家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金融管理制度,这样的侵害也只不过是在逃脱金融监管同时的一种间接性侵害,这点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直接针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犯罪行为是有区别的。因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类犯罪所涉及的主要客体实际上是金融秩序中的金融交易秩序。而在金融诈骗这一类罪中,所有的犯罪类型在行为方式上都具有欺诈性,因此对于具体个罪的划分,我国《刑法》实际上是以行为对象为主要的划分标准。
正是基于这种犯罪分类方法,使得即使是同样的犯罪对象,由于与不同的行为方式或不同的行为阶段相结合,就体现出了不同的客体价值,因而在犯罪的类型上就有了不同的归属。以金融票证为例,我国《刑法》中所涉及到的金融票证包括:票据(汇票、本票、支票) 、金融凭证(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它银行结算凭证) 、信用证(及其附随的单据和文件)和信用卡。
在中国的金融行业中,国家既是宏观调控者,也是直接的竞争参与者,所以我国的金融市场是一种不完全的竞争市场。我国强调公权力管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金融机构主要以国有资产或通过国家持股的形式而创办,国家直接参与金融竞争,对金融体系的破坏实质上就是对国家所有权的侵害。此外,对公权力的倚重也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行政管理的一种惯性。因此,对金融秩序的破坏,不仅是侵害了国家所有权,而且还是对国家管理权威的蔑视。
国家虽然通过制定金融领域的管理规则而调控并参与金融市场,但当这些管理制度受到违法行为挑战时,为保护国家所有权和维护国家管理权威,刑法其最后的严厉性必然成为了保障转型时期国家对金融市场管理有序化的最后武器。因为这种秩序是国家管理和参与之下的有序化,所以刑法在将行为进行犯罪类型的归属时,也必然与国家金融管理的不同领域相适应。金融犯罪客体的区别就是基于国家管理和参与金融市场的不同领域而产生的不同社会关系。正是国家对金融秩序的直接管理和对金融交易秩序的间接管理决定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的不同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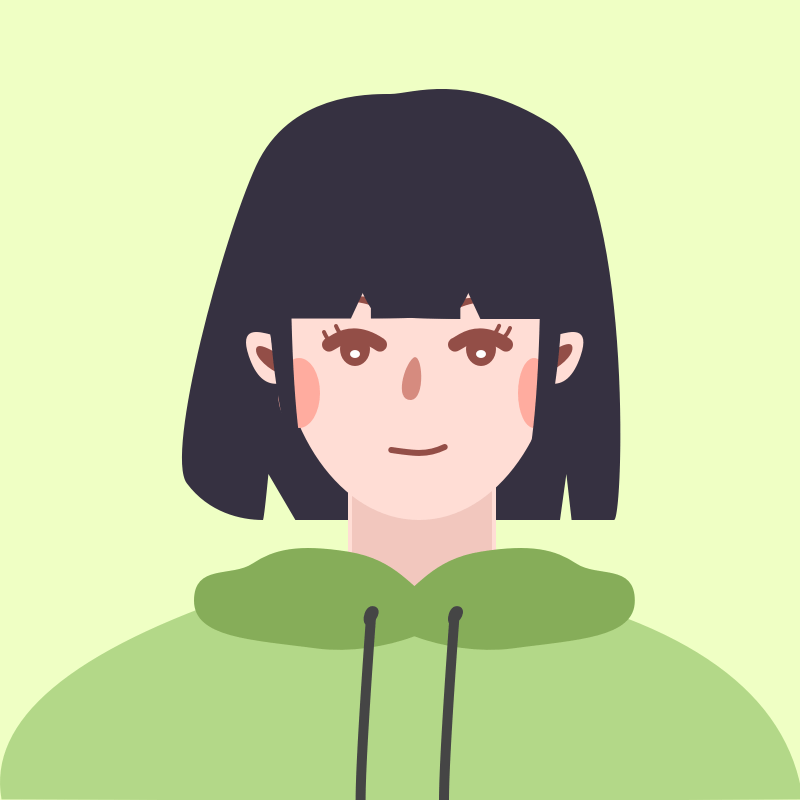 U880271396
U88027139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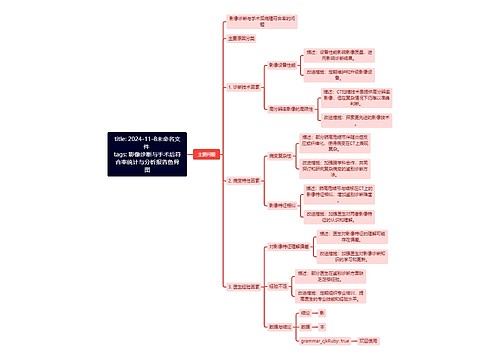
 U382105938
U382105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