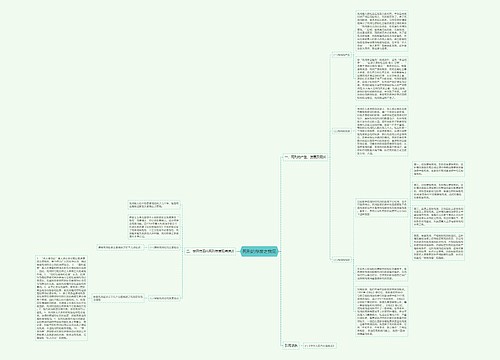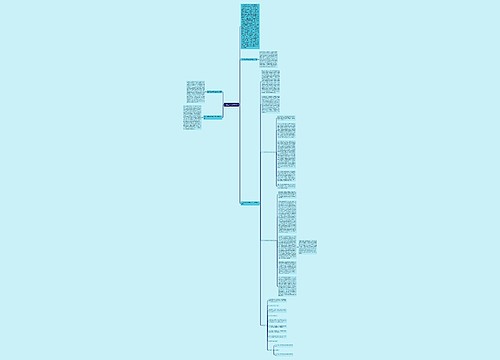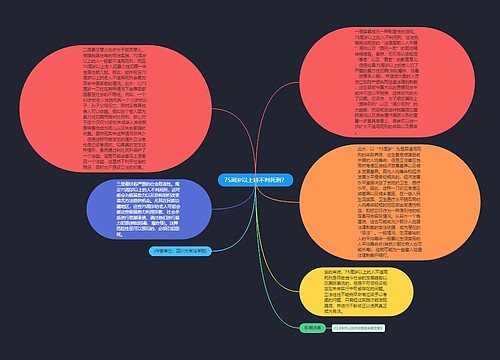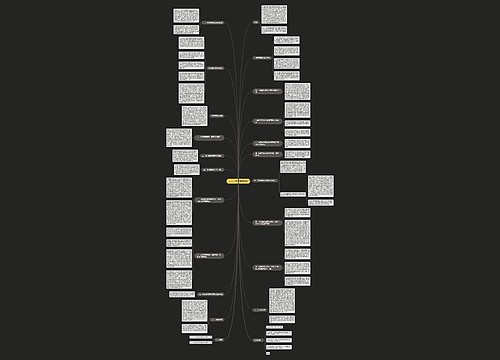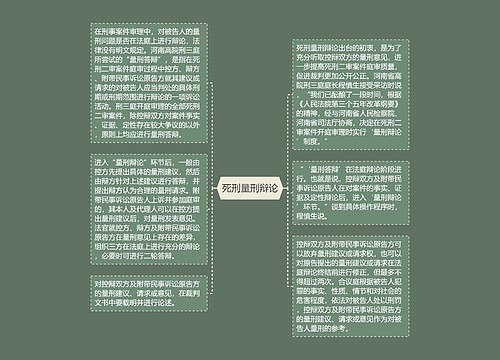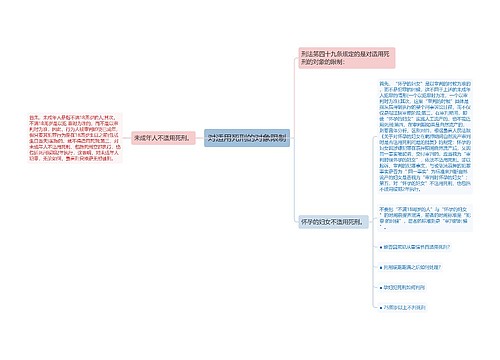在死刑的适用上,许多保留死刑的国家一年也难得判决几个死刑犯,即使判决了,也还有种种救济方式,最后真正执行死刑的也是微乎其微。而我国在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方面无异是最多的。许多年来,我们在“从重从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口号下错杀了多少人,误杀了多少人是很难统计的。但近几年,犯罪嫌疑人被错判死刑后,真凶又浮出水面的报道屡见不鲜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使然。但我国作为一个渐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各方面都迫切要与国际“接轨”的发展中大国,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在国际上日渐高涨,我们有什么理由还这样大开杀戒呢?就连印度这个国内各种矛盾都十分尖锐,经济发展还不如我国的亚洲国家在死刑的适用上都能做到严格限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有人认为,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死刑不宜废除。但联合国在1988年和1996年组织的两次关于死刑与杀人罪的关系调查中都得出结论,没有证据支持死刑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况且,在我们适用的六十余种死刑罪名中,并非每一种犯罪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民愤较大的主要还是那些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抢劫、投毒等严重侵害他人生命的暴力犯罪。
“无论谁犯了谋杀罪,都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合法的替代办法能够满足正义的要求”注2。对此,即使在那些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里,也一定还有不少人持此观点。笔者亦然 。这是对侵害他人人身甚至生命安全的犯罪而言。但是对于那些非暴力犯罪,如盗窃、贪污、受贿、甚至贩毒等是否也必须判处死刑,就值得研究了。有人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犯罪猖獗,需要用死刑来惩戒那些贪官。但事实上,对经济犯罪的严惩,并没有有效遏止贪污受贿案件数量的攀升。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甚至前赴后继,前任刚被判处死刑,后任又东窗事发。如果纪检、检察部门都不怕得罪自己的上级,能够顺藤摸瓜,扩大战果的话,现在被查处的贪污绝对可以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应当看到,这些贪官之所以贪,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自身素质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社会管理制度的缺失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公。坦诚地说,如果让笔者去担任某一要害部门的要职,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笔者也难免会去贪的。因此早就有人撰文说,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谁说不想腐败都是假的,之所以有人还没有腐败,是因为他不具备腐败的条件。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儿以偏盖全,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疏漏和社会分配不公方面的责任。而国家的责任如果全部让犯罪者个人去承担,显然也是不公正的。同样,对于毒品犯罪来说,尽管也杀了不少,但涉毒犯罪案件的数量并没得到有效的控制。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山寨里,因涉及毒品犯罪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的人已占全山寨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后继者仍层出不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穷”。当地政府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拨款扶贫,帮助边民致富,涉毒犯罪的人数就明显下降了。这说明防治犯罪,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建设,而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
我们知道,生命之于人只有一次,人一旦被处以死刑就无法复生。特别是在审判错误的情况下,后果就更为严重。而人对于生的欲求也是极为强烈的。前不久笔者有幸读到了李玉霄采写的《尘封40年的夹边沟事件》一文,其中的一段文字让笔者久久不能忘怀:
“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他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人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这是他们在偷吃拌了农药的麦种。
而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他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中,更是描写了一个淘金者在荒无人烟的阿拉斯加地区,在天气极度寒冷、食物极端缺乏的自然条件下,所表现出的极为坚强、卓绝的求生意志,“……病人一路爬着,病狼一路跟着,两个生灵就这样在荒原里拖着要死的躯壳,相互(等待)猎取着对方的生命”。
即然人对自己求生的欲望如此熟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轻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对于那些没有进行暴力犯罪的罪犯,监禁或终身监禁已达到了对他们惩罚目的。“一个人在受到适当的惩罚后或者从惩罚中吸取教益变好,或者应对其同伙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他们可以看到他受的苦难,从而害怕了、变好了。
鉴于死刑的适用并无多少益处,我们何不废除死刑?既然我们全部废除死刑尚有一定的困难,尚难以被公众接受,我们为何不先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