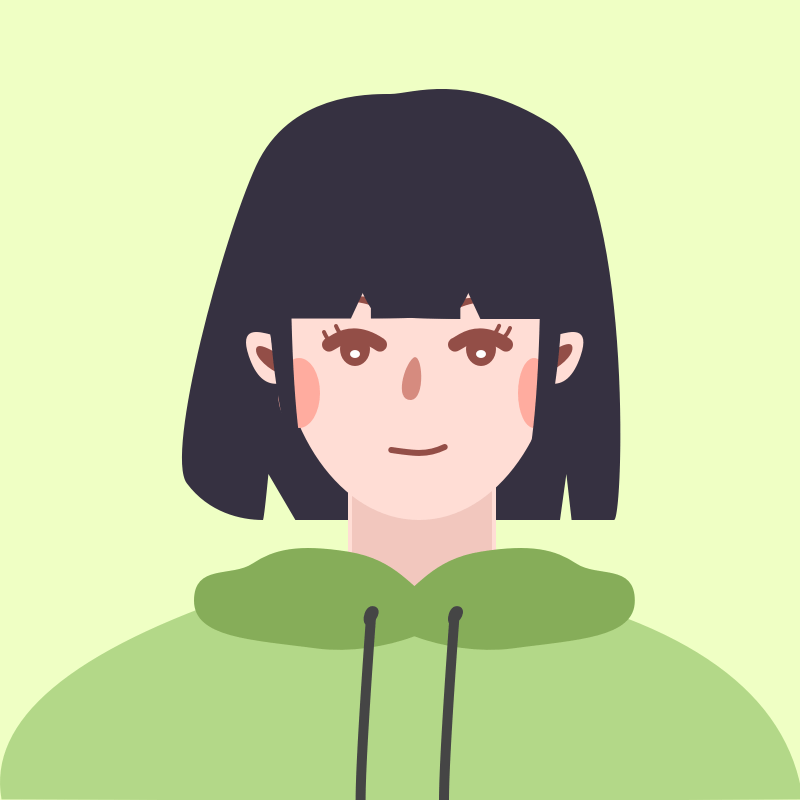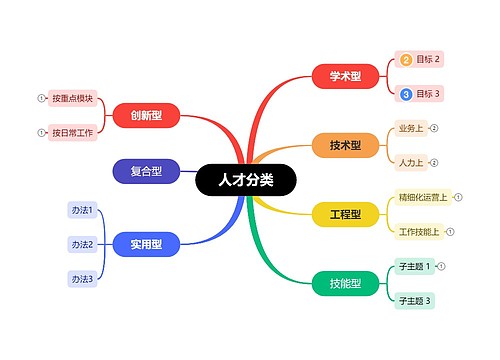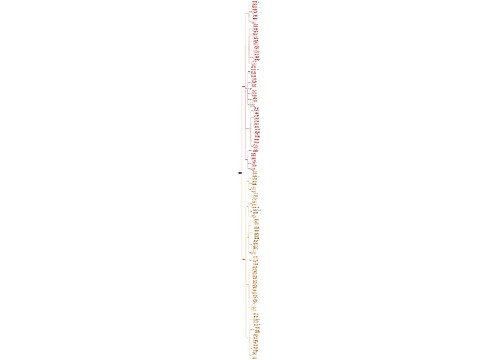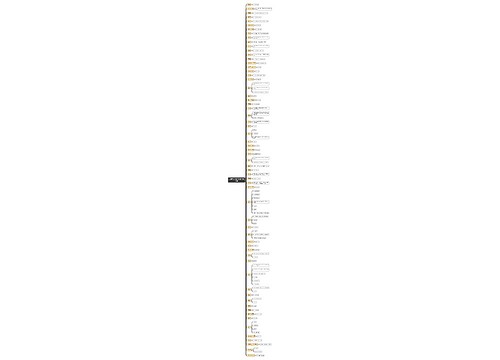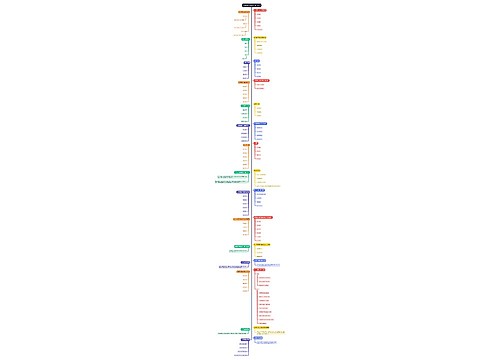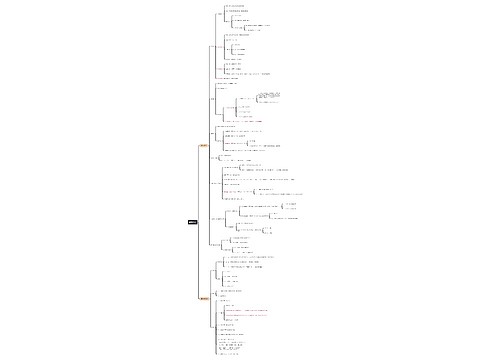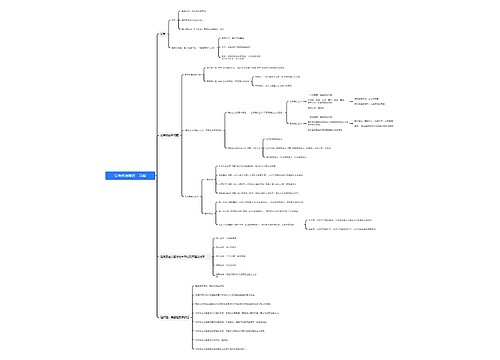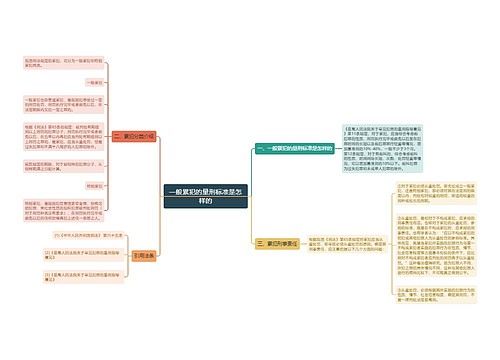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近来被再次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其实旨在对行政权力的规范与约束。日前,行政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接受媒体专访,回顾行政立法近三十年历程,强调“行政法系的立法过程,是政府权力收缩的过程,更折射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路径较量”。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纵深改革,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赋以“壮士断腕”的力道,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收缩本身,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既有利益与部门利益,在“自我革命”的逻辑范畴内,要真正做到“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市场、社会,不得截留”,殊为不易。而具象化到制度层面,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终究难以绕过包括《行政许可法》在内一揽子行政法律的审视和打量。
所谓行政许可,指的是行政机关依公民、法人申请,审查并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对行政许可特性的解读,学界角度各异,赋权抑或对禁止行为的解禁,见仁见智。于公民、法人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决定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更多属于恢复行政相对人自由的行为,而非某项权利的授予。对社会成员普遍限制(或禁止)、同时依申请而有限度许可的实质,根源上是基于特定行为的潜在危险性,这让行政许可本身注定成为一种特例,而非对所有社会行为的普遍约束。政府管的多少与政府的好坏之间,在此节点上建立了联系。
2004年6月,《行政许可法》制定出台,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设定了较明确的界限,部门规章不再拥有设定行政许可权力。但就在《行政许可法》生效前两天,“确需保留的500项行政审批项目”前置性地被设定了行政许可;该法颁行后,又出现所谓“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概念,首次开列211个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就是从那时起,一度被等同化理解的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被刻意区别对待。此后,各地更是大量存在变相设立行政审批的现象。《行政许可法》作为试图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的法律规范,其颁行伊始其实就已经面临妥协与让步的难题。
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其制度背景与目的诉求的理解,有必要回到以《行政许可法》为核心的行政法治化轨道。中央层面,目前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成绩或算可观,但对通盘改革的观察仍须首先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做造册统计,并用《行政许可法》的精神与标准去逐一衡量、审定。此前地方性试点时屡屡提到下大力气放权的标准,在于“可取消可不取消的,要下决心取消;可放权可不放权的,要下决心放权”,目前需要厘清的恰恰就是对取消、放权的“可与不可”判断标准,改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改革主体一元化局面。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政府改革这篇大文章,“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整篇文章做好,更多释放市场活力”。行政权力收缩回到其应负起责任的那个范畴,将市场的还给市场,表面看在于具体审批项目数量的减少,但却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弃守,在减少事前审批的同时,事中、事后的监管、规范是需要同时加强的方面。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可能与肆意妄为、不受限制的权力共存,它一定是权力变得谦卑、得到有效约束的结果。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纵深化发展,就是要逐步改变目前由行政部门自身主导“放与不放”判断权的现状,让行政法治原则对行政权力本身进行无死角覆盖。具体而言,首先便是用《行政许可法》所已经确立的原则逐一审核现有行政许可类行为的必要性、合法性,进而列出放权清单与改革时间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除了“自我改革”的属性,还应当注入法律的约束,让改革本身回归法治轨道,首先就是要尊重法治精神与法律规则。行政权力的第一角色,必须是守法者,才能让合格的执法者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