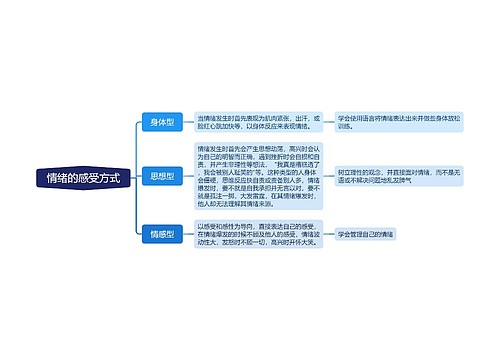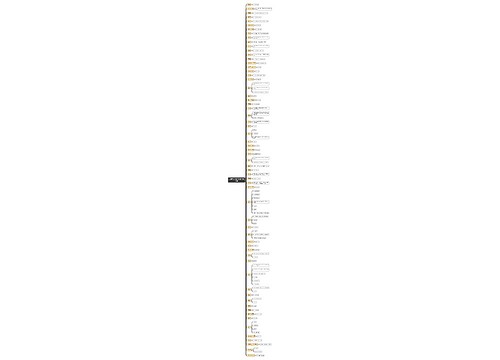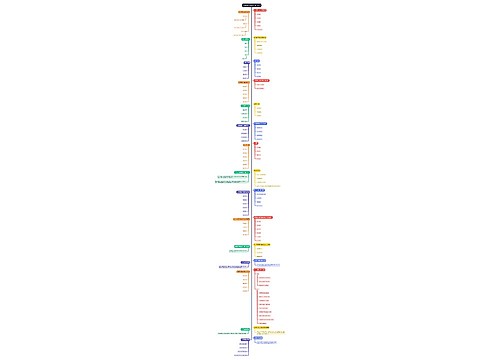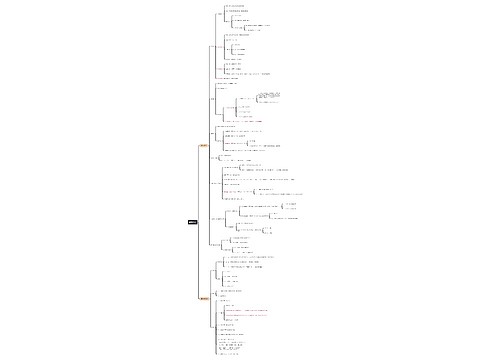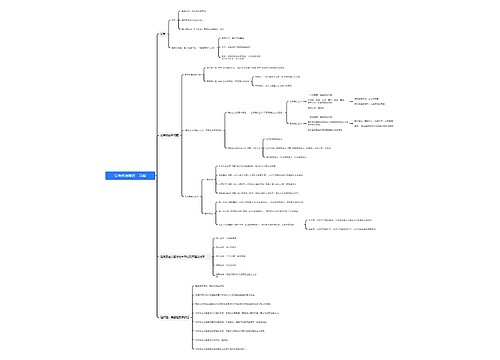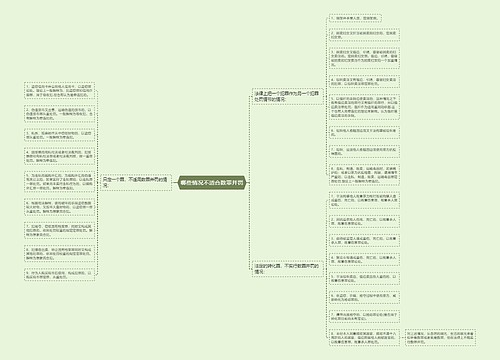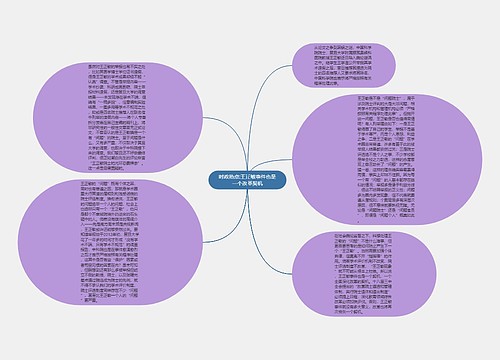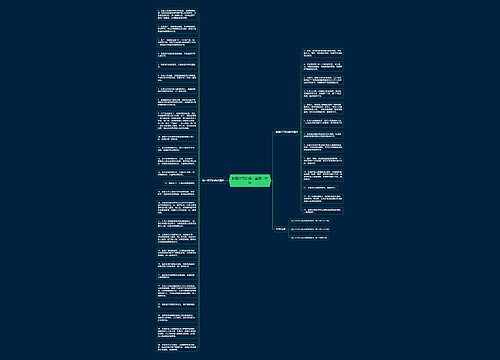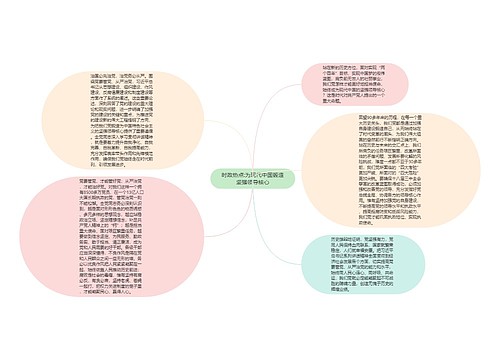季羡林先生写于1934年3月31日的一则日记新近走红了。记了些什么如此跨越时空?骂考试。“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的什么东西?”季先生一向给人以温文尔雅之感,对考试也如此极端厌恶,与今日的学子“心有灵犀”了。不过,我倒是建议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们深入进去,爬梳一下季先生当年动怒之因,与今天那些懒蛋学生的抱怨是否存在本质的不同。倘若同样是荷尔蒙过剩,自然无话可说;否则,别让季先生莫名其妙地充当他们今后高举的盾牌。
季先生这段日记是公开出版的,出自其《清华园日记》。报道说,出版时编辑曾提出“做适当删减”,季先生的意见则是一字不改。他说:“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就对了,这句话也道出了日记的应有面目,日记原本就应是作者最具体的生命痕迹的记录。不过,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一路走来都见识过不少“伪日记”——全无私密度可言,且“记主”的出发点就是要日后待人“发现”其品德之高尚;甚者由他人根据需要而就地编纂——当然这些都是后来阅读“披露”或“真相”一类才了解的,当时忙不及为之感动,热泪盈眶进而邯郸学步者亦不乏。
春秋战国时,周舍想在赵简子的手下谋事,立其门“三日三夜”。简子问他:“夫子将何以令我?”周舍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按照《辞源》的说法,这就是“日记”一词的最早出处。那么,原初状态的日记确是由别人来写,功能则与“伪日记”正相反,是专挑“记主”的毛病。赵简子即赵鞅是赵国基业的开创者,政治、军事、改革的才能均可跻身杰出之列,因此他录用了周舍。周舍死后三年,赵简子对这一诤友仍然不能忘怀,某天“与大夫饮,酒酣”,简子哭了,大家不知怎么回事,纷纷自我检讨:“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赵简子说了句享誉后世的名言:“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翻译过来意思是,你们这帮拍马屁的家伙,哪里比得上动不动跟我争辩的周舍。
好的日记是个人的“编年史”,它按照年月日记载亲身的经历和见闻,可靠性往往在一般史料之上。近代许多重要的官员、学者、文人,都留下了内容十分丰富的日记,如《曾国藩日记》、《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等等均已标点出版,为晚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绝好素材。
如果片面寻找令人瞠目的“金句”的话,在季先生的《清华园日记》中还有不少。比如,“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又比如,“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记录自己的青春年华,季先生率真得令人忍俊不禁。但是,如果我们捉住其中的片言只字,对上了自己的胃口,就以为和大师产生了共鸣,就是低估了《清华园日记》所以如此的价值。

 新自我
新自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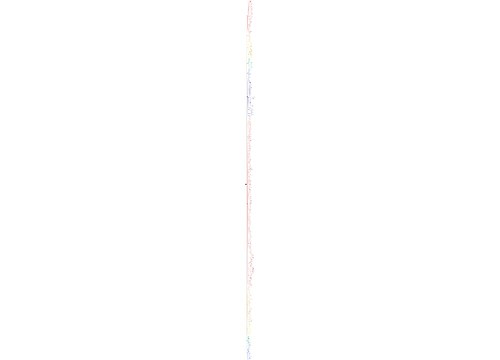
 U382064030
U382064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