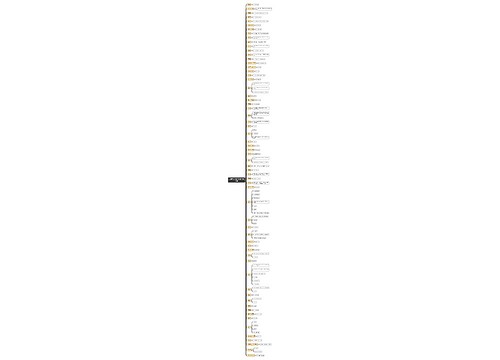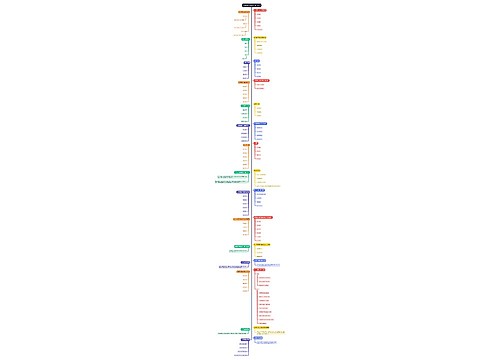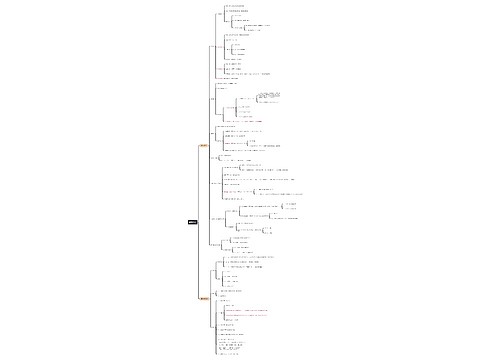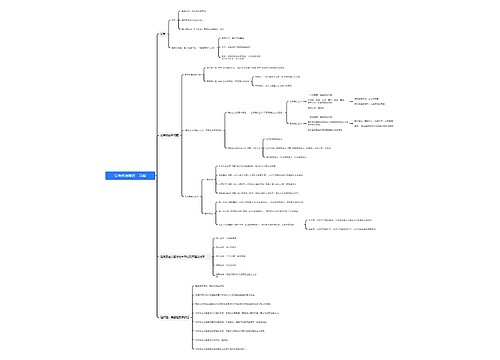在大街上,你看到一个男人衣衫褴褛,跪坐在人行道边,旁边放了一个纸盒子,一张纸牌子,纸盒子里放着若干小额人民币,牌子上叙述着男人的悲惨遭遇,你会有什么反应?是认为面前跪着一个需要救助的不幸的人,还是一个活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职业乞讨者,甚或是编造谎言的诈骗者?总之,面对这样的"街头求助",很多人会对是否伸出援手犹豫一番,认为没有施以援手的道德义务。
这反映出陌生人在面对面情境下的信任崩坏。对很多人来说,面对真假难辨的街头求助,首先预设求助信息是假的,求助者是别有动机的。因为这样的信任危机,也导致很多有真实需求的求助者不愿意采取街头求助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看,街头求助这潭水生动地演绎了"劣币驱逐良币"。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求助行为,街头求助已丧失了其功用;而在现代慈善理念中,街头求助的正当性也是备受质疑的。
互联网上的个人求助刚出现时,社会信任得到了洗牌与重构。1995年,清华大学学生朱令出现不明中毒症状,北京几大医院均没有给出确切诊断结果,朱令的同学通过刚出现的互联网向全世界求助,获得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医生回复,许多医生给出了铊中毒的意见。这被视为互联网求助的经典案例。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互联网成了有困难的人获得有效帮助的快捷通道,公众对互联网求助信息往往预设了信任的态度。
互联网求助的社交性与阶层性,使之与街头求助相比更胜一筹。很多产生巨大影响的求助案例,其求助者或发挥关键作用的人拥有较强的信用度,从早期的知识分子到现在的中产阶层,求助人与救助者感到心理上的接近性,其求助方式也让人产生共情。"罗尔救女"的主角罗尔从事媒体工作,他所掌握的传播技能,对求助信息获得如此大的关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身份在一开始让人信任,后来事件发生逆转,其本质也是罗尔透支了自己的信用。
和互联网普及后网络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一样,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网络上的社会信用。如果说,早期互联网存在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有能力提供援助的人乐意互帮互助,求助者也对发布求助信息采取审慎的态度,那么现在普及的互联网已经大大稀释了这种共同体的作用。有句玩笑说,你不知道网络那头是人还是狗鈥斺�敻非械氖牵缒峭返娜艘丫哟臣壑抵械木ⅰ⒏咝庞萌禾澹涑闪似胀ǖ拇笾凇�
罗尔这样拥有传播技能的人,利用的就是互联网的大众性。比如,用一篇情绪指向强烈的文章吸引公众关注,赢得积少成多的巨额"打赏",而不是用客观、经得起质疑的陈述。固然,他的身份可以为其信用背书,但是当真相大白以后,其身份是无足轻重的。人们不会因为他是正处于中年危机,还是离异再娶,就宽恕其隐瞒事实的错误。
罗尔后来主动发声,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他拥有多套房产却没有卖房救女的原因,结果注定是把自己的舆论形象抹得更黑了。当公众的信任底线被击溃后,就再也不会表达同情,更不会产生共情。任何求助都以求助者提供完整、确切的求助信息为道义的前提,罗尔被钉在了互联网求助的耻辱柱上,其原因也在于公众认为他所获得援助的方法是不符合道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解释也是枉然。
可以预见,在不遥远的未来,互联网残存的那种以技术、阶层为门槛的共同体会进一步消逝,互联网将成为对现实社会的完整投射。现实社会的信任度怎样,网络社会的信任度便怎样。但是,互联网的另一大优势却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密集信息的交换与汇集。"罗尔救女"真相被迅速挖出,公众"赞赏"的资金被妥善处置,均离不开互联网的技术力量。在舆论场中,罗尔的信用已经破产。让没有信用的人承担沉重代价,是互联网渠道发起个人求助的优势。
但是,要避免类似"罗尔救女"事件腐蚀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互联网信任,畅通互联网个人求助的渠道,最根本的还在于做好求助信息甄别,发挥专业机构的价值。公众不需要求助者的自我背书,这种自我背书跟街头放个小纸盒求助没有本质的区别,公众所需要的永远是更全面和准确的事实真相。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