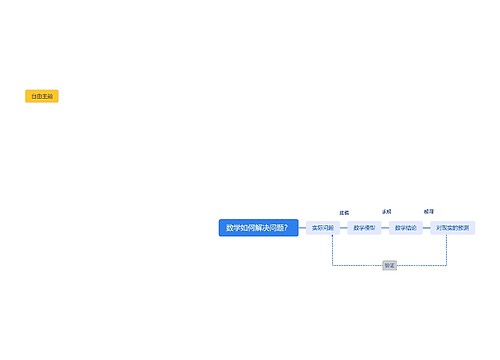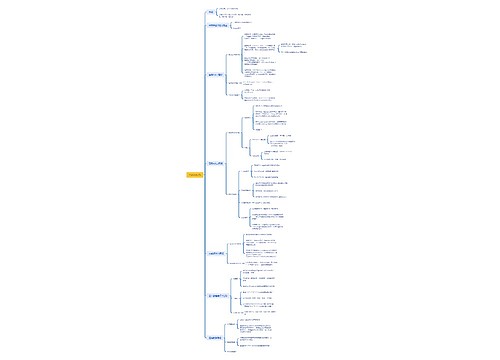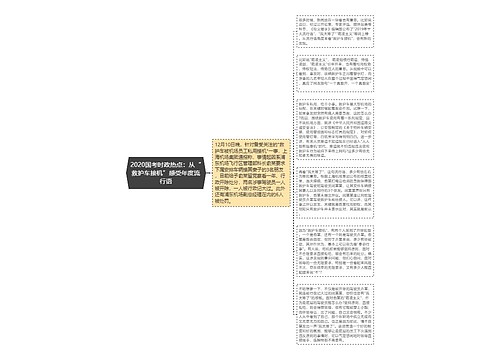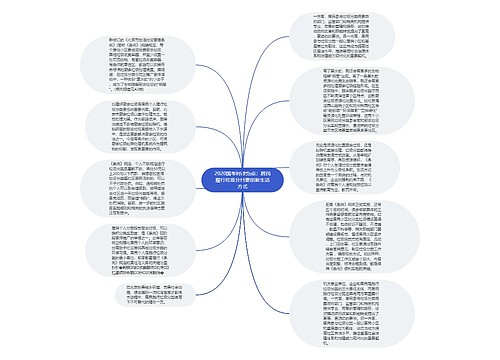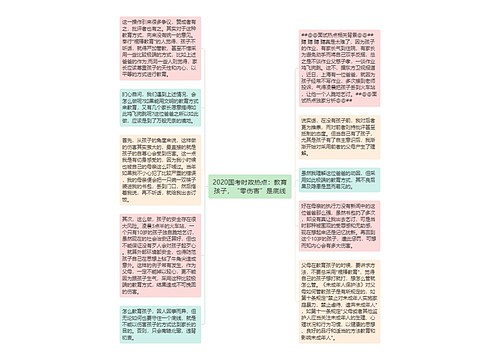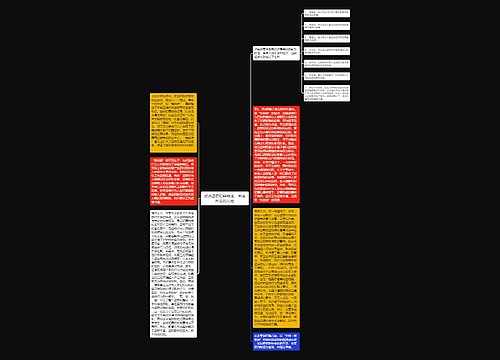笔者认为,通说的观点不能成立。在此,仅通过上述理由的评析试论如下。
第一、如果说在一些外国刑法中,其分则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规定的确是以既遂犯为模式构建的话,在我国刑法中,“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等都是既遂为标本的”这一结论却不成立。因为在一些外国刑法中,是以处罚既遂为原则,处罚未遂为例外的。我国则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一则,新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未遂等的处罚规定原则上实用于各种犯罪,而且处罚未遂并不以刑法明文规定者为限;二则就分则而言,对各种犯罪具体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也比较大,可以适用于各种形态的犯罪。可见,此观点之所以错误,显然是因为只简单移植某些外国刑法理论的结论但未做深入分析所致。
第三,众所周知,危险犯与实害犯相对,两者是从处罚根据的不同对犯罪所作的一种分类。其中,“把被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不是把发生侵害法益的现实作为处罚根据,而是把发生危害的危险状态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叫危险犯”(注:(日)山口厚:《危险犯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显然,不能因为两种犯罪处罚根据不同就认为两者构成既遂的标准不同。否则,“处罚根据”岂不成了“区分既未遂标准”的代名词?既然“危险犯”一词仅仅意味着它与“实害犯”的处罚根据不同而已,并非指两种不同的既遂形态。换言之,并不意味着危险犯就是既遂犯。所以,退一步讲,即使行为人的行为已造成一定的危险状态,已符合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我们也只能得出结论说:该行为人已构成犯罪,需要予以处罚,但仅此而已。并不能因此还认为,该行为人就构成犯罪即遂。
第四,尽管刑法分则为危险犯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但也不能由此就认为危险犯属于既遂犯。因为,刑法总则虽然规定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但并未强调说对未遂犯就不能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其实,当刑法需要强调对某种未遂犯特别处罚的时候,完全可以规定比按既遂犯从宽时所处刑罚更重的独立法定刑。这样规定的必要性和优点在于:它杜绝了对此类未遂犯作更大减轻处罚的可能。(注:候国云:《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义》,《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
第五,通说认为,立法者之所以把本来属于未遂形态的危险犯上升为犯罪既遂,是因为这些犯罪具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将其未完成形态往前推移,才能给予严厉的打击。笔者认为,这也难以成立。诚如论者所言,刑法关于犯罪形态的规定应是犯罪的客观规律性与立法者主观意志性的统一,既然犯罪人犯罪的主观意志和行为是犯罪要件事实之一,是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立法评价就不应忽视犯罪人主观目的的实现与否这一客观存在。否则在司法实践中就很难行得通。比如,行为人出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动机,无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故意实施破坏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行为,显然不是仅仅为了对交通工具造成某种倾覆或毁坏的“危险”,而是要追求对社会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和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等实害后果。但按通说,只要足以“造成某种危险”,尽管尚未发生严重后果的,也是犯罪既遂,这怎能服人?(注:段立文:《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宏观研究》,《法律科学》1996年第5期。)为重要的是, 这不仅不足以服人,而且还会产生诸多弊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不利于对其教育改造。比如,食堂临时工李某,因工作原因受到领导批评便怀恨在心。某日乘无人之机将1两多“甲胺磷”倒在发馒头用的酵母面内。 炊事员不知酵母面内有毒,便和面粉50斤做成馒头。但在卖给夜班职工食用之前,李某怕因事情弄大受到法律制裁,便主动向领导交代了上述投毒行为,从而避免了一场人员伤亡事故。显然,李某及时中止犯罪,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是值得鼓励的。然而,按通说此已构成既遂。(注: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27页以下。)这样就很难起到鼓励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的作用。
第六,如果按照通说,同一种罪名的犯罪将有两个不同的既遂标准。比如,同为放火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是既遂,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是既遂。这岂不是在同一个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不仅如此,若按通说,在同一个罪名下还将有两个不同的未遂形态。因为,一方面。危险犯的犯罪未遂只能是尚不具备危险的形态;另一方面,对实害犯言,只要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并且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发生实害结果的,不论是否已经出现了危险,则均为未遂。换句话说,即使出现了危险状态,只要尚未发生危害结果,就属于未遂。问题是,这岂不与危险犯的既遂犯状态相重合?这岂不是说,该犯罪既是既遂犯又是未遂犯?在笔者看来,诚如论者所言,导致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与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有关。因为,从逻辑上讲,危险犯是否属于既遂,首先应确定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正确标准,然后再以此为标准加以区分。而通说却恰恰相反,它是先将危险犯、连同行为犯、结果犯等均认定为犯罪既遂的形态,然后再找被认为能支持这种划分的标准。显然,这种以论题的真实性来论证论据的真实性的论证方法,势必陷入逻辑上的混乱。(注:李居全:《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探讨》,《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
第七,实际上,危险犯并非犯罪的既遂形态,而只是与之对应的实害犯的未遂犯而已(注:杨敦先:《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对此, 可从人们关于未遂犯性质的判断上得到佐证。因为,众所周知,“对未遂犯实施处罚的根据,是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性”,(注:(日)早稻田大学教授野村稔:《刑法中的危险概念》,载《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换言之,未遂犯是公认的危险犯,即未遂犯以发生危险状态为前提。(注: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36页。)当然,如前所述,通说之所以反对将危险犯视为实害犯的未遂犯,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这将“排除对危险犯的未遂犯进行处罚的可能”。笔者认为,对此担心没有必要。因为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并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即使现实的危险并未发生,也完全可以按实害犯的未遂犯进行处罚。就持通说论者所举上述例子来说,既然刘某已将一根铁棒往正在使用中的铁轨上捆绑,而且一旦绑牢将足以危及行车安全,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造成危害,显然这已符合119条之罪的未遂犯, 只不过是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