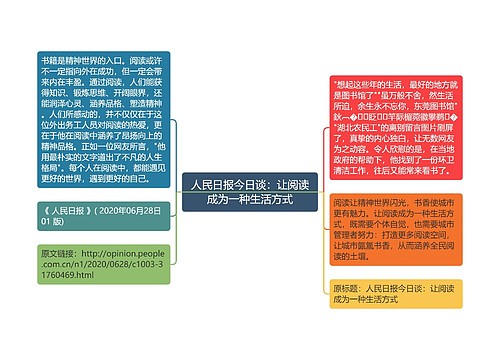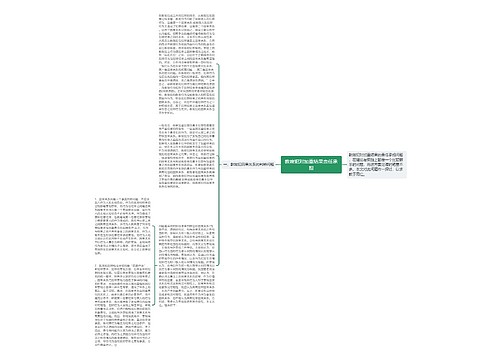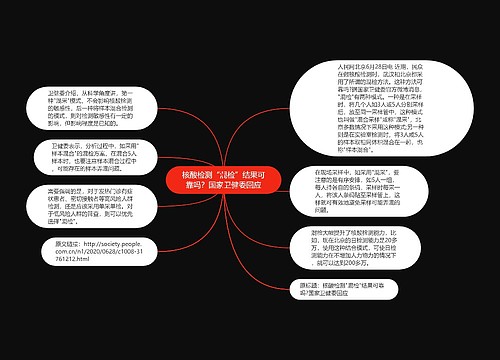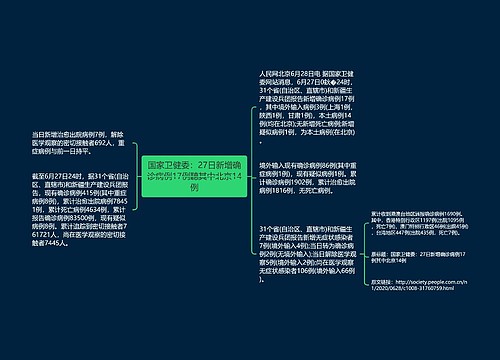该说认为现行刑法第29 条第1 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只有在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才成立,即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须成立共犯关系,教唆犯的成立及其形态都依附于实行犯,这就是教唆犯的从属性。但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不是比照实行犯的刑事责任,而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追究,这就是教唆犯在处罚上的独立性。只有这种情况的教唆犯才存在教唆犯的未遂问题。现行刑法第29 条第2 款所规定的教唆犯,是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形,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根本不成立共犯关系,但现行刑法仍对其规定了刑事处罚原则。这种情形的教唆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也无刑罚的从属性,亦即只有独立性。该说否定刑法第29条第2 款有存在教唆犯未遂的余地,但如何理解该款则见解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既遂说。该说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仅止于教唆,一经教唆完毕,其犯罪就已终了,不论被教唆的人是否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均构成既遂犯。实际上该说以教唆行为为标准,即只要被教唆者接受了教唆,并产生了犯罪意图,教唆犯的行为即达到既遂。此说的论据欠缺说服力,它机械地将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割裂开来,视教唆犯为举动犯,与教唆犯二重性说理论相左。更何况, —行为实行终了并不等于犯罪既遂,还存在实行终了的未遂的情形。
第二,特殊教唆犯说或成立说。该说认为这种情形的教唆犯不构成共同犯罪,不是犯罪的任何一种停止形态,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特殊教唆犯或犯罪成立,而没有必要再认定其是犯罪的哪种形态,应根据其本身的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从轻或减轻处罚。因为在被教唆者没有犯教唆之罪时,我国刑法第29 条第2 款只规定如何处罚,并未规定“以未遂犯论”,因而对于这种情况,只要依教唆犯定罪,根据刑法第29 条第2 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就可以了,无需确定为教唆犯的未遂与预备。此说将教唆犯的停止形态的问题简单化,只谈定罪或犯罪成立,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第三,预备说。该说认为在这种情形的教唆犯应以预备犯论,教唆犯对被教唆者实施教唆行为,与为犯罪寻找犯罪同伙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寻找犯罪同伙正是犯罪预备的一种表现形式;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构成未遂犯的一个必要条件,被教唆者没有实行犯罪的情况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着手实行犯罪以前的行为,只能属于犯罪预备。刑法第29 条第2 款不是对教唆犯的未遂而是对教唆犯的预备所规定的处罚原则,因为刑法第23 条已有未遂犯的处罚,没有必要再对教唆犯的未遂作同样的规定;而教唆犯罪的预备比一般犯罪的预备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有必要对之规定一个比刑法第22 条一般预备犯处罚原则更为严厉的处罚方法。有学者认为预备说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其一,它所坚持的实行犯着手犯罪前教唆行为只能视为犯罪预备的观点,完全是外国刑法学中具有客观主义片面性的教唆犯从属性说的见解,而不符合我们所坚持的教唆犯二重性说的要求。按照教唆犯二重性说的观点,教唆行为因刑法总则的修正性规定与具体犯罪的结合,也属于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实行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教唆行为已不能等同于非教唆犯罪情况下寻找共同犯罪人的预备行为。教唆行为的着手实行和完成都不受实行犯是否实行犯罪的制约,但是教唆犯的既遂却要以实行犯完成犯罪为标志,因此,在教唆犯实施了教唆而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下,教唆犯构成的不是预备,而只能是未遂。其二,它对刑法第29 条第2 款所规定的处罚原则的解释是错误的。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往往危害较严重,对此刑法在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中已作了充分考虑并有所体现,因此,对教唆犯罪的预备、未遂等,应该结合教唆犯罪和犯罪的预备、未遂的有关规定来处罚,而不应认为在犯罪预备的一般规定之外,法律还规定有—个较重的对教唆犯罪预备的处罚原则。所以,刑法第29 条第2款是对这种情况下的教唆犯要按照未遂处罚的明示和强调。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