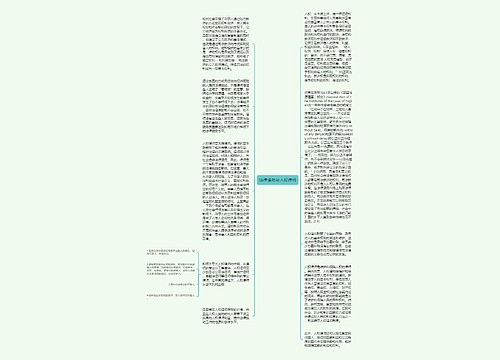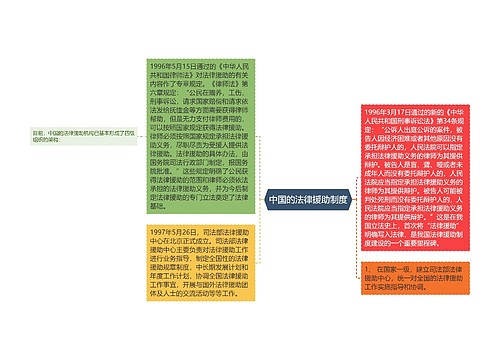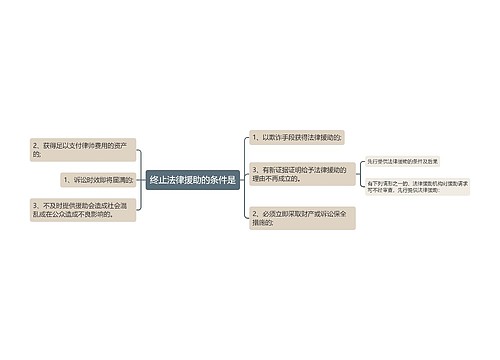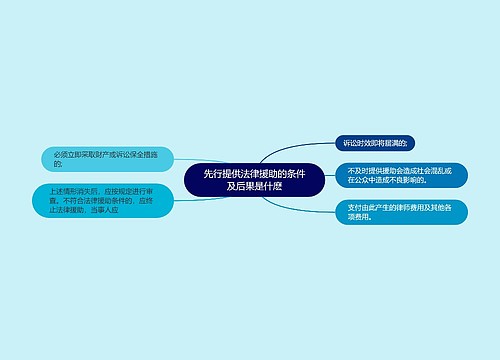首先的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负有法律援助的责任?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可能有多种理由,例如可以从政府的性质、功能和职责等各个角度予以解说。对此,本文不作详尽的分析。考虑到《条例》是一项行政法规,从增加的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权力角度看,政府是因为有一项有效的法律的存在而负有法律援助的责任。尽管这一理由显得不是那么丰满,却是现代社会依法行政原则的体现。当然,如果继续追问政府为什么要依法行政,则涉及到一个很大的政治哲学问题。
我们的兴趣在于,律师负有法律援助的义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吗?因为《律师法》和《条例》有规定,所以律师有法律援助的义务?从《条例》的主旨看(《条例》第1条的规定),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的法律帮助,以维护其法律赋予的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问题在于,是谁在为当事人实际上减免法律服务费用?进一步的追问是,律师为什么要减免法律服务费用?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有规定吗?
事实上,在法律宣布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之前,律师一直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事实上,长期以来,即使贪婪的律师法律服务市场总是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指责和不满,对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律师也没有中断过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事实上,法律援助的十年实践中,律师是主要的实施主体。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因为政府给予律师必要的办案补贴,因为政府集中管理和分配法律援助案件,就宣称为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对律师而言,应当是一项职业伦理,它源于律师在法律实践中对司法正义的自觉追求。律师的职业伦理或职业道德,首先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律师作为普通人表现出来的对弱者的同情、怜悯或不忍,例如,卢梭的观点。[3]它毋宁说是韦伯、涂尔干意义上的职业伦理。职业伦理,是对一种被称为天职的概念的表达。天职起初具有宗教的色彩,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做的事。在政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职业,职业既是对人的一种身份定位,也是对具有某种职业的人的社会责任的界定。“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4]虽然中国人不说天职,在传统上也不大说职业伦理,但中国人一直在讲分,例如说“做分内的事”。分内的概念首先隐含了规范特别是道德规范。不过,分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更主要是一种身份关系,而不是职业关系,因此,在强化人的身份伦理,而不是职业伦理方面,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有其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是,分的概念所蕴涵的内在规范却可以与天职相通,做好分内的事就是在履行天职。
职业伦理是不同职业群体的道德规范,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各自的道德特殊主义。涂尔干说:“有多少种不同的天职,就有多少种道德形式,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只能履行一种天职,于是,这些不同的道德形式便完全适合于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5]而所有形式的道德都在不同的领域关怀、关心和维系含有普遍道德因素的公共品质,否则,特殊的道德就是有缺陷的。[6]律师职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比之其他社会职业更为浓厚的公共性质。这种性质主要源于对作为公共产品的法律的适用和维护。即使从纯粹功利的角度考虑问题,律师也需要在维护法律的尊严的名义下才能获得赖以生存的报酬。在法律服务市场上,律师与当事人的交往的确像是一个典型的交易:你给我钱,我给你正义。在这场交易中,法律和正义似乎成了律师手中囤积的私品,随时用来出售给前来购买的当事人。然而,这种表面上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即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也不能得出法律和正义可以被交易的结论。律师制度的合理性不能从律师是否与当事人存在交易以及交易的程度方面来考察。在任何一个存在律师制度的社会中,律师分享了与法官、检查官以及任何解释和适用法律的人或机构的权力是问题的关键,而且重要的是,律师在科层体制之外获取了这种权力,这意味着律师一方面在适用和解释法律,另一方面却免除了科层之累而获得更大的独立性。权力分享者和共同使用者可以达成一种有目的的共谋,但也可以造成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对抗和制约。律师在与其他权力主体的对抗中获得力量和尊重,形成了律师获取职业荣誉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职业荣誉在考察律师职业伦理的作用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此外,我们还需要把律师个体获取利益的本能与律师职业团体追求正义的努力区分开来。在现实的力量面前,对律师个体而言,对利益和正义的关系的平衡艺术总是难以驾驭的。韦伯曾经正确区分了以政治为业的两种形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而生存。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者。不过,韦伯认为,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至少他有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他也肯定会两者兼而有之。‘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为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中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从这种内心的意义上,所有为事业而生存的忠诚之士,也依靠这一事业而生存”。[7]如果套用韦伯对政治职业的两分法,那么,律师职业也可以分为“为”法律而生存和“靠”法律而生存两种情况。我们坚信,在律师执业的长时段内,所有为法律而生存的律师,也依靠法律而生存。这一结论与其说是价值判断,不如说是事实判断,对后者而言,最为紧迫的任务是需要弄清楚哪一种状态被现实所张扬,而与此同时哪一种状态被现实所遮蔽,以致出现了两者关系不协调、不均衡或失范的局面。
米尔恩指出:“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的。假如没有这种义务,那么服从法律就仅仅是谨慎一类的问题,而不是必须做正当事情的问题。------假如没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那就不会有什么堪称法律义务的东西”。[8]因此,如果没有这种律师的职业伦理和道德义务作为基础,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法律规定律师有帮助穷人的义务?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市场经济社会,法律为什么不规定富人有帮助穷人的法律义务?为什么选择了律师?是因为律师懂得法律?是否有必要用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令律师为穷人无偿地贡献他们的法律才智?如果政府一方面宣称法律援助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因指派关系而由律师承担,那么,究竟是谁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就会成为问题。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