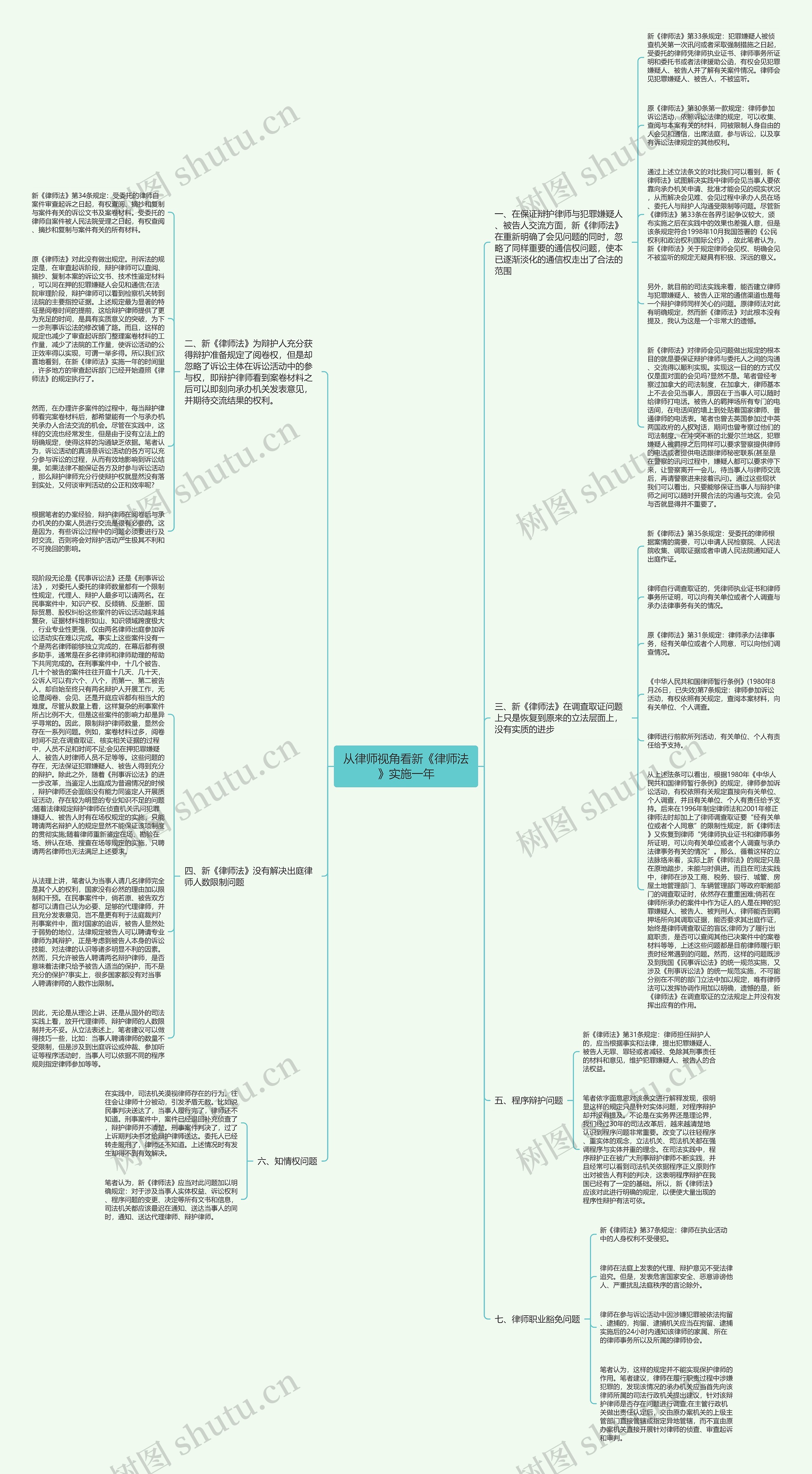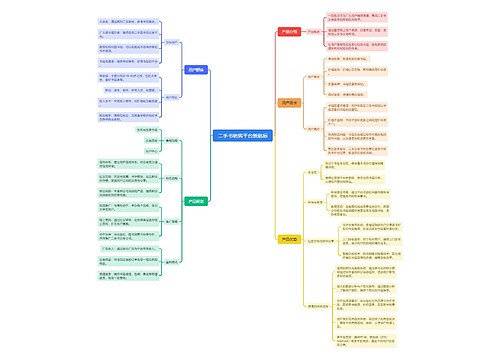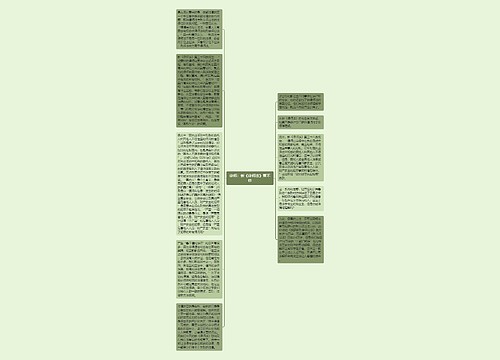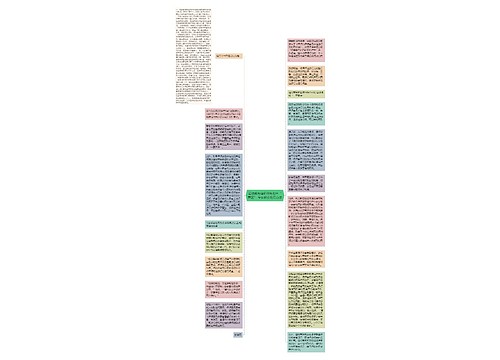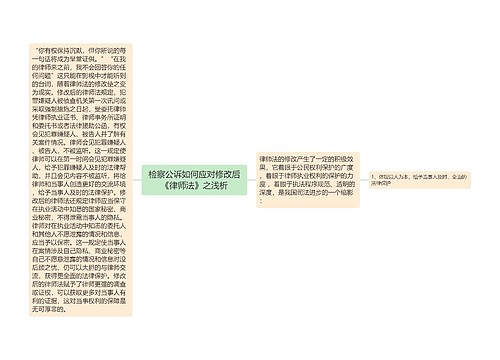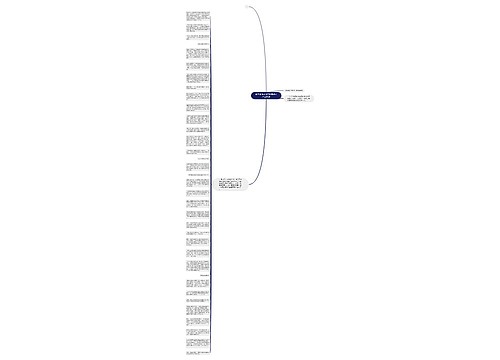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原《律师法》第30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通过上述立法条文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新《律师法》试图解决实践中律师会见当事人要依靠向承办机关申请、批准才能会见的现实状况,从而解决会见难、会见过程中承办人员在场、委托人与辩护人沟通受限制等问题。尽管新《律师法》第33条在各界引起争议较大,颁布实施之后在实践中的效果也差强人意,但是该条规定符合1998年10月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故此笔者认为,新《律师法》关于规定律师会见权、明确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无疑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另外,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能否建立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常的通信渠道也是每一个辩护律师同样关心的问题。原律师法对此有明确规定,然而新《律师法》对此根本没有提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问题做出规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辩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得以顺利实现。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仅仅是面对面的会见吗?显然不是。笔者曾经考察过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在加拿大,律师基本上不去会见当事人,原因在于当事人可以随时给律师打电话。被告人的羁押场所有专门的电话间,在电话间的墙上到处贴着国家律师、普通律师的电话表。笔者也曾去英国参加过中英两国政府的人权对话,期间也曾考察过他们的司法制度。在冲突不断的北爱尔兰地区,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之后同样可以要求警察提供律师的电话或者提供电话跟律师秘密联系(甚至是在警察的讯问过程中,嫌疑人都可以要求停下来,让警察离开一会儿,待当事人与律师交流后,再请警察进来接着讯问)。通过这些现状我们可以看出,只要能够保证当事人与辩护律师之间可以随时开展合法的沟通与交流,会见与否就显得并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