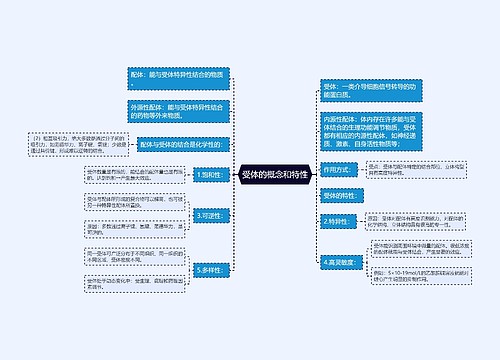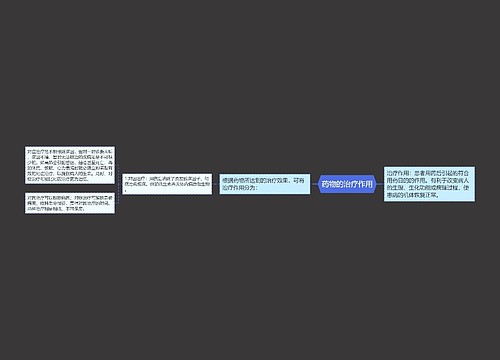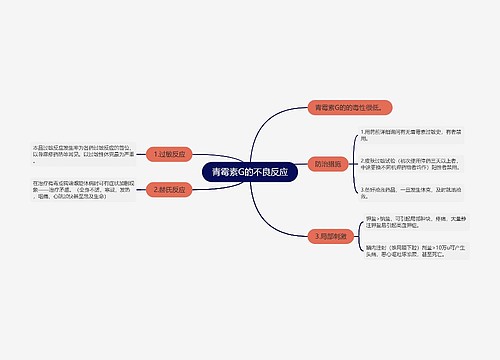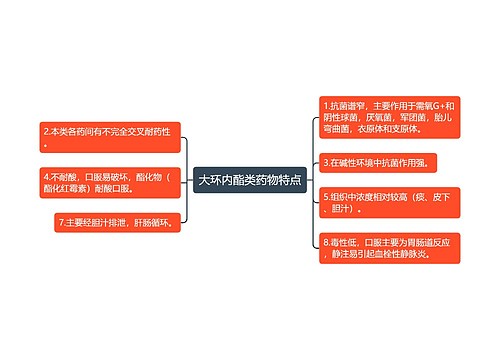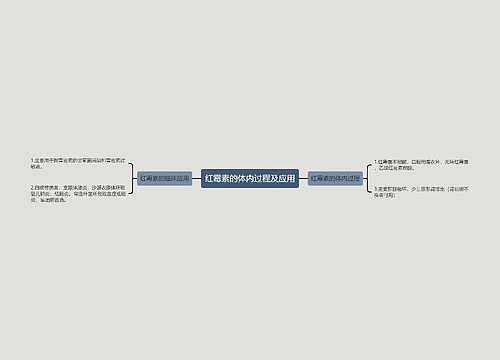没到过全国政协医卫界的讨论现场,你很难想象医务界对医患关系的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凌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医闹已达到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
而在医闹升至“史上最为严峻”的关头,公众对医生的信任也几乎降到“史上最低水平”。
于是,医生接诊怕患者找茬碰瓷、患者就医怕医生不负责任医患关系俨然成为一个雷区,没有人敢轻易通过。
此种局面已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在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改善医患关系”的相关表述赫然在目。
在凌锋看来,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特殊场所,少数患者家属在医院内挂横幅、设灵堂甚至行凶等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医疗秩序,对医护人员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伤害,医生无法集中精力为患者看病。她建议制定《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保护医院和医生正常行医治病。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亦看到医患纠纷的严重性,但他坚称,医生对患者更加负责才能真正消除双方的不和。“病人闹医院肯定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想想,有多少病人本意就是为了闹医院?他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找事儿的!这些年一些医生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儿,药厂请吃喝,埋单的是患者。误诊误治了,受伤的还是患者。”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医闹”横行医院肯定不对,但也要看到医疗纠纷背后的复杂原因。
从许多患者的角度看,红包、回扣的行业潜规则使他们在就医之初就提心吊胆,生怕医生为一己私利对自己痛下“黑手”——用“大处方”、“大检查”使自己多花钱、花冤枉钱,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在诊治的末期,倘若一切尚属顺利,患方纵然心里存有不快,往往也还能以“花钱买平安”的态度自我安慰,但若是花了大钱还没能治好病,患方的不平衡感会急剧增加,认为医生和医院“图财害命”,希望通过“闹”来避免“人财两失”。
而医方普遍认为,医学是一门充满局限性和风险性的学科,远未达到包治百病的程度,对大多数疾病来说,医生只能是缓解、拖延,而不是治愈。在不少医生看来,患方对治愈的要求近乎苛刻。至于态度生硬冷漠,那是工作繁忙所致;红包回扣,在一些医生眼里是对这个岗位“高风险、低收入”的灰色补偿。
显然,这涉及到中国公立医院当前急需转变的运行机制。据黄洁夫介绍,在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约为医院收入的7%~15%,剩下的运营费用都要靠医院去挣。而医院最重要的挣钱手段是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于是,众多医院纷纷制定相关政策,把医生收入与病人缴纳的费用挂钩。
一旦出现医患纠纷,目前有三种通行解决方式:一为“私了”,即患者借助私人力量和医院达成解决协议;二为“官了”,即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主导下,按照正常程序达成解决协议;三为“司了”,即通过司法的介入等达成解决协议。
现实中,患方青睐的往往是第一种解决途径。这与公众对主管部门和医疗鉴定机构不够信任有关——卫生行政部门是医院的“老子”、医疗鉴定人士是医生的“兄弟”。从根子上说,依然是体制使然。
中国60%以上的医疗纠纷由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态度引起。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提供的数据。
医务界流传着这样一个“四句话说死病人”的故事。一位农村患者好不容易借上钱,去他认为“水平高”的县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专家见面看了看检查报告,接连说了三句话:“你来晚了”,“没治了”,“回家吧”。这时病人的精神快受不了了,急忙央求医生:“大夫,您给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求求您了。”医生又说了第四句话:“你早干什么去了?”病人当即站不起来,没出医院大门就一命呜呼了。
前述案例或许比较极端,但常见的情况是,如果患者多问几句,就很可能遭到医生的白眼,不少患者受过类似教训:“你只需要照我说的做,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
一些医生的这种“知识傲慢”、“技术傲慢”,很容易让患者产生权利被漠视的感觉。而在后续的医疗过程出现问题时,这种沟通的不顺畅将迅速点燃患方情绪。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然而在当前的中国医界,“语言”已经被相当一部分医生抛至脑后、逐渐淡忘了。
许树强说,人文关怀在实际工作中收效不大,其重要原因是医院缺少人文关怀制度的建设和政策导向,缺少由人文关怀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环境。他建议,在对医务工作者的教育培训中,要加大对伦理、法律、心理、沟通、社会学等体现人文知识的内容,引起医务工作者对医学人文的重视,并变成自觉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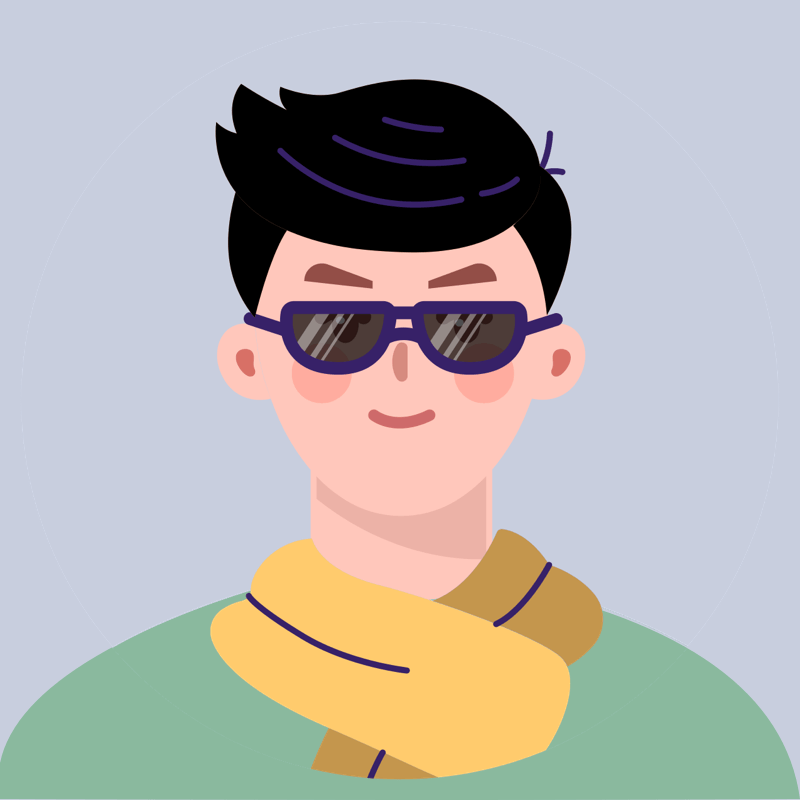 U245265618
U24526561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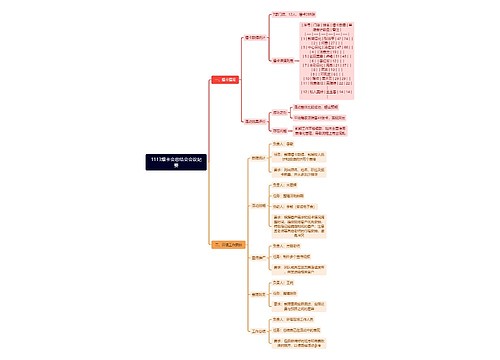
 U381614141
U381614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