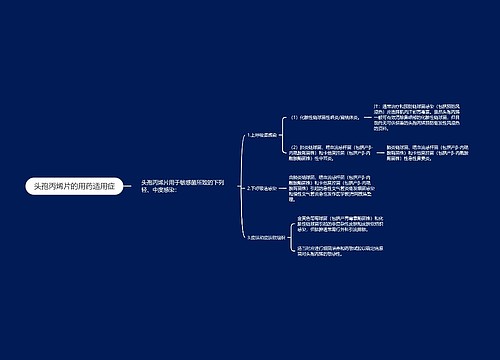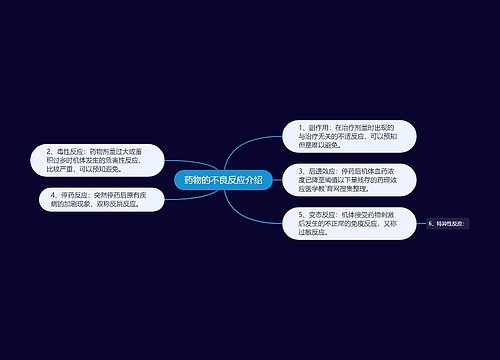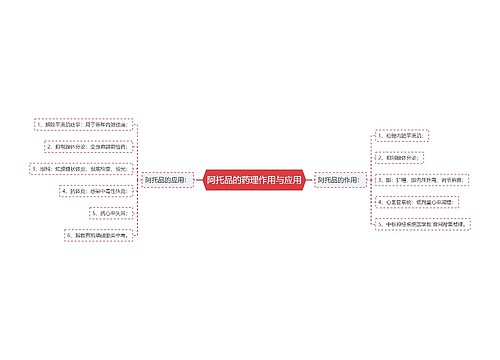Gerald Lazarus因此认定,在中国行医是危险的,中国医生“非常可怜”。尽管如此,对中国大部分医生来说,除了偶尔发发牢骚外,他们只能选择面对每天一拨儿又一拨儿排着长队的患者。
一名姓董的年轻医生抱怨说,和国外相比,中国的医生不但辛苦,而且收入很低,在发生医患纠纷时,常常得不到保护。“医院领导躲得远远的,生怕误伤;医务科出面对患方说小话,无论有没有责任都自觉理亏;出现赔偿,医生护士自掏腰包;赔完钱,本来没责任,也会被认定有责任。如果患者打人,医院保卫科一般不敢上,甚至有的警察也看热闹。”
在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中,44%的受访医师认为,一些人民法院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显失公正,并且八成以上的人称“媒体对医疗纠纷的报道不客观”。
这种情绪正在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当一些医生感觉到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可能踏进牢房时,他们也许会视患者为“对手”,在治疗活动中将自我保护上升为第一原则。
一名资深医生曾经告诉记者:“我和我的同事,在平时的工作中,满脑子就是尽量不要干什么事情,尽快把病人打发走,别在我这里闹事就行了。结果就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加剧,直接导致后者的利益受损。”
在网络上,不满的情绪发泄更是俯拾皆是。“我们这里一些医院都开始消极怠工了。不积极收病号,不加床,高风险的手术不做,周六、周日不加班做手术。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费力不讨好。不知道再发展下去会怎样。”“兄弟们,在政府、媒体及民众均将所有矛盾归结为医生的黑、贪婪的恶劣环境下,工作悠着点儿。”
“假如自我保护上升为医生的第一原则,将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解释说,大家通常所说的医生为了自我保护让患者过度性检查还只是小事情,更可怕的是,面对不熟悉的疾病,医生不再敢去探索,本来有希望攻克的疾病或许就耽搁了,整个医学科学也会因此停滞不前。
显然,责任不能完全推给医生。“多年的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医院和医生从谋生到牟利,继而将原本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推向敌对一方。”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说,他相信整个医疗队伍是好的,“非典时期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数据显示,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的只占7%,有的三甲医院甚至只有3%,其他靠医院自筹解决。
如果说对立情绪仅仅局限于一代人,解决起来或许并不困难。可不幸的是,怨恨总是“遗传”的。医患的对立不仅仅影响到现在的医生和患者,而且还影响到未来的医生、未来的患者。
在复旦大学医学院的BBS上,一篇名为“医生如何保护自己”的帖子在精华区挂了很久。该帖用条令的方式教导医(学)生:门诊的诊断须谨慎,尽量全面但模糊,留回旋余地,比如“黄疸原因待查”等;详细而且有选择地记录患者及家属的于病情治疗不利的要求及行为,部分要求其签字……目的无他,唯求自保。据说,很多医学生看后奉之为行医必备的“葵花宝典”。
自保的理念甚至走进了课堂。26岁的住院医陆嘉回忆说,大学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讲的一个小事例:一个患者家属对手术不满意,和医院大闹起来,声称没有在术前告知他风险。医生就拿出谈话记录说,这有证据证明我们已经尽了义务。没想到,病人家属一把将谈话记录抢了过去塞进嘴里吃掉了。从那以后,这个医院把病例全都锁起来,以防被抢。
《医事》的作者讴歌,也讲过类似的故事——有一名医学生问她的导师:“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医生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儿?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学生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学生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医生终于抬起了头:“你想过没有,你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例记录吗?有人证吗?”
尽管这只是个个案,但医患间的不信任可见一斑。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多年医生的于宗河老司长总是怀念他当医生的那个年代,“医生是多么受人尊敬的职业啊”。
在今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卫生部要把优化医疗执业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配合宣传、公安等有关部门,开展‘平安医院’建设,努力营造尊重医学科学、尊重医务人员的社会氛围。切实维护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正当权益,坚决打击破坏医院秩序的违法行为。”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