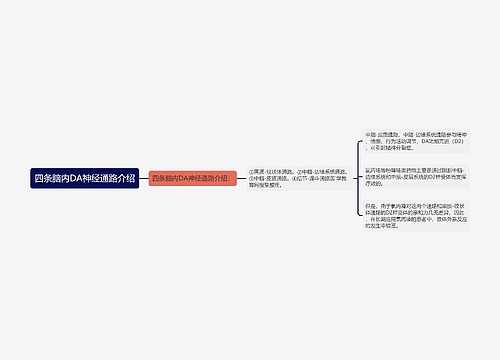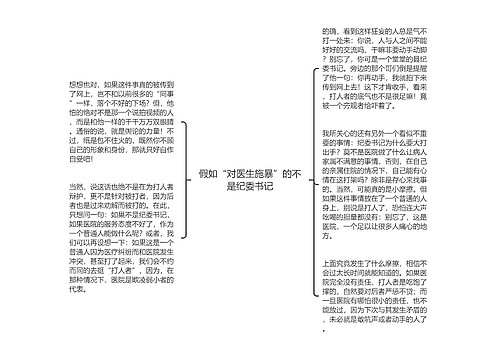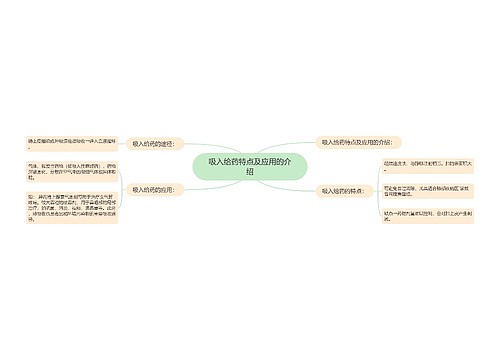坦率地说,医患间天然具有的专业性鸿沟是妨碍医患互信的重要瓶颈,但因专业信息不对等带来的医患不对称博弈并非是难以克服的鸿沟。例如医疗保险体系的构建,使现代医疗市场变成了复杂的结构性服务市场,患者向保险机构购买健康和疾病险等导致医疗服务市场出现医疗服务供给主体、服务接收主体与支付主体的三分离。即医院向患者提供专业医疗服务,而最终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是保险机构,同时保险公司或自身配置医学人才或外聘专业的医疗服务评审公司,决定向那个医疗服务主体购买服务等,从而在机制上使医疗服务的供需具有专业对称性,消除了医患间因专业不对称直接导致互信风险。殊不知,患者通过购买保险把监督和评判医疗服务质量的责任让渡给保险公司,而专业的医疗保险机构则使其在医疗专业知识上与医疗服务机构具有较高的信息对称性,使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事故和过度医疗不仅侵犯患者权益,而且直接侵犯了保险公司权利,从而在医疗市场出现对等的制衡主体。
遗憾的是,当前虽然国内医疗市场也引入了保险体系,但整个医疗制度体系和市场秩序却未能有效培育出对等的博弈主体,医保机构对医疗服务机构制衡的缺位和不到位,反而使医生与患者成为了医疗纠纷的直接冲突主体,进而使医疗纠纷直接蜕变成了医患纠纷。
垄断地位的公立医院在性质认定上并非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既具公益性又带有市场逐利性的特殊组织。以公立医院为主的医疗服务机构的角色紊乱,使国内的医患关系并不具有民法的主体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等三大特征;同时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和医疗服务机构的去事业化,又使医患关系并非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从而导致医患关系蜕变为一种难以有效定义的医事关系。
而卫生部则事实上肩负老板加婆婆的双重角色。尽管新医改提出了管办分离,但卫生部拥有研究区域卫生规划、统筹规划与协调卫生资源配置、医院人事任免以及公立医院公共财政预算拨付的管理权限等职能,使卫生监管部门与医院间不仅难以实行管办分离,而且卫生监管部门与医院带有明显的上下级依附之利益关系,致使卫生部监管更多是对医院的呵护而非规制。因此一旦出现医患矛盾,患者诉求很难基于卫生系统的医疗事故仲裁机构等获得伸张。殊不知,当前由卫生监管部门主导的医疗事故仲裁机构,以及最近为缓解医患矛盾而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够提供专业医疗行为评估的主要来自医疗系统的专业人士,这使医疗事故仲裁变成内部人评估,无法使患者相信同行人的仲裁结果的独立性和可信性,从而更容易激化医患矛盾。因此,这种卫生部主导的医疗事故责任仲裁,无疑很容易变成整个卫生医疗系统与患者间的不对等博弈。是为当前医患关系日趋激烈和紧张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医患关系本质上是医院与患者间的关系,而非医生与患者间的关系,因为医院与医生是雇佣关系,医生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然而,医患关系蜕变为患者对医生的敌视,则暴露出了当前国内医疗卫生体系所存在的严重责权和角色紊乱风险。当前尽管从医疗纠纷争端机制等制度设计上,医院和医生在医患纠纷上都相对患者占优,特别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去掉了医患纠纷中的辩方举证条款;但事实上医疗制度对医生权利的保护是不完备的。如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具体供给主体,自然被直接推向医患矛盾前台,致使医生面临激励不相容性:由于医生收入主要源自医院发放的薪资,医疗服务收益不会直接反映为医生收入和福利,而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患者损失不仅不会成为医生福利,反而使医生不仅直接面临来自患者的侵权风险,而且还面临吊销执业资质风险。同时,由于目前的医疗制度,尤其是医疗纠纷争端机制,牵制了保险机构向医生推行医疗事故责任险的空间,导致医生既无法获得医疗制度的完备性保护,又无法利用保险分散风险。
此外,当前过度倚重医生医德等医疗伦理,而忽视构建医疗服务市场权责清晰的激励相容机制,致使医患纠纷很容易直接形成对医生医德的拷问,而处于信息和博弈不对等地位的患者自然首先把医患纠纷归罪于主治医师的医德,进而使医生而非医疗机构成为患者非理性攻击主体。这无疑遮盖了医患互信缺失的制度性障碍——患者在同医疗体系博弈中面临的信息和制度等双重不对等性。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