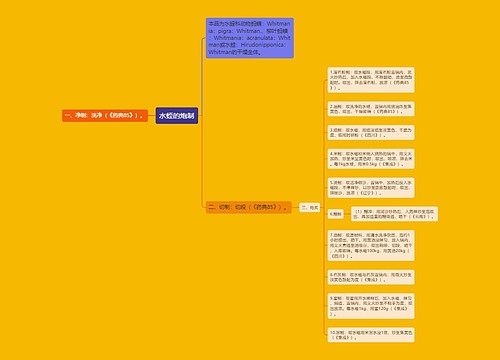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人类生物学要比大数人想象的复杂得多。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另一个造成新药物和新疗法迟迟没有问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物医学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未能把握住1万亿美元的医疗科研支出所带来的最新科学。这些最新科学不仅包括基因学,也包括神经科学、纳米科技以及环境对DNA的影响等各个领域。
这种“新生物学”目前仍处在襁褓阶段,它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况且,当前我们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所以无法确知究竟其中哪些部分才能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或者降低医疗保健成本;也不知道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究竟谁才能够运用这些科学知识。
不过,我们仍有希望迎来一种新的医疗保健方法,它与现行医疗保健方法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这种方法将基于:1)利用某个人的基因和其他生物标记,加上传统的诊断测试以及家族病史,来预测他未来的健康状况;2)利用设计好的防病策略来使人们保持健康,而不是等到患了病再去治疗;3)加强调个性化、定向化的医疗保健和治疗方法。
这种新科学还将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关于他们自身健康的信息,使那些希望能为自身健康担负起更多责任的人能如愿以偿。
不过,未来可能出现的生物转化技术却撞上了“传统”这堵墙。此外,科学、医学、政府、商业和法律基础设施的落后,也阻碍了生物转化技术的发展。虽然这些领域自身在做出重大发现时,都纷纷表现出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然而在适应“新科学”的过程中,这种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却并未得到体现。
例如,尽管法律界已经争论了30多年,要给DNA下一个法律定义,而且这个法律定义可能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的法律系统却仍未决定是否可以对基因授予专利权。再比如,要对数千种新发现的基因标记进行验证,就需要进行人体试验。做试验当然需要花钱,但投资人迟迟没有为这些试验买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尚未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法,使企业能够享有DNA测试的开发权或此类开发的许可权。另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目前也还没有弄清楚,如何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基因标记——尽管他们正在努力。
此外,生命科学界也应承担一些责任,生命科研系统已经变得过于细化和专业化了,就连类似领域的各研究机构之间也很少相互通气,他们与医生、病人之间的交流就更少了。这使生物医学界很难将单独的研究成果融入对人体的全盘理解中。
最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启动了一系列计划,重点在于加快从科研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转化过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所划拨的总计400亿美元的资金只到位了2%。一些代表病人的游说团体,例如“病人如我”(PatientsLikeMe)和迈克尔 福克斯基金会(Michael J. Fox Foundation),正在努力填补这些预算空白,使科学研究更快地运用到实际治疗中。不过去年,所有非营利机构和私人机构的预算加在一起,也只有不到20亿美元。
这些预算远远不够,因此,许多志同道合的生命科学界、病人游说团体和医疗保健界的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他们呼吁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通力合作,加速科研发现向实际应用的转化过程。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足够的资金以及全面的计划,它的规模至少要相当于最初的人类基因组工程(Human Genome Project)。
他们将在华盛顿特区发表一份名为《个性化健康宣言》的简短声明。这份宣言是由尤因 马里恩 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资助并发起的,由35位专家共同起草。他们代表了科学家、医生、企业家、投资人、病人游说团体、伦理学家、律师、政策制定者以及新闻记者等各界人士的不同意见。
虽然对于变革的迫切需要得到了许多生物医学界人士的理解,不过要改变一个如此根深蒂固的系统,绝对会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任务。为了我们的健康——也为了我们花在医疗保健研发上的钱物有所值——让我们祈祷他们的努力能够成功吧。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