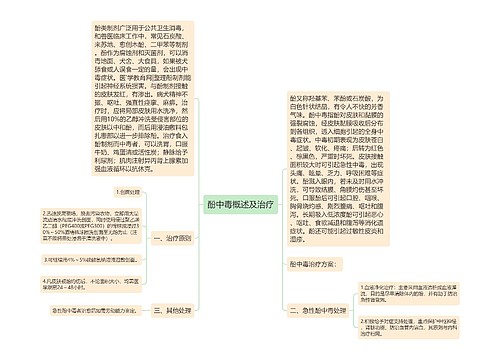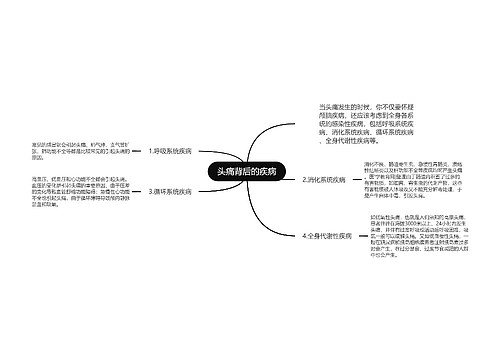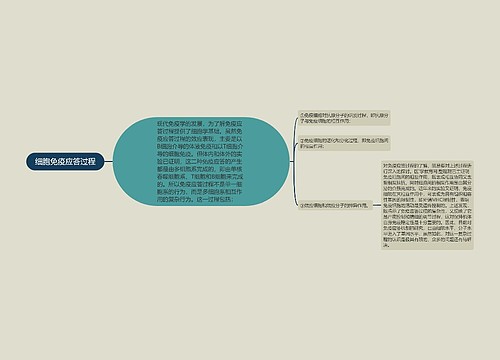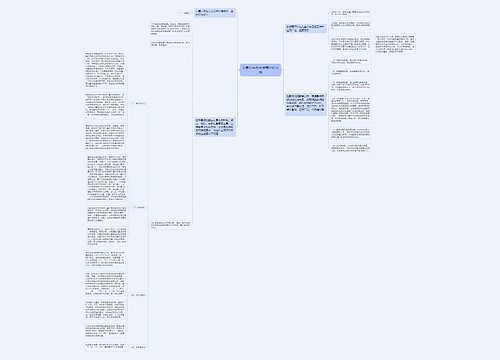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法律制度,在其发展、变迁和转换的过程中间都充满了来自于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以及价值导向等一系列因素的干预和影响。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来说,那些适应了这种社会转型所导致的逻辑变迁的制度和观念,经过人们的利益选择之后,自然的保留、生存下来,乃至在日后的生活实践中被人们屡试不爽,在自由选择中占据了市场,从而逐步地发展壮大。仲裁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其独特的性质决定了其生存和发展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强劲趋势,几乎(而非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运作所形成的结果。在仲裁制度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充分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理纠纷的公正性与效率性,其一方面比人民调解制度具有更高的专业性,另一方面较之法院的诉讼程序又具有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因此倍受现代社会尤其是商业领域纠纷解决机制的青睐,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非诉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和制度出路。
就在不远的十几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具有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中国正从单一所有权关系、高度行政化的社会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多元所有权关系、分权自治的社会类型。在所有制的结构形式上,虽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占有大头,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也必然导致利益主体的独立化和社会价值观念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在市场逐步放开之后,原来被社会固有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禁锢了的“社会分子”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市场浪潮鼓动下,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起初在某个社会特定的大环境下不断的运动,在运动和相互碰撞之间,激活了社会中的某些积极因素,随后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迅猛发展。在这种“社会分子”(社会中独立个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某种愿望和动力)不断的无规则运动的状态下,必然导致其相互之间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索引发的后果就是社会矛盾(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商业纠纷)的迅速激增,而往往又由于“经济先行”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念导致我们的社会对于如何解决这些纠纷找不到合理的方式和途径,而社会的本体在需求上又要求我们(不光只有法律人)对于这种现象予以制度和方法上的回应,于是在供给与需求上出现了某种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应当预想到而往往又被忽视或根本就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带来某种“学术无用”尴尬局面。
然而,用一种不太“后现代”的语境来分析和阐释这一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往往不因为人的因素而受到改变。在以经济交往为主要生活方式和符号系统的商业社会中,当再也不存在一个高于利益主体的人或组织像上帝那样为一切人们安排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时,就只有依靠彼此之间的协作,利用他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来实现自己对于利益的追求。而这――却不仅仅是这――形成了我们今天已由应然转为自然的纠纷解决的“契约”观念。在这种“文明人的方式”的影响下,纠纷的解决由古代的沙场争战、刀光剑影、血洒疆场转变成为今天的调解、仲裁与诉讼。虽然我们认为通过暴力的纠纷解决在时效、方式和效果上往往具有低成本的优点,但是这种私力救济由于其极易引起刑事犯罪和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激增,故长期以来都受到民族国家的排斥和压制,也只有在某些极特殊的法定情形下(如正当防卫的场合),法律对于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才予以认可。
而在调解、仲裁与诉讼这三种纠纷解决的文明机制中,仲裁制度在市民社会和商业领域中往往较之另二者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当然也存在不足。与调解制度相比,仲裁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性。由于仲裁机关在市场运作中具有某种经济主体的性质,因此其必须通过聘请优秀的仲裁员对于每一个案件进行公正的裁决。在仲裁机关是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取的情况下,公正是仲裁机关赖以维系自己生命的唯一道德源泉,也是其付出得最多的道德成本。而这种对于仲裁“消费者”信赖关系的建立,必须通过对每一个案件的公正而无偏移的裁决,这样,也只有这样仲裁机关才能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得以生存。实践证明,仲裁员往往由著名的学者,律师和专职仲裁员担任,这些人往往都受过良好的法学训练。在现今的中国,仲裁员的专业素质往往要高于法院的法官。这样,仲裁的结果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容易形成一种“表面公正”,而在实质上是否公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今社会是一个“诉讼爆炸”的社会,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分子”在“受热”后的剧烈运动过程中碰撞的机会增加,更是因为人们都希望像秋菊一样“讨个说法”(当然,我并不认为案件的逻辑递增就一定预示着人们法律意识和观念的觉醒和提高)。可是,繁杂的诉讼程序,高额的诉讼成本,频繁的出庭应诉,使得诉讼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人们不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的“高消费”产品,甚至有人在写过《懒得离婚》之后还想写本《懒得诉讼》。虽然我们有学者在社会的剧烈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刻高喊“民事诉讼的契约化”,然而这种诉讼契约观念的建立毕竟不是在短期内说变就变的,也许――甚至可以肯定――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仲裁制度却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仲裁制度实行一裁终局制,即一旦作出裁决就发生法律效力,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得推翻仲裁的裁决结果。这里便省去了诉讼中上诉审和再审程序繁杂和诉讼费用的诸多问题。
其次,仲裁具有更大的选择性。仲裁当事人对于仲裁机构、仲裁员、审理方式等事项都可以进行选择,而不受到管辖权的限制。仲裁的审理往往是不公开审理,而这对于维护当事人社会形象和保守法人的某些商业秘密也具有其价值。但仲裁往往只涉及到平等社会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涉及公民身体权、生命权等重大人身权利的案件,不由仲裁机关受理。因为保障人权往往是国家的任务,而仲裁机关往往只是对于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使社会的整体经济流转趋于稳定和平衡
。在当今这个国际化的社会里,国际组织之间复杂的商业贸易活动十分频繁,这种繁荣的景象需要我们对于国际商事活动中所发生的纠纷提供一种共同的解决机制,对于各类国际商事纠纷适用共同的规则,从而屏蔽来自政府的各种压力和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找寻正义与公平。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我们每每说到正义与公平时总是带有某种来自政治因素的影响、总是在各种“禁区”之间寻找“现代法治的出路”。诉讼的进程因为受到太多的“地方性”因素的影响,从导致判决的正义往往只是种“过得去的正义”。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地方性”这个热门的词汇。正如霍姆斯所说的:“每个人在其实践中注定都是地方性的”。这样比较的意义只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说明仲裁制度的纯粹性与排除其他因素影响的技术性,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不存在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判断,目的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仲裁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契约机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一旦案件牵涉到诉讼,无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案件,总是会自觉不自觉的牵涉到关于国家利益和宏观视野的大局问题。因此,为了回避这些非契约性因素的影响,平等的商业交易主体之间通过这种非诉解决纠纷的契约来找寻纠纷解决的捷径。双方当事人通过在订立契约中扩大对方抗辩权的方法来换取纠纷解决的迅捷化和低成本化,而这往往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益的,至少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减少交易的边际成本和沉没成本,从而为双方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谋求某种程度上的实际收益。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