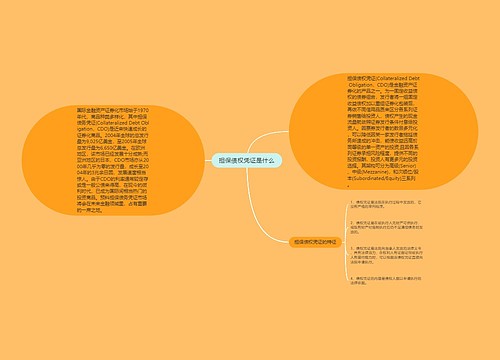破产和解与重整程序具有优先于破产程序的性质。如上文所述,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制度已更倾向于保护债务人、社会的利益;而有担保债权的行使也在破产法上不受破产程序的限制,有担保债权则把对有担保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两种利益相冲突,现今各国破产法在和解与重整程序上作出的选择结果却不同。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破产重整程序中对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加以限制达成共识。在重整程序中所有的债权,无论其性质如何皆一律平等,有担保债权的行使和其他债权一样也告停止。因为在“整理期间,很多担保物由于整理程序所需要,而不能由有担保债权人取走,而必须留给经管债务人。”[2](P187)
按英国统一破产法,处理公司不能支付的程序有四种可供选择,其中的管理程序类似重整制度,其实质就包括“限制有担保权益的债权人执行担保物权。”[3](P396)规定重整制度的日本公司更生法也规定“担保债权在这程序中也不得优先行使权利。”[4](P10)中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破产法,已有的破产法规里也没有规定重整制度,这是一大缺憾。相信不久出台的新破产法会纳入重整制度,并会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对有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加以限制。
但是,在破产和解制度上,各国依然按传统民法之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规定对担保债权的优先性不加限制。和解协议虽有强制力但不影响有财产担保或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实现其别除权(即担保物权)。如: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第37条规定:和解不影响有担保或者优先权之债权人的权利,但经该债权人同意者,不在此限。日本破产法上也规定了优先权债权人不受破产和解协议约束。我国和解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对有担保债权的优先性不加限制。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39条:经过整顿,企业能够偿还到期债务的,只能按和解协议规定的期限、数额清偿。但是有财产担保并且没有放弃优先权的债权不在此限。我国学术界也对在和解程序上限制有担保债权人的优先性鲜有同意者。邹海林在他的《破产程序和破产法实体制度比较研究》中说: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行使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约束,除非该债权人放弃优先受偿的权利。李永军在他的《破产法律制度》上也指出:从效力上看,和解程序不能限制担保物权的行使。李永军还认为和解制度的所有手段均是为了保证债务人按和解协议偿还债权而设,正是因为它是以对债权的保护为中心,故它不限制担保物权的行使,这个观点与和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与原因的不契合性,前文已论述。
笔者认为,和解制度中也需要对有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性作出适当限制。和解制度设立和发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使债务企业得到喘息机会从而东山再起。但是,民法上的“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常常使企业在因和解协议的通过与认可中得到的新生希望化为泡影。按照这一原则,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不依破产程序行使担保物权。“然而在担保物权发达的今天,担保物权往往覆盖了债务人的全部或大部分财产,而别除权的行使无疑使企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分崩离析。”[3](P394)这使得债务企业几乎丧失了重振经营的任何可能性,至少,债务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物质条件难以得到保证。所以债务人拟制和解协议向法院提出申请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后,为了履行和解协议往往需要担保债权人作出程度不等的谅解与让步。[5](P227)别除权的保护本位立足于债权人个体,而破产和解程序的设置宗旨则兼顾破产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整体利益。因而自然应以抑制别除权的行使作为解决途径。否则,预防破产的目的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无奈之下债务人只好进一步与有担保债权人达成第二个“和解协议”,而能否达成协议,大权定夺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之手,从而可能因协议的无法达成而使和解协议无法继续进行,这是有违破产和解制度设立初衷的。有的学者已认识到“和解协议对有物权担保的债权无约束力,债务人在同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后,为避免担保物被执行,往往还需要与有物权担保的债权人个别达成和解,在实践中存在一定困难。[6](P80)而且这也与商法所追求的“效率”的价值目标有违
有人将破产和解程序对有担保债权无约束力的弊端看作和解制度难以积极挽救困境企业,谋求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从而导致重整制度产生的必要原因。其实,重整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破产和解制度只能就公司企业的外部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调整,而无法对导致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的关系到公司最后能不能更生的内在关系进行调整,如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内部的权力结构、经营方针和管理措施的关系。公司的振兴则取决于公司企业内部深层关系的优化协调。还有,重整制度不需到支付不能、停止支付或资不抵债的严重程度即可以实施,从而起着积极的、预防性的程序机能。可在企业有破产解体的可能时来整顿企业,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同心协力下,使企业得以重建再生。而破产和解与重整程序谋求的利益是一致的。正是此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破产和解应与破产重整制度一样,对有担保债权的优先性要有所约束。

 U682687144
U68268714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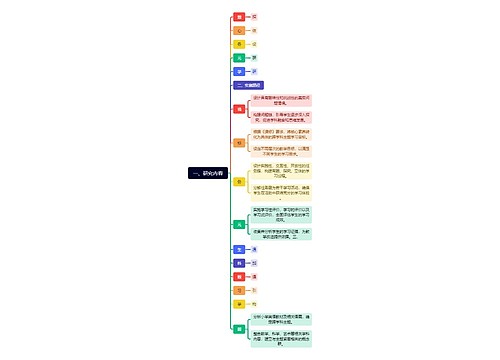
 U633687664
U633687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