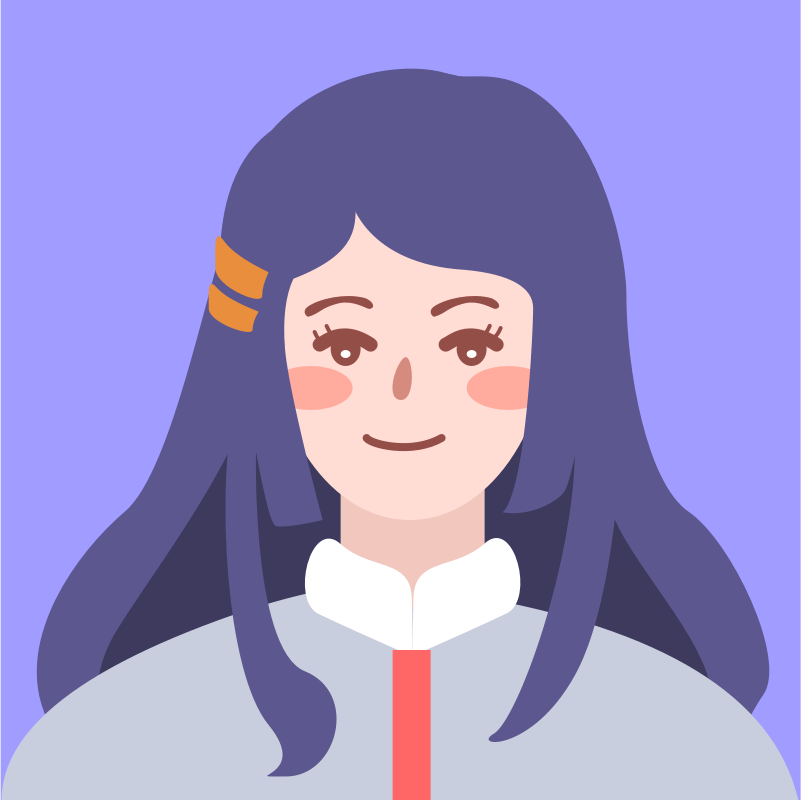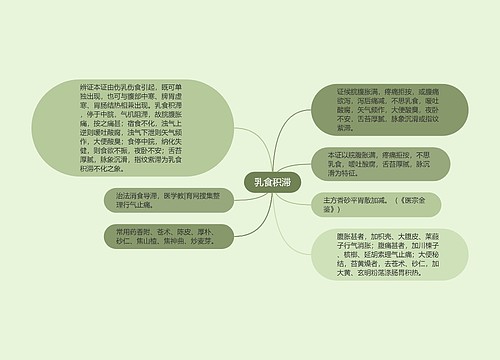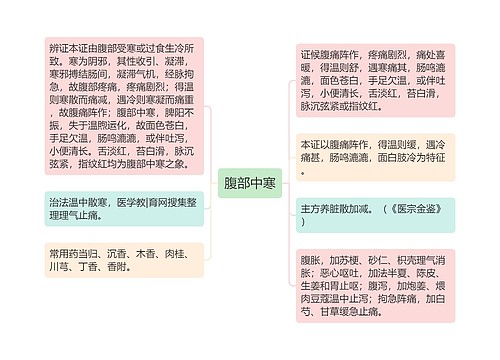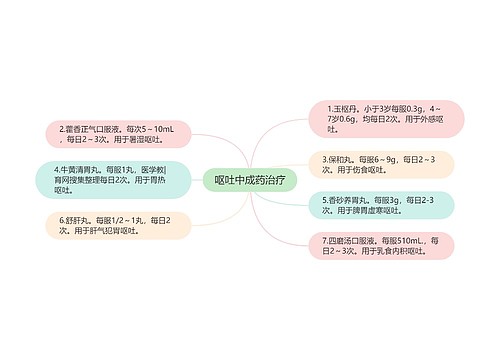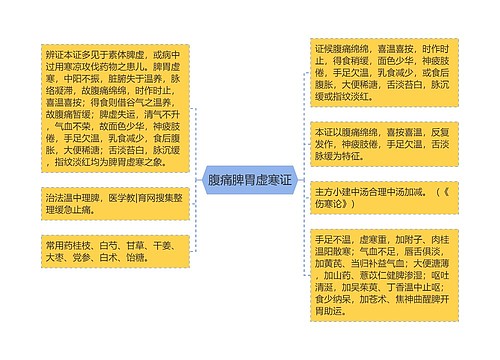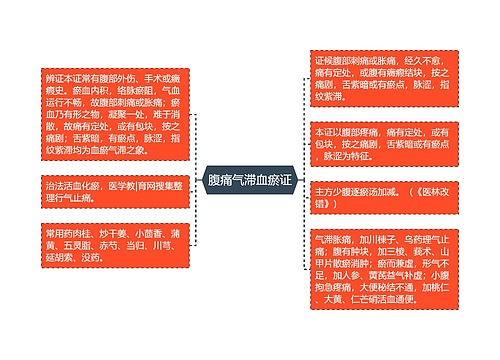“看到张岳鹏(音)和张陈萍(音)后,我们村的那个男人对我说,我们替你找到家人了,并指着张岳鹏说,这是你哥,指着张陈萍说,这是你姐。说完之后,我被他们按住打了一针,打完针之后,我就睡过去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醒来后,只是觉得头疼,其他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从那时开始,以前的事情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只知道他们告诉我的一切:自己叫张小美,张岳鹏是我哥,张陈萍是我姐。”
药物的作用让兰兰失去了记忆,并从此认贼作了亲人。到现在为止,提起这两个人,她仍然一口一个哥、姐地叫着。“我姐对我很好,她给我衣服穿,给我买吃的,还给我吸一种放在纸上的白面儿(警方分析认为,这可能毒品),就因为我觉得呛,才没有吸下去。”
“孩子从小是我养大的,这哥是从那儿蹦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兰兰的父亲气愤地说,“他们这是作孽呀!活生生地把人药坏了。”
“打针是下午的事,晚上姐姐就把我带到了后北屯的一个洗头房里,让我在那儿上班。”兰兰所说的上班就是做起了洗头女。 “姐姐”收了所有工资
据兰兰回忆,她“工作”的洗头房相当小,仅有十几平米大,外面是理发室,里面隔了一间,放了两张按摩床。店名叫“温州理发店”,女老板30岁左右,还有两个男老板,一个大约20岁,另一个大约30岁,他们叫“老虎”和“熊猫”,平时他们不干活,只有人多的时候,他们才帮帮忙。那段时间里,兰兰和这家理发店原有的两个女孩每天给人洗头按摩。
“我在那儿给客人洗头的工资是一次20元钱,有的客人要求按摩,还要再给20元。这是我偷偷看到的。”兰兰讲了她偷偷看到的一幕,“有一个胖子经常来按摩,每次都要我给他洗头按摩。有一次胖子给老板钱时,我看见是20元,钱上还有胖子留给女老板的手机号码。”
所谓的收费只是兰兰看到的,这些钱兰兰从没有拿到过一分,洗头房老板在扣了自己的一份后,将另一半给了兰兰的“姐姐”。也正因为没有钱,兰兰离不开洗头房,不得不留下继续工作。兰兰清楚地记得“姐姐”和洗头房老板说的一句话:“一分也不要给她。”
“我姐在每晚下班接我走的时候,就跟老板把钱拿走了。”据兰兰回忆,“除了洗头、按摩挣钱以外,我每天就是睡觉。每天上午,‘姐姐’让我匆匆吃点东西后,就把我送去洗头房,晚上定时接我回家睡觉。每天都是固定时间接送,我姐接送的女孩除了我之外,还有20个,她们都比我大。我们每个人每月都要打针。‘姐姐’非常厉害,有一次,‘姐姐’带我去大王村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女孩,当看到那个女孩病得不重,就马上让她起来上班。”
现在兰兰身上穿的还是“姐姐”给她的一件衣服,白色的毛绒棉衣,尽管稍稍显大,但新式的款样,让年幼的她,看上去成熟了很多。“身上的裤子也是姐姐给我买的。”
虽然“姐姐”给了兰兰不少东西,但她依然非常害怕她这个姐姐。“你们抓不了她”,对着民警兰兰脱口而出,“她很厉害,她手下有100多号人呢!床下有好多刀子……”
让兰兰最担心的就是每个月这些女孩和她一样要打一次针,“针是红色的,打完后,都要昏睡一个多小时,家里还有很多药瓶,不知道是什么药。我姐和我哥每晚都吸一种白面面,放在纸上吸的,不仅他们吸,我姐带的那20多个女孩们也吸。”
“姐姐”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五台拿这种“白面”,有一次她还带着兰兰去五台县玩了几天。“那几个地方也都是按摩、洗头的,那儿的人也都吸这种白面面。”兰兰说。
兰兰的这种生活,最终还是被老魏知道了。3月8日,老魏在后北屯摆小摊的一个亲戚看见了兰兰并发现了她的住所。亲戚将这消息赶紧通知了老魏。
听到女儿的消息,老魏骑了3个多小时自行车,从郊区马上赶到后北屯来到了女儿的住所。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女儿见到老魏后却不认识他:“你不是我爸,张陈萍才是我姐,张岳鹏才是我哥。”
“一伙人坚决不肯将兰兰还给我。并说兰兰不是我女儿。后来他们看我实在不走,就打了个电话,这才同意我把女儿带走。并和我说‘是你女儿就带回家吧!但如果你报了警的话,我们就不会放过你。’”现在老魏想起当时的情景,仍情不自禁地感到害怕,“我是一个外地人,在太原无依无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
当晚接上女儿后,老魏就没敢回东太堡村,而是将女儿带到了自己的姐姐家。但令他伤心的是,女儿连姑姑也不认识了。一天后,她只能认出老魏是自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