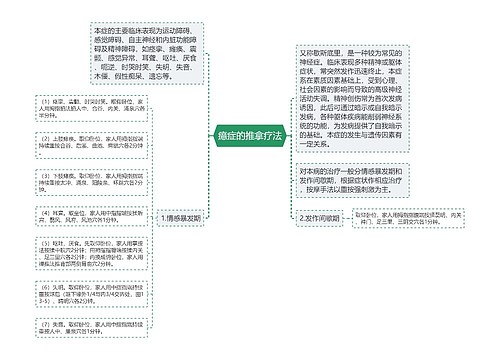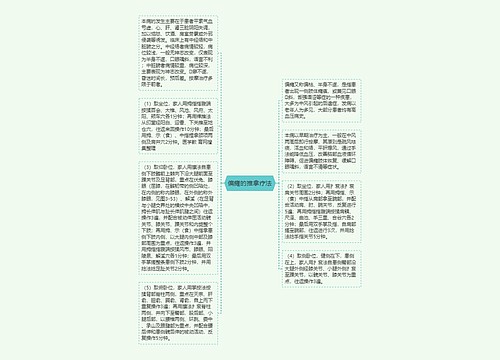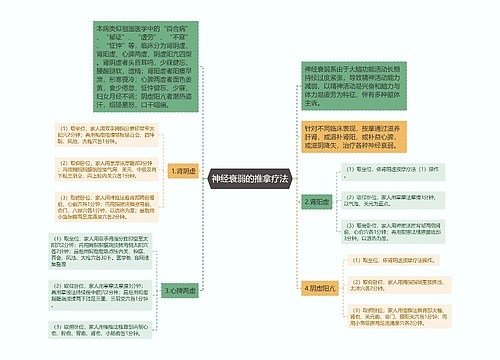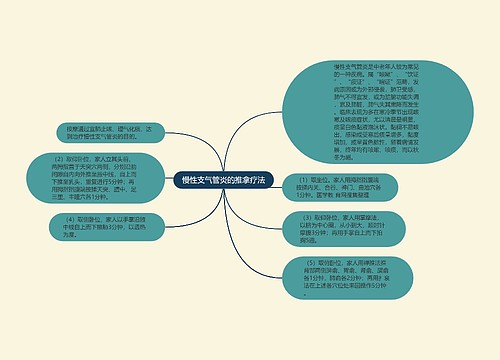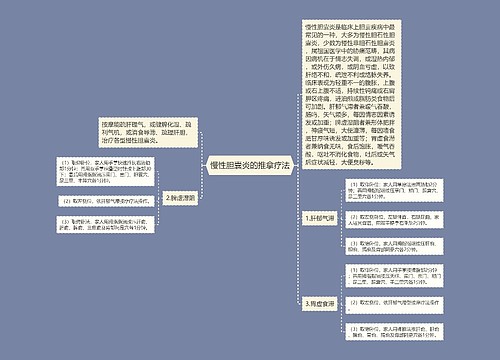本案是典型的由雇员的侵权行为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涉及到三个法律适用问题。即雇员致害的赔偿责任原则,“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界定,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问题。
最高院司法解释中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该规定阐明雇主责任属替代责任规则,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应由其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对雇主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雇主承担的是替代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向雇员追偿。雇主替代原则是为了保障受害人赔偿权利的实现。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该规定中还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致人损害的,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这样的规定连带责任与传统的雇主责任有很大区别,为什么确定雇主责任为替代原则后又确定一个连带责任?这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议,认为两个责任纠缠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容易引起理解上的困惑和执法上的不统一,雇主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向雇员追偿,雇主承担替代责任后难道不能向雇员追偿吗?按替代原则的理解当然也有追偿权利。雇主替代责任与连带责任之间的规定是“分号”连接,在适用上是选择适用关系还是特殊与一般关系?本案由于蒋某某伤人后逃逸,当事人也没要求其参加诉讼,故法院按雇主替代原则判郑某赔偿原告安某某,但如果蒋某某参加了诉讼,其伤害行为也属故意的,法院很可能按连带责任判郑某与蒋某某连带赔偿安某某,这极易引起执法上的不统一。笔者认为,从司法解释本意理解,两个责任适用上是一般与特殊关系,即一般适用雇主替代原则,但雇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适用雇员与雇主连带责任原则,当然无论适用哪个原则,雇主都有追偿权利。
对“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界定,司法解释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对于是否超出授权范围的行为,一般采用“客观说”,即以执行职务的外在表现形态为标准,表现形式上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具有此外在特征,即可确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蒋某某伤害安某某的起因,时间,场所与其雇员身份是有紧密联系的,目的也为了维护雇主的利益,故其行为虽然不属雇主授权,但亦应认定为雇佣活动。但需指出,雇员在工作中与客户打架是否属“雇佣活动”一直争议较大,执法尺度上也很不统一,笔者认为应区别情况处理。1.客户与接受的服务之间并无明显争执,雇员因自身素质原因与客户发生打架纠纷,因其纠纷与雇佣活动并无必然关系,故不属于雇佣活动;2.雇员与客户有私仇,在服务过程中故意挑起事端发生纠纷,其行为也不属于雇佣活动;3.雇主有明确规定,由专职人员处理与客户的该类纠纷并禁止其它他工作人员介入,而雇员知道该规定却擅自介入,属超越授权行为,由雇员个人承担责任;4.雇员在处理相关工作事宜中与客户发生争执,进而发生打架纠纷,虽然雇主一般不会授权雇员可以用暴力解决工作中的纠纷,但雇员的行为是与其工作紧密相关的,且基本目的是维护雇主利益,故应按司法解释精神推定为雇佣活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是对“从事雇佣活动”进行了扩大解释,以前第4种情况很多时候没有认定为属雇佣活动,因为单从文意上讲很难理解雇员与客户打架是“从事雇佣活动”。但从受害人角度讲其接受服务是冲着雇主的经营而来的,雇主完全不承担责任不利于社会正义的合理分配。同时,从法律激励机制上讲,这类情况以前经常发生,与雇主不承担责任有一定联系,雇主纵容雇员伤害客户后,雇员一走了之,客户找谁赔偿?雇主显然不会承认其授权过雇员伤害客户;即使雇主真的没授权过雇员伤害客户,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雇主没有加强管理密切相关的,从经济角度讲,这种法律责任成本是诱导其加强对雇员的管理,何况这本来就属雇主应当作为的义务。
本案还涉及安某某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即过失相抵的构成及适用问题。过失相抵是建立在过错归责基础上的,过错归责的含义是,一个人应当就其自身所犯的过错,在其理性能够预其或应当预其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形成损害的原因力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两方面的,则受害人也应当按照过错归责原则,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应的责任,表现出来就是冲抵了致害人的部分责任,故称为过错相抵。过错相抵的构成在客观上要同时具备损害结果的同一性和造成损害的原因力的竞合这两个条件,而本案中,一方面安某某的行为与蒋某某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显然不会相同,不具备损害结果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安某某被刺伤也只有蒋某某的损害行为是唯一原因,并不存在原因力的竞合,故并不构成过失相抵。其次,在过失相抵的运用上,加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与受害人的一般过失不适用过失相抵。本案中,蒋某某的加害行为显属故意,安某某只是一般过失,两者也不能过失相抵。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