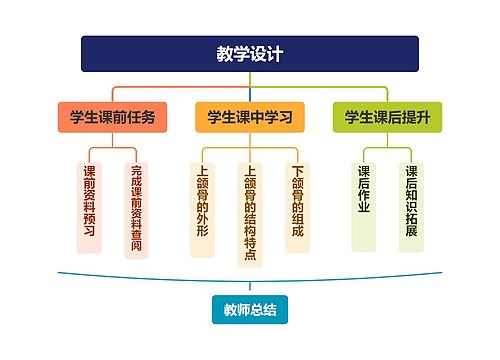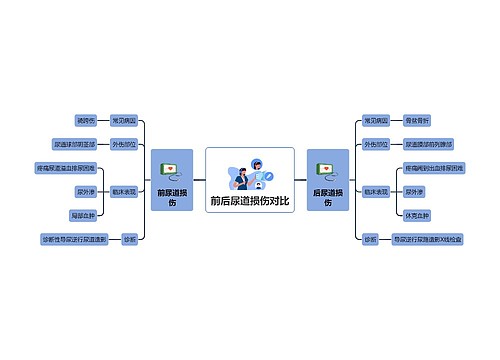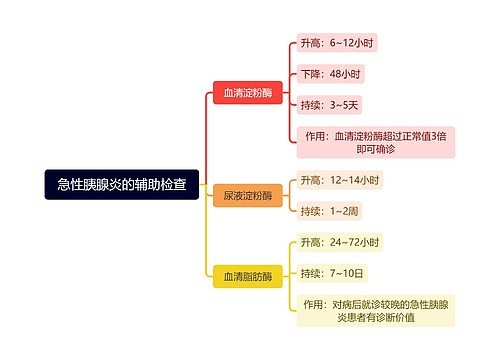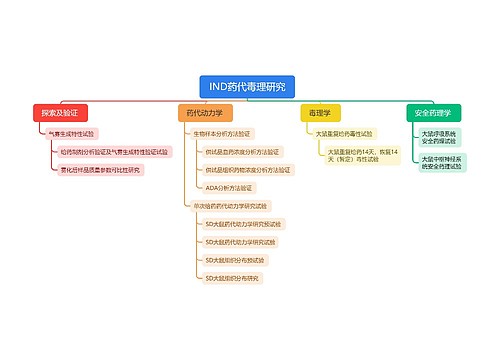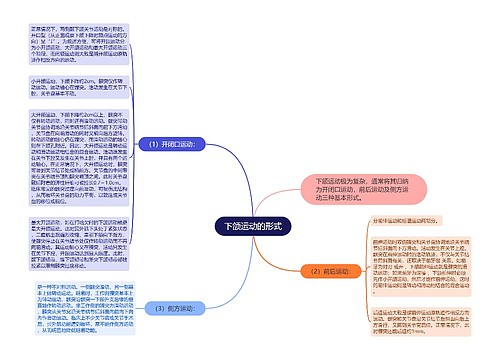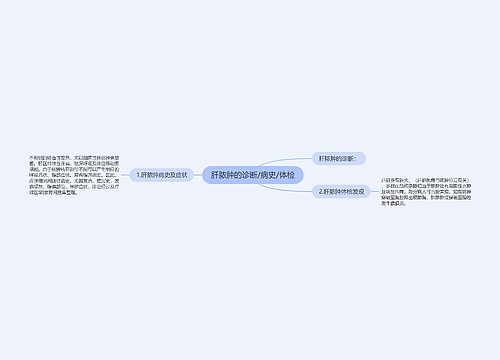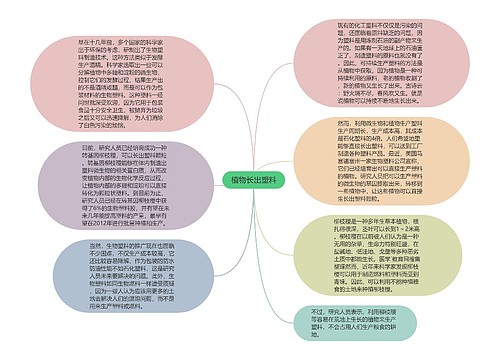基因检测是与非思维导图
谎话最甜
2023-02-17

最近,谷歌联合创始人兼技术总裁塞吉。布林有了新的任务,那就是每隔数天,就要反复地从3米高的泳池跳台上勇敢跳入水中并潜泳一段时间。他从事这项有些怪异的运动并非是为了健身,而是希望能降低未来某一天身染帕金森病的风险。帕金森病是一种典型的晚发型疾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一般集中在50~60岁。
树图思维导图提供《基因检测是与非》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基因检测是与非》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c5c1ddff524407e044a240bdf99b8d53
思维导图大纲
相关思维导图模版
9.战斗的基督教思维导图
 U582679646
U582679646树图思维导图提供《9.战斗的基督教》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9.战斗的基督教》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33d168acd0cd9f767f809c7a5df86e3a

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思维导图
 U882673919
U882673919树图思维导图提供《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在线思维导图免费制作,点击“编辑”按钮,可对《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_副本》进行在线思维导图编辑,本思维导图属于思维导图模板主题,文件编号是:1672f555831e7d9a3bb2cf2fb792cb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