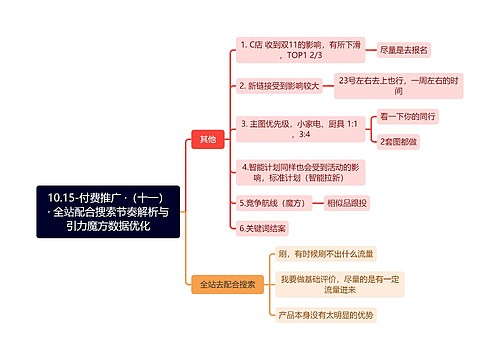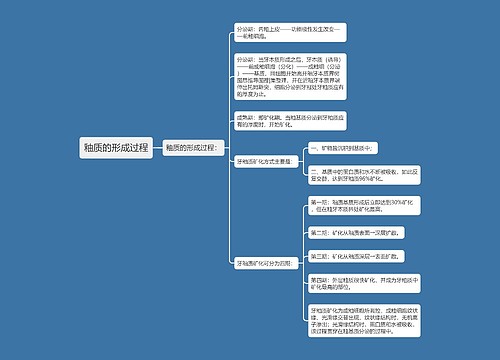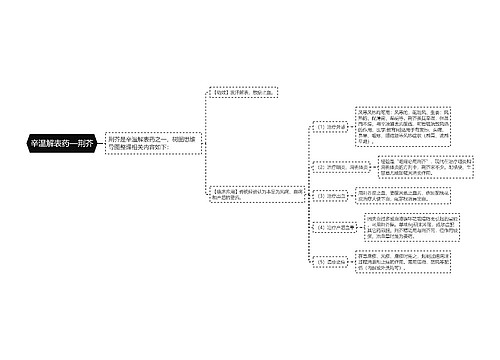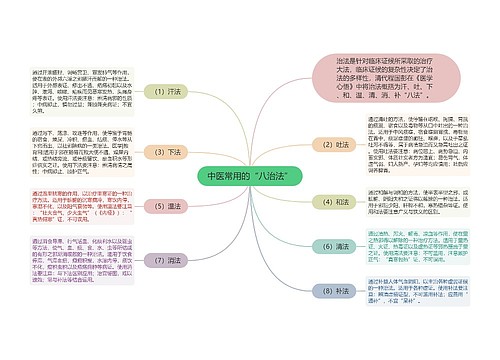经上海海事法院审理查明,被告W公司于2006年11月委托原告G公司将一批男式夹克从中国上海运往美国纽约,约定海运费为每个40英尺高箱美元4400元、每个20英尺标箱美元3350元,AMS费用美元25元。原告向被告签发了提单,载明托运人为被告W公司,收货人为T公司,货物为1个40英尺高箱及1个20英尺标箱的男式夹克,海运费支付方式为到付(FREIGHTCOLLECT)。后被告W公司通过在原告G公司费用确认单传真件上签字的方式,对涉案海运费美元7750元及AMS费用美元25元予以认可。被告W公司还出具电放保函,请求原告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电放给提单记名收货人T公司。原告G公司依约完成运输事项后,于2007年2月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W公司支付涉案货物海运费及AMS费用,但被告W公司至今未予支付。
裁判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海上货物运输事项的约定意思表示真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已成立、生效,并为涉案提单所证明。双方均受该合同约束,并应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现原告G公司作为承运人履行了合同项下的海上货物运输义务,即有权依约收取相关海运费用。对于费用组成及金额,被告W公司已作确认。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提单项下的货物已作电放处理,承运人可以不凭已签发的提单放货。在此情况下,对运费支付方式修改是正常的应对措施,且原告亦已据此开出运费发票,由此产生的支付运费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即便双方约定的是运费到付,在提单未经流转到收货人的前提下,托运人作为运输合同缔约方,仍有支付运费的义务。关于利息损失,原告请求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但未提供相关贷款依据,故可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币种企业活期存款利率支持原告的利息损失。法院依照《海商法》、《合同法》之规定,判决被告W公司向原告G公司支付海运费美元7,750元、AMS费美元2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服判未提出上诉。
评析本案纠纷围绕运费支付方式确定及运费支付义务承担展开。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支付运费是相对于运输货物的主要合同义务和对价。通常在提单上载明的运费支付方式有“预付”和“到付”两种,相对应的分别由托运人和收货人支付运费。涉案原、被告原先通过提单载明方式约定的运费支付方式的确是“到付”,但原告主张事后被告曾出具保函承诺变更支付方式为“预付”,被告却对此加以否认,同时辩称涉案保函上的印章系伪造的。同时被告还认为,原告应首先证明其已向记名收货人主张运费并遭到拒付,被告作为托运人才应承担支付义务。
笔者认为,就涉案纠纷中的运费支付义务承担问题而言,双方究竟如何约定已不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即使被告关于“其未做出变更海运费支付方式”的抗辩主张得以成立,涉案海运费亦应由其承担。
收货人是否支付运费由证据规则来辩明原告认为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无人提货,记名收货人亦未支付运费;被告则认为原告应首先证明其已向记名收货人主张运费并遭到拒付,被告作为托运人才应承担支付义务。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自主张。显然,“提单记名收货人是否已履行了涉案海运合同项下约定的向原告支付海运费用的义务”即为双方重大争议焦点之一。就该争议焦点,如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而导致该节争议事实难以认定时,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作出裁判。原告主张的是“收货人未履行支付海运费用的义务”。被告认为根据合同运费到付的约定,应先由收货人承担支付义务,且只有原告证明了收货人拒付的事实时,被告才应承担支付义务,并还表示无法明确原告是否可能重复收取两笔运费。根据被告的上述抗辩,其主张的实质就是“收货人可能已经履行支付海运费用的义务”。因此,原告主张的是“收货人运费未付”的否定性事实,据此其不可能也无须对此举证加以证明。反之,被告作为托运人提出后履行抗辩,其依据的事实必须是“收货人运费已付”,对此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必须对其肯定性事实主张举证加以证明。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收货人已依约向原告支付了涉案海运费用,故应认定“收货人运费未付”事实成立。
运费支付义务归属由合同法来厘清就海上货运合同中的运费支付之债而言,无疑承运人是债权人,托运人是债务人。本案中,海上货运合同曾经约定的运费支付履行主体是合同缔约双方外的第三人———提单记名收货人。由于在电放条件下,涉案提单并未正常流转到记名收货人手中,故该收货人并非海上货运合同当事人,其仅负担向债权人即承运人履行支付运费行为而不承担合同责任。因此该合同是一个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收货人作为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其加入合同履行也并未改变承运人作为债权人、托运人作为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在依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确定“收货人运费未付”事实的情况下,被告作为负有支付运费义务的债务人,应代第三人履行;如被告不代为履行,即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为此,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涉案合同项下相关运费并赔偿相关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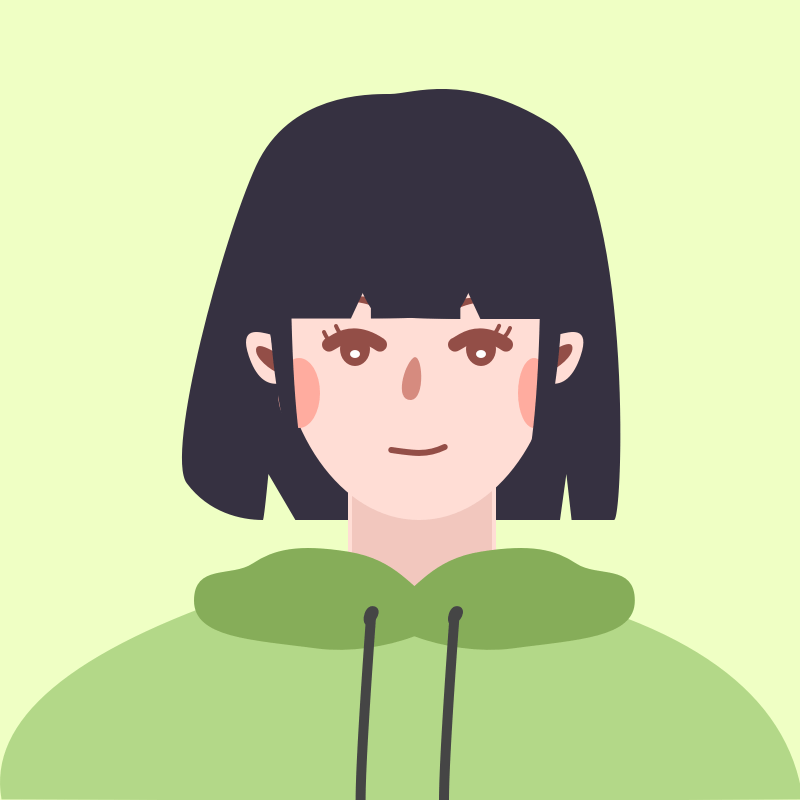 U880271396
U88027139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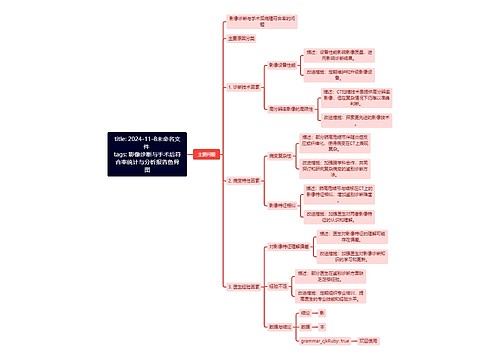
 U249128194
U249128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