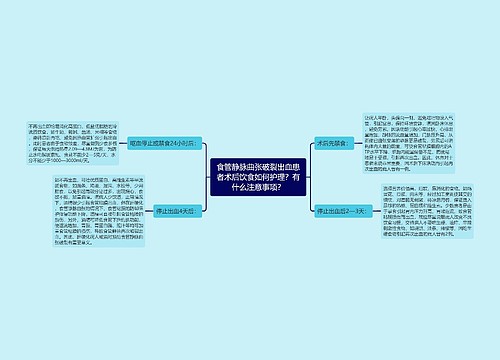意思表示真实是有效合同的基本精神,而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手段订立的合同却违背了这一精神,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欺诈、胁迫方可通过行使撤销权而使合同无效。但包含了仲裁条款的合同因此归于无效时,仲裁条款是否也随之无效呢?虽然美国的“Prima Paint Co. V. Flood & Conklin Mfg Co.案”中最高法院作出了因欺诈而签订的合同中,仲裁条款仍然有效的判例。但先前审理此案的布莱克法官却自有他的道理:“法院认为,合同在欺诈取得情形下的有效性问题由仲裁员来决定与其决定在有效合同下的争议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如果合同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那么,除非被欺诈方当事人选择认定合同存在,合同本身根本不存在,没有东西可供仲裁”。[1]在早年的英国曾有过类似的判例:当主合同自始无效的情况下,仲裁条款无效。
主合同设定的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与义务,依据民法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一种平衡。一方当事人基于欺诈的意思,其目的在于破坏这种平衡,以获取非法利益。但仲裁条款是在双方当事人就主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时的救助条款,这一条款不是单为一方当事人设定的权利或义务,它规定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利将争议交付仲裁,也都有义务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设若主合同欺诈的情况下,仲裁条款的订立也必然受欺诈,那么当被欺诈方将主合同欺诈行为交付仲裁后,欺诈方不仅承担了不得改诉法院的义务,同时面临着仲裁员对欺诈行为的确认与制裁。而且与诉讼相比,仲裁的灵活性更大,公正性更强,欺诈方承担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也就更大。欺诈方不仅不能因此获取利益,反而为自己设定了如此的义务,按常理,这种可能性极小。况且,在多数情况下,尽管合同的实体权利义务存在欺诈,但在双方签订仲裁条款时,是明示的、可选择的。故在主合同受欺诈情况下,仲裁条款不必然就是欺诈的产物。香港城市大学的莫世健就认为,在主合同存在欺诈时,应考虑仲裁本身的意志表示是否真实,其与主合同的意思表示不完全一致,可能存在主合同有欺诈,仲裁意志是真实的情况。[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Prima Paint Co.V. Flood & Conklin Mfg Co.案”中也指出,即使争议是因主合同欺诈而引起,只要仲裁条款本身不是欺诈的产物,法院就不能排除仲裁。[2]所以除非有证据证明仲裁条款本身是以欺诈手段订立的,该仲裁条款才与主合同一起无效。[3]
随着仲裁制度的发展,国家对仲裁的有力支持,现今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对主合同欺诈情况下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均表现出宽容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在主合同因一方当事人的胁迫而签订的情况下,由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随主合同条款,归于无效。[4]笔者认为,如此理解不合实际情况,也与国际商事实践的需要相矛盾。从民法的基本理论出发,“欺诈”可认为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缺乏“意思表示的一致”,“胁迫”与“乘人之危”则是一方当事人缺乏“意思表示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缺乏是否扩及仲裁条款的订立呢?受莫世健教授对欺诈合同中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意见之启发,笔者以为,主合同受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应考虑仲裁条款本身是否亦是胁迫或乘人之危的产物。如同主合同受欺诈而仲裁条款并不必然受欺诈的情形,存在主合同受胁迫或乘人之危,而仲裁条款却是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所以,主合同在订立过程中的自由意志的缺乏并不当然扩及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仲裁条款的订立。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如果能证明仲裁条款本身是受胁迫或乘人之危订立的,则与主合同一起无效。
综上,主合同无效(包括自始无效与失效)情况下,仲裁条款的效力不受影响,相反,正是仲裁条款发挥作用之时。对于合法有效的合同,仲裁条款的效力体现为对争议事项的解决方式的确定。对于主张无效的合同,仲裁条款的效力表现在仲裁庭或仲裁员对主合同效力的认定。只有当主合同无效的原因影响到仲裁条款的效力时,仲裁条款才与主合同一起无效,两者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因果联系。至于作为管辖权基础的仲裁条款是否实际上无效,在仲裁过程中,是由仲裁庭或仲裁员就仲裁条款本身的效力进行审查,并依此确定其是否具有管辖权,此即管辖权/管辖权做法。至此,笔者以为,本案中,双方订立的仲裁条款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法院无权管辖。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