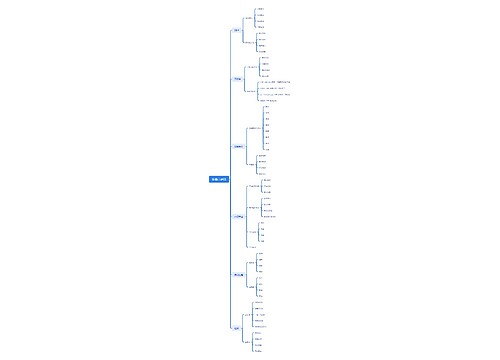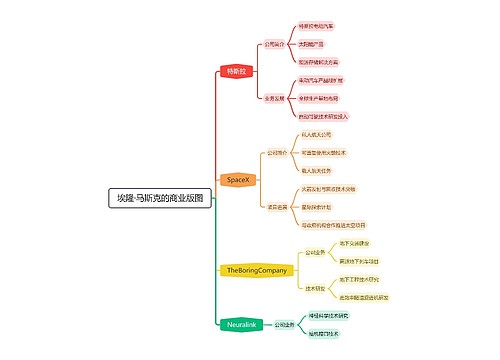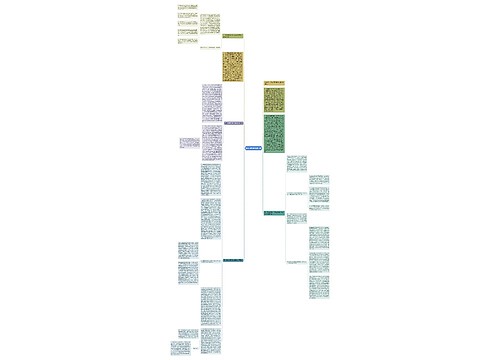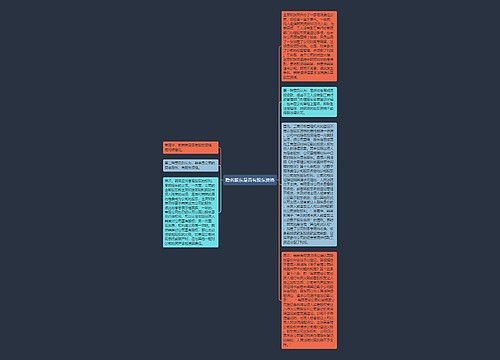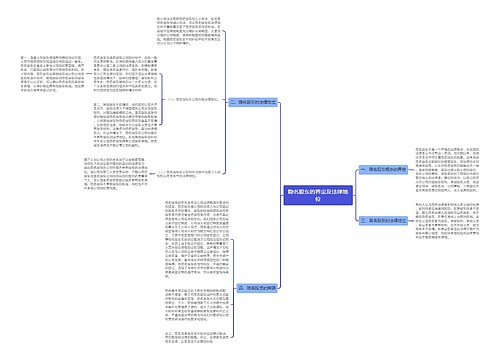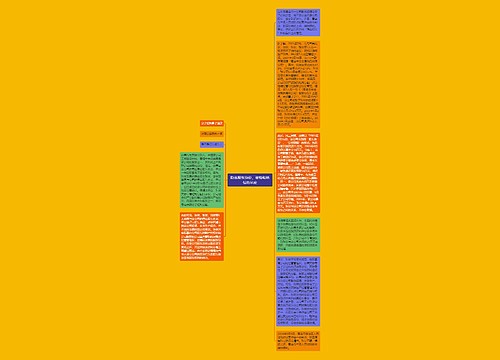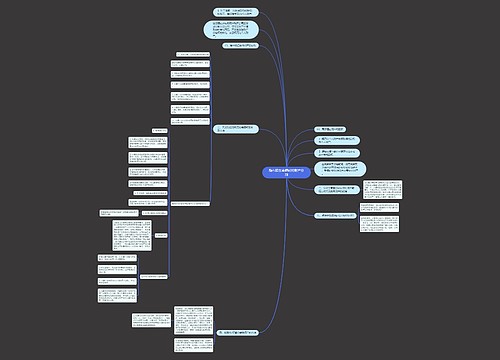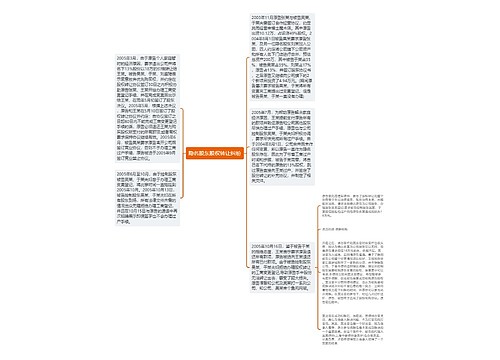[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外服公司”)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静安商楼(简称“静安商楼”)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百乐门经营服务总公司(简称“百乐门公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宝城商业房产公司(简称“宝城公司”)
原座落于华山路307号全幢公房由“百乐门公司”下属正章洗染工场租赁。1987年12月26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财贸办”)批准,“百乐门公司”与“宝城公司”在上述房屋旧址联合建造“静安综合服务楼”。1988年3月2日,静安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以下简称“区财贸办”)批准将“静安综合服务楼”定名为“白玉兰饭店”。随即,“百乐门公司”与“宝城公司”联合组建了“白玉兰饭店筹建处”,并以该筹建处名义向“市财贸办”申请年度贷款,获建设银行两次放贷125万元。
1989年间,静安区人民政府与“外服公司”洽谈,引进“外服公司”参与白玉兰饭店投资。因“外服公司”坚持要求静安区用一家企业名义与之合资,故区政府决定由“宝城公司”出面与“外服公司”签订“白玉兰饭店”合同书。1989年8月24日“宝城公司”与“外服公司”签订联合投资经营白玉兰饭店的合同及白玉兰饭店章程,明确“宝城公司”占40%股份,“外服公司”占60%股份。因“百乐门公司”对区政府的行政决定有异议,故“区财贸办”于1990年4月召集“百乐门公司”、“宝城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白玉兰饭店”合同中属于“宝城公司”一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百乐门公司”、“宝城公司”共同享有和承担,在“宝城公司”应向白玉兰饭店投资的240万元资金中,已投入贷款125万元,由双方共同偿还,其余部分也由双方共同投资,所得利润和亏损由双方各半分摊。
1990年10月20日,“宝城公司”、“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决定抄送“百乐门公司”,“百乐门公司”委派的毛申媚为董事会成员之一。1990年12月25日,“宝城公司”与“外服公司”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联营企业即白玉兰饭店的登记注册,并定名为“静安商楼”。经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验资,注册资金640万元,“外服公司”实际投资384万元,“宝城公司”实际投资256万元。“静安商楼”营业后,自1992年起获得利润,直至1997年度,“宝城公司”与“外服公司”按“静安商楼”章程规定的比例领取了各自的收益,“宝城公司”亦按与“百乐门公司”的协议,与“百乐门公司”共享了“静安商楼”的收益。
1995年,“宝城公司”以“静安商楼”名义向银行贷款1180万元,所贷款项划至“宝城公司”用于房地产经营。1996年7月,“宝城公司”又与“静安商楼”签订房屋参建协议,收取“静安商楼”300万元。1998年9月,“静安商楼”向上海院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宝城公司”,分别要求其退还钱款、返还房屋参建款,两案经调解结案,确定“宝城公司”共应返还“静安商楼”1400余万元。“百乐门公司”担心其在“静安商楼”的权益受损,于1998年9月1日起先后向“外服公司”、“宝城公司”发函,要求尽早解决其在“静安商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并请求静安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出面协调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3月25日,“静安商楼”董事会以“受宝城公司债务影响”、“静安商楼各项设施陈旧需要改造”为由,决定1998年度利润暂不分配。为此,“百乐门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在“静安商楼”的股权。原审法院追加“外服公司”和“静安商楼”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百乐门公司”作为“静安商楼”的原投资者之一,在其以投资人名义实施筹建工作过程中,依据政府行政的决定,变更为隐含于
一审判决后,“外服公司”和“静安商楼”上诉称:“静安商楼”系“外服公司”与“宝城公司”投资设立,有“静安商楼”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为证,“百乐门公司”并不具备投资人身份;“宝城公司”与“百乐门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宝城公司”在“静安商楼”中的40%股权一半属“百乐门公司”所有系无效的民事行为,应不予保护;“外服公司”对“百乐门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不知情,也未表示认可。为此,不同意一审判决确认“百乐门公司”在“静安商楼”中20%股权及办理相应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百乐门公司”辩称:“百乐门公司”系“静安商楼”投资人之一,虽然“百乐门公司”的投资隐含于“宝城公司”,但双方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且“外服公司”、“静安商楼”对此明知而未提出异议。现“百乐门公司”要求确认“静安商楼”20%股权并办理有关工商登记手续应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静安商楼”系“宝城公司”与“外服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联营企业,虽然“百乐门公司”对其具有投资,但该投资系以“宝城公司”名义投入,“百乐门公司”系通过“宝城公司”间接享有“静安商楼”的股权。由于“静安商楼”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均无“百乐门公司”投资记载,故“百乐门公司”的投资行为属隐名投资。“百乐门公司”的权利义务是通过与“宝城公司”的隐名投资协议来实现的,而该协议的效力仅限于“百乐门公司”与“宝城公司”之间,“百乐门公司”不能以此协议对抗第三人,故“百乐门公司”要求变隐名股东为显名股东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据此判决:一、撤销原判;二、对“百乐门公司”要求确认“静安商楼”20%股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是一起股权确认纠纷,审理中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百乐门公司”在“静安商楼”中的投资性质是否属隐名投资。
隐名投资又称隐名合伙,是指双方当事人以订立契约的方式约定一方对他方所经营的事业进行投资,分享利益,并在出资的限度内分担损失,但不参与他方经营活动的合伙。“静安商楼”系“宝城公司”与“外服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联营企业,其中“外服公司”占60%股份,“宝城公司”占40%股份,双方的投资份额在联营企业章程中写明,在验资报告和年检报告中均有记载。“宝城公司”又与“百乐门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宝城公司”与“外服公司”关于“静安商楼”的联营合同中属于“宝城公司”一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百乐门公司”和“宝城公司”共同享有和承担;“宝城公司”向“静安商楼” 投资的资产由双方共同承担;“宝城公司”从“静安商楼”所得利润由双方各半分享。从协议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来看,“百乐门公司”的这一投资行为符合隐名投资的特征。虽然我国法律对隐名投资未作规定,隐名投资属于不规范的投资行为,但
(二)“百乐门公司”作为隐名股东能否转变为显名股东。
隐名投资中,隐名合伙人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并相应地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分担企业的亏损,隐名合伙人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其一经出资,出资财产的支配权就归显名合伙人,隐名合伙人对隐名投资的财产没有共有权。他与一般的合伙投资的区别在于:(1)隐名合伙人只出资而不具名,显名合伙人一方负责经营;(2)隐名合伙人不是合伙的权利主体,不能以合伙人名义对外行使权利;(3)合伙财产支配权属显名合伙人,隐名合伙人只享有收益权。“百乐门公司”在“静安商楼”投资中是以“宝城公司”名义投入,并通过“宝城公司”间接地享有“静安商楼”的股东权益,“百乐门公司”与“静安商楼”之间没有直接的投资法律关系。从隐名投资法律关系的特征来看,“百乐门公司”本身不是“静安商楼”的权利主体,不能以“静安商楼”的名义对外行使权利。“百乐门公司”要求确认其在“静安商楼”中的股权,从隐名股东转变为显名股东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百乐门公司”的权利是仅通过与“宝城公司”之间的隐名投资协议保证实现的,该协议的效力限于隐名合伙人和显名合伙人双方之间,“百乐门公司”不能以该协议对抗第三人。“百乐门公司”由于不具备“静安商楼”股东地位,如要成为“静安商楼”的股东,必须征得联营另一方“外服公司”的同意,否则无异于将新的股东强加给“静安商楼”,有悖于“静安商楼”作为联营企业本身具有的“人合性”,也违背当初要求“百乐门公司”隐名的初衷。虽然“外服公司”在与“宝城公司”共同经营“静安商楼”过程中,知道“宝城公司”投资中部分是“百乐门公司”所出,及“宝城公司”推举“百乐门公司”毛申媚为董事,或者将利润再分配给“百乐门公司”,但也仅是明知“百乐门公司”隐名投资,不能视为认可“百乐门公司”股东地位,即“外服公司”的“默认”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并不因此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况且,“宝城公司”上述行为的实施均是“宝城公司”作为股东的单方面权利,“外服公司”并无权拒绝和阻止。本案中“宝城公司”因自身债务而危及在“静安商楼”中的40%股权,进而影响到“百乐门公司”的隐名投资,“百乐门公司”只能依隐名投资协议向“宝城公司”主张权利,而不能成为“百乐门公司”转变为显名股东的理由。因此,二审法院对“百乐门公司”要求确认其在“静安商楼”中20%股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判决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按:
公司法施行后,在先成立的不符合公司法要求的公司,有充分的时间按照公司法的要求予以规范,如修改公司章程、重新制作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股东变更登记等。但此应当是公司股东与利害关系人之间协商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公司的内部股东登记和工商股东登记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且不一致情况下,有关当事人才有权提起确认股权或股东之诉。本案原告作为联营企业静安酒楼的隐名投资人,未在该时机要求规范公司,从而取得显名投资人即股东的资格,进而确立其在公司的与其投资相应的股权,应当认为其虽有苦衷,但仍接受了隐名投资人的地位。
隐名投资最大的风险就是不能取得显名投资人即股东的资格,因为它与股东公开的要求不符(公司的内部股东登记和工商股东登记都是为了股东公开)。但隐名投资行为并不因此而无效,而是对外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仅在隐名投资人与为其投资的显名投资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公司的内部及外部股东登记行为因其公示性而具有对抗隐名投资人的效力,除非全体显名股东同意接纳隐名投资人为显名股东,并因此而变更股权持有份额和比例及股东登记,否则,隐名投资人应当自行承担隐名投资行为的风险后果,不能请求法院强制将其确认为显名股东并持有一定的股权。否则,股东公开原则就失去了意义。
隐名投资要求隐名人将其投资交给与其发生隐名投资关系的显名投资人,并以后者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公开的投资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隐名投资人仅与为其投资的显名投资人发生隐名投资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与第三人发生公开投资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隐名投资人对第三人及依公开投资设立的民事主体均难能享有法律上的请求权。虽然隐名投资人也追求投资回报利益,但这种投资回报利益并不是以显名股权的持有及以显名股权分红的方式表现和实现的,而是以与其有关系的显名投资人的协议约定的投资回报方式表现和实现的,因此,隐名投资人在协议约定的年度投资回报不能取得或顾虑其隐名投资风险时,应向与其有关系的显名投资人提出请求,或者要求该显名投资人给付年度投资回报;或者要求解除隐名投资关系,由该显名投资人退回其投资;或者通过该显名投资人依法定程序为其取得显名投资人的资格。据此,隐名投资人仅对与其有隐名投资关系的显名投资人有实体诉权,对与显名投资人有公开投资关系的第三人及依公开投资关系设立的民事主体没有实体诉权。没有实体诉权也就没有程序诉权,本案即应驳回作为隐名投资人的原告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