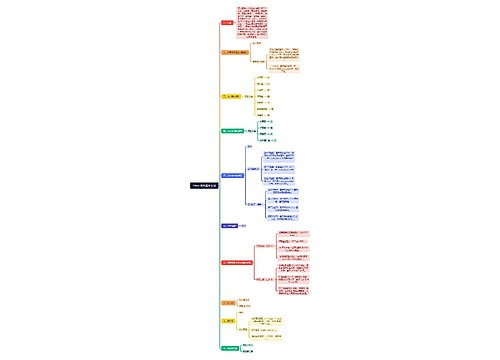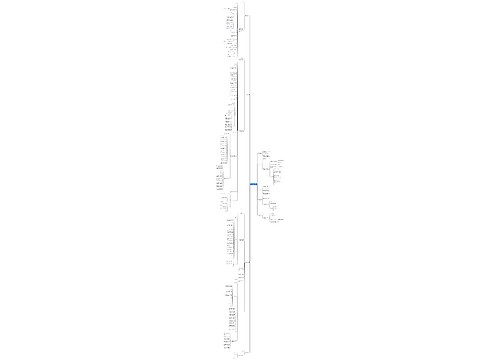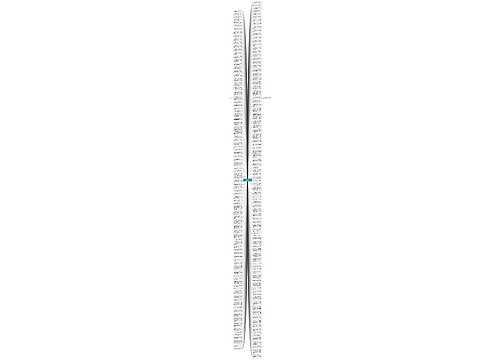"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经纬分明的桃形蒲艺错落着挂满一面墙,轻盈的流苏扇坠,随风摇曳的悠悠绿荷无不引人神往。蒲草在纤纤指尖翻飞,似爱,住于掌心。
村落里有一片池塘,水深过膝,积了淤泥,蒲草便于其间恣意疯长,葱笼蓊郁,纤瘦高展,蔓延成一片青翠的浪涛。而她,便住在池旁,双手抚过蒲草,在清幽间把爱存于掌心。
待到秋风起,雁儿鸣,虫声敛,蒲草黄,她就会收割了蒲草,晒去水分,以蒲作纬,草绳为经,编她的蒲艺。晚间,斑斓的余晖洒在小院里,跃动在她粗糙的指节上,摇晃在她那写尽了人生百态的脸庞上,隐匿在她那干燥的双唇间,伴着霞光,欢悦在蒲艺的淳朴中绚烂。
时间吞噬了蒲艺,咀嚼,再碾碎,意欲将这种坚决永久掩藏。那样可贵的倔强与柔软,细小卑微但坚定不移,一如她的蒲艺,是住在她掌心的爱。
余晖,柔和了蒲草;而住于掌心的爱,温暖了余晖。她编织的,是岁月。在乡村这首舒朗恬淡的散文诗里,她与她的蒲艺是最质朴清新的章节,沉稳坚定又富有节奏。
每每完成一件蒲艺,她就徐徐侧身,眯缝起眼,凝视着手里的清香,似孩子一般笑。那蒲艺是发光闪亮的,大概是她用自己的半生辉煌为蒲艺着了色吧。
隐约地,我看见她浸润着蒲草香,端坐池塘边,坚守在那里,编织心灵深处氤氲着蒲香的岁月。
有位苏联诗人说,想要将心灵冰冻、冷藏,多年后再取出重温,看它融化,再次鲜活。现在,我多么想将她的蒲艺永久冷冻,让它保鲜,不为众人所忘。
她是使者,引領传统,却被那朴素深深吸引。于是,她抛下杂念,让爱成为使命,凝聚成一股住于掌心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