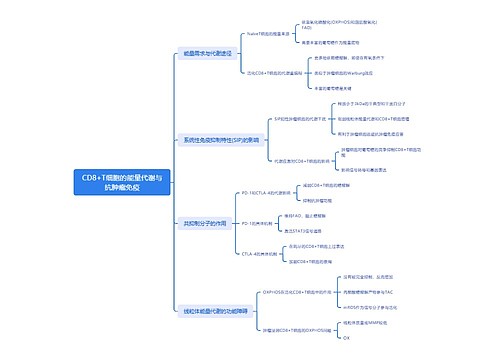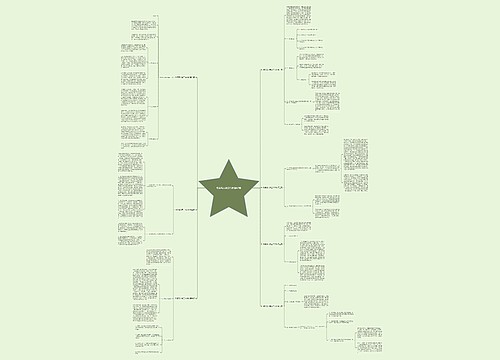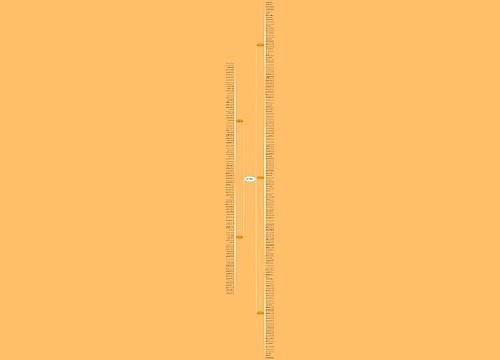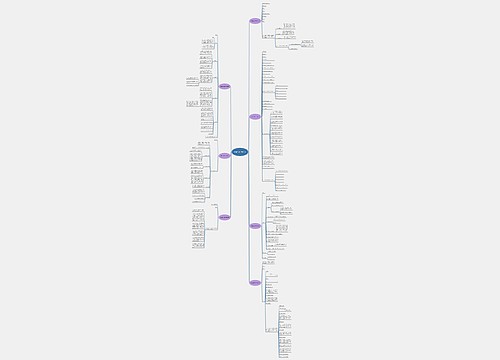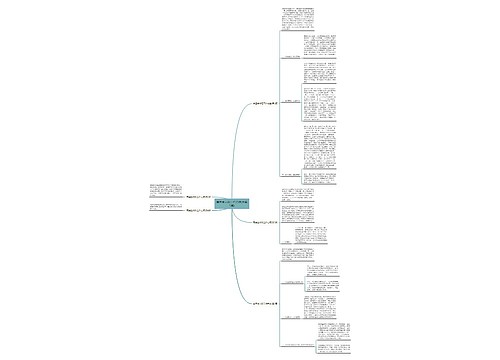《重走》中讲了非常多的抗日故事。上面不知名的老人,桃源县不到一个月建起来的机场,至今仍能在当年野战医院所在地挖出的一堆一堆白骨,反反复复拆好修修好拆的公路。书中涉及湖南地点,都没去过,却都在《国殇》中看过。我对xxx史的了解,基本来自于大学,正值反xxx胜利70周年,出了特别多相关的出版物,包括《国殇》。
现在《南方周末》那期特刊仍然留存着,是南香红写的细菌战专题。报纸里浙江那位老人拉起裤腿给记者展示他腿上一直腐烂的伤口的图片一直存在脑中。《重走》中在常德处如此记载黑死病,源于日军空投的含有鼠疫病菌的麦粒、谷子、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有名有姓的死者达7643人,包括沈从文的"牯子大哥"。
今日还刷到一则微博,博主于三羊鲜声讲了自家部分的抗日记忆。昆明奶奶那边回忆的是轰炸。说有一次轰炸,他们家来不及跑,只好躲在佛桌下,一枚弹药落入院中,没有炸;隔壁一家却在跑警中罹难。"躲警报前,这家人的女主人正要洗衣服,刚把衣服泡在盆里,警报响了赶紧拉着娃娃跑,正要洗的衣服还泡在盆里,等警报解除,却再也没有人回来洗衣服了。"《重走》中关于爆炸的记忆也很多,贵阳"草地上靠电杆边寂寞地躺着一个小娃娃,黄蜡般地肚皮上赫然是机枪子弹穿过的洞,是他母亲把他由轰炸中、火烧中,挤扎中抢出来的。"
还有民国知识分子的气节。一直以来,民国热中大家往往神话知识分子反对政府的一面,反倒忽略了他们的其他面向。他们手头是有专业的事情,他们的确是在颠沛流离中做学问,他们也会因为不能上战场杀敌而痛苦。这一点读林徽因、沈从文部分时非常明显。
费正清的回忆录专门写过林徽因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他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精神而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方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以前写过,可戳")
书中提到了林徽因一家迁徙中和湘黔滇旅行团中那些学生的错落。那些年轻人比他晚来三个月,他们都曾留宿在大同旅社。林徽因他们碰到了中央航空学校的学员。那是在晃县,梁从诫直到晚年都还记得那个雨雪交加的晚上,父亲怎样抱着他和姐姐,搀着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找客店。那里是湘黔道上的重要中转站,所有客店都人满为患。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梁思成听到了大同旅社里传来有人拉小提琴的声音。
"这演奏者一定来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时贸然敲开他们的门。房间里八个小伙子都是来自广东,是中央航空学校的学员,等车前往昆明。就这样,年轻人把他们迎进屋子。林徽因一家与这八位年轻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航校7期学员毕业,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举行,他们没有任何一位亲属在昆明,梁思成林徽因作为荣誉家长出席。1939年开始,他们的遗物也一个又一个寄到了"荣誉家长"梁思成和林徽因手中,每接到一次包裹,林徽因都要哭一场。
辗转迁移中有很多不放弃有韧性的故事,这种迁移中或者那个时代肯定也有无数生厌又无奈的事情,比如xxx,比如无头无尾的遗憾。比湘黔滇旅行团晚10个月出发的李霖灿一行碰到了一个跟踪他们的小女孩。国立艺专的学生在沾益一家店里收集当地年画时,小女孩可能就在店里。
小女孩可能那时决定尾随他们去曲靖,带着仅有两毫钱。书里最后没有写出小女孩为何出逃,但是这样反复劝她回去,她反复追上来之后,最后小女孩停留在大道中央,似乎是孤独地回沾益去了。
我们不再知道这个小女孩后来有了怎样的人生。不过那些留下姓名的人物,不仅是湘黔滇旅行团中的成员,也包括与他们有交集的地方人士,他通过各种文献资料,查阅当地方志等多种手段进行还原,有些虽有名姓,今日看来也已不熟悉。有些则如沈从文的大哥,人生的坎总也过不完。还有更多无名无姓人的故事。
在这种迁移的叙述中,你会意识到,国土以及国土上生活的人民纳入到中国的叙事中,是通过一次次这样的迁移,包括战争中的迁移。这种互相的给予、哺养关系也出现在2018年杨潇的重走中,他们给他贡献了很多故事。
说几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有些农民看到他,认为他是记者,就想让他管管乱挖沙的事情。也有人会很热情地讲述祖上甚至与湘黔滇旅行团交集的故事,也有人会讲怎么做好一碗粉。还有害羞的苗族妇女,她的确说的是"害羞",令我想起之前在迪庆采访,也有同样藏族人跟我说同样的话,"好害羞啊",这个词语好像已经很少出现在我们这些人的语境中,很多时候我们过的都是没羞没臊的生活,对什么都不认真时,自然就没有害羞这个词语存在了。当然还有直播的年轻人,想开民宿的回乡人,说"你要把自己投入进去"的住持。

 U249128194
U24912819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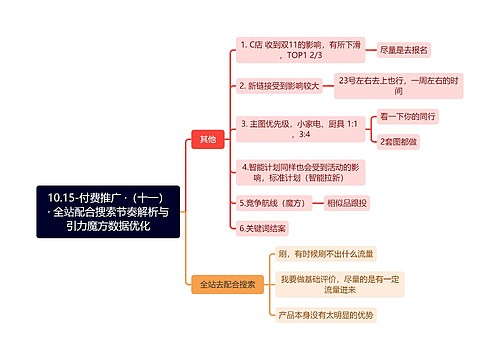
 U182035684
U182035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