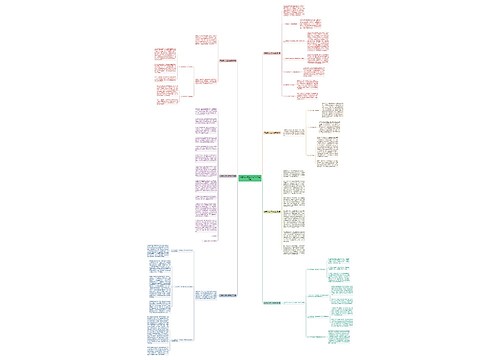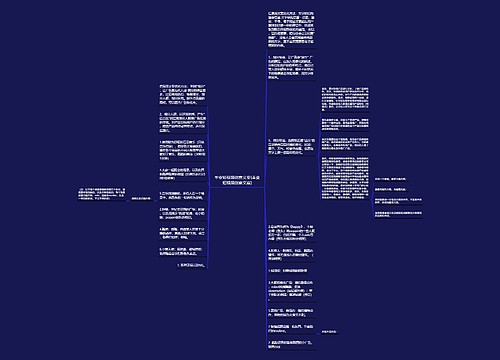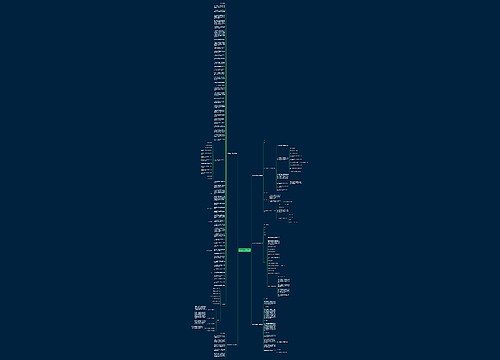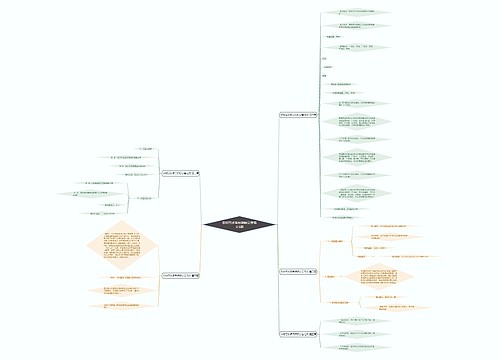不大的几案上,各类粗粝手卷残简堆得满满当当,倒是摆放颇为整齐。
个子已经开始抽条儿的少年正襟危坐,认真翻阅研读,郑重其事,正……
灯盏火光忽朔,染绯少年尚显青稚的脸庞,窗外落雪簌簌,糊窗绵纸上,投下暗影斑驳。
"阿嚏……"少年趴伏在几案,双手交叠垫着下巴,抽抽鼻子,指尖药香清浅,是前几日生的几颗冻疮,可把先生心疼坏了。
少年眼睑轻垂,忍不住嘟囔,"这是什么鬼天气呀,跟师兄生气时的臭脸似的。"坐起身来,"其身正也冻人,其身不正,照样冻人。"
摊开一张生宣白纸,怎奈砚墨冰坚,少年撇撇嘴,只得将书卷卷好放回,又拿过另一卷,注解疑惑无处记下,便索性自问自答。
简陋屋舍里,少年嗓音抑扬顿挫,时而作扶额蹙眉问询状疑惑不解,时而作背手抚须状胸有成竹。
窃以为至人大我,故以生万物,仙佛小我,故能容万物,圣人无我,故能养万物。"
"至人大我,而非无我,故有亲疏之间,物我之别,何也?"
"情礼之本,在于一人,万法之前,先明一我。佛言渡化,无我何以渡?亦言超脱,无我可以超?其与求道何异?知道而求道,求道而知道,其必在我,知我明我而求无我小我,推己及人,由人观己。
"一洲之地,一国之下,及州府郡县至于一家之下,很大余地。"
少年忽然抱臂,气呼呼道剑来描写过年的句子:"我于左右,不留余地剑来描写过年的句子!"
又有些心虚,比出寸余,"还是留一点点余地,先生,如何?"
"那自然是善了个大善喽。礼圣来了也要说善……咳咳……"
"先生,众生平等,我看着很好啊,可我也知其不能。清静无为,我看也很好,静能生定,静能生慧,所谓修内虚极静笃,明澄无滞嘛,还解无为而无不为。哈哈,这诸般教义混为一谈,可也?"
"无妨,心主一也,道理万千,用之在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先生,人之生也,性相近也,本无善恶,性分善恶,用也,否?"
"善,教化之用,不可不察,此之谓‘体用一源’,我知善知恶,我为善,我去恶。"
"先生,师兄教我下棋时,总喜欢扯皮,说什么黑白天地,我们就是在经天纬地,行与不行,下过了才知道,唯行方以证言,唯结果方以证明。而不像那个谁谁谁只会竖大旗的,空谈误也……"
少年垂下头,有些失落,抿紧嘴唇,许久才喃喃,"所以他想什么,从来都不说,赢了棋也不告诉是怎么赢的我。"
"先生,我总觉得,想不想得到是一回事,说不说又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又是一回事。对吧?他输了棋,也从来不告诉我,怎样输给我,还要怎样赢我,可他不说,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先生。做不做的到,总要先想了再说,想的对与错,总要说说看,对吧?就像我……"
少年的情绪来去如风,此刻却是神采飞扬地一挥手,系紧的毛边儿衣袖都被甩开,"我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要做阿良那样的大剑仙,要打得左右满地求饶,也要做很大很大的圣人……"
少年挠挠头,"好像有些远哦,阿良到现在还没答应教我呢……"
少年托腮,含糊应道剑来描写过年的句子:"算啦算啦,先学做君子叭,做不做得到,学了再说,做不做得成,做了再说。哪怕让人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少年略带倦怠打了个哈欠,搓搓有些麻木的手掌,撑开窗子。
降雪已停,亮白映着渐渐消散的沉铅暗色,吹面不寒……
"谁人秉烛行?漠漠起洪钟。我观其销未肯溶,夜色化入光明中,咳咳咳……"
揉了把脸,少年回身收拾好书卷扇灭灯光,乌漆嘛黑对着块儿不甚平整的铜镜整理衣衫,还是不忘念叨,
"镜以自照,也以鉴人。衣衫不理,何以理天地,冠带不正,何以正人心。"
咧嘴扯了个灿烂笑容,像模像样地拱手笼袖,对镜作揖,"敬天敬地敬师敬己,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蓦然收敛,侧耳细听,平静不似刚才,又走向窗前,像是摇头晃脑地只自顾吟诵,
"斯是陋室也,惟吾德馨,静心得意也,天下迎春,吹面不寒也,心境如春,吾行吾道也,九死……"
猛然一扶窗棂跳出窗户,在地上抓把雪,看也不看,便向门口方向砸去,
——引用曲解,未能详注,个人见解,不喜勿喷。[笑哭]

 U633687664
U633687664
 U582679646
U582679646